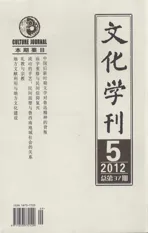礼教与宗教
2012-03-20司马云杰
司马云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如果说某个人或某些人没有信仰,那是他们的自由,谁也不好说三道四,但是,如果说某个国家民族没有信仰,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民族,如果说它没有信仰,那可能就是无知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能够绵延赓续五千多年,没有大道理、大哲理,没有真实无妄的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绵延赓续这么多年的。为使人理解中国人几千年精神世界的信仰及其真实无妄之理,这里不妨把中国礼教与西方宗教作一比较。
明儒陈白沙先生诗说:“人生贵识真,勿作孟浪死。”(《赠陈秉常》)个人尚且贵于认识至真的存在,何况国家民族呢!西方人相信上帝,接近上帝,以此建立起真诚的信仰与发展出宗教情怀,并无可非议的,因为那是西方民族的信仰自由,但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大凡理性的人生,无不即事穷理,无不求乎真知至善,未有不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领悟得真知至善所在,而能够正其心,诚其意,建立起坚定信仰信念,成为至诚之身的。懵懵懂懂而来,懵懵懂懂而去,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就整体而言,就中国这个理性自觉的民族来说,若无诚身之道,或只以某种虚幻的价值设定,让其建立起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早熟的民族。当人类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中国在远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唐虞时代,就建立起了以古华夏氏族部落与东夷氏族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统一国家。希腊人建立斯巴达国,希伯来人建立犹太国,比这晚得多,而且国家也小得多;罗马帝国的出现,比唐虞帝国更晚了一千八百多年,而俄罗斯九世纪才建立国家,欧洲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是很难真切地思考人生大哲学、大道理,思考世界万物最高存在,而建立最高信仰信念的。中国不仅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唐虞时代,就建立起了以古华夏氏族部落与东夷氏族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统一国家,而且在宇宙万物存在地哲学思考上,达到了“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的高度。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文化早熟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穷理尽性至于命的民族,一个信仰上最早理性觉醒的民族。他们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皆要穷尽其理,明白那至真至善者为何种存在。不然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诚其心,正其命,以此建立信仰信念的。这就是儒家讲的“诚身有道”问题。诚身有道,才能建立诚明的信仰信念;而若“诚身无道”,“不明乎善”,则“不诚乎身矣”。 (《中庸》第20章)。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早熟的民族,一个穷理尽性至于命的民族,一个最早理性觉醒的民族,所以中国远在上古时期,就渐渐隐退了“上帝”一类宗教信仰,发展出一种本于天道法则的礼教,以此建立信仰信念,教化天下人民。唐虞时期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尚书·皋陶谟》), 帝舜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命夔“典乐,教胄子”,以此平治天下,使人性“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就是这样的礼教。特别是发展到周代,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乐教化天下,礼教不仅成了中国文化政治教化的重要形式,而且成了国家民族建立信仰信念的最高知觉形式与性命之理。
那么,中国的礼教与西方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礼教者,以理为教者也。宗教者,以宗为教者也。不论是礼教,还是宗教,哪怕是原始宗教,都牵涉到形而上学存在,牵涉哲学本体论问题,不论礼教、宗教都是这样,不过图腾、巫术一类原始宗教之形上存在,文化形态较为低级而已。中国的礼教,乃是以天道义理设教的。 故曰“礼者,理也”(《礼记·经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礼即天理也;乐乃天乐也。大音乐的旋律同天地的旋律一起和谐,大礼的升降旋转合于天地的节凑。这就是中国的礼教。它是一种道体形而上学,是以天理最高存在设教的。而西方宗教,乃是以上帝的神性形而上学为天下万物之宗而设教的。西方宗教中 “上帝”,最初的耶和华,本是原于宗教神话,后来与希腊哲学相结合,也就变为“逻格斯”与上帝同在,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存在了,但就其神圣本质而言,仍属于神性形而上学存在。即使现代神学把“上帝”解释为存在的根据,解释为“存在的存在”,它也没有脱离神性形而上学本质。中国文化以天道义理设教,虽然讲“道”也以“至精、至神、至妙”形容它的存在,如《易传》讲“阴阳不测之谓神”;“寂然不动”而为“天下至神”(《系辞上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等,但不管怎样至神至妙、变化莫测,它仍然是“道”的存在,是天道义理的存在;即使讲“圣人以神道设教”(《彖上传》),它也是天道四时不忒存在,真实无妄之理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的价值设定。故孔子说:“知变化之道,知其神之所为乎!”(《系辞上传》引);宋儒明道更讲“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所以,中国礼教不同于西方宗教者,就在于它以天道的真实无妄之理为教,而不是像西方宗教那样以“上帝”的价值设定而为宗教信仰。
中国自古是一个本于天的民族。以天为本,就是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为万物本原,为生命源头与性命之理存在。故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以天为信仰,以天道义理存在为最高信仰。这种信仰是不同于西方以“上帝”的宗教信仰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发展中,虽然各原始氏族部落的信仰一直是存在着低级形态的宗教、图腾、巫术,但对“天”或“天道”的信仰,从伏羲时代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开始,则一直是信仰天道法则的。它发展到唐虞时期,天道法则的形而上学思维,已经达到“惟精惟一”的高度;即使殷人尚鬼神,在哲学上也是以“惟和惟一”(《尚书·咸有一德》)思考天下万物之理的。发展到殷周之际,虽然仍然存在着“皇矣上帝”“昊昊上帝”的存在,但那不过是皇皇光明的上天存在。故汉代儒家解释《诗》《书》中的“上帝”,无不曰“天也”。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周人礼教郊祭天地,以祖配之,就是报谢天地本始存在;而“以祖配之”,就是将祖先神提升到祖先所出神高度,提升到皓肝光明的“昊昊上帝”存在。如果说它还带有神性形而上学性质,而《诗经》讲“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纯,假以溢我”(《周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刑仪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则已是以纯粹道德获得天道命令与政治法则了。特别是晚周隐退“上帝”代之“道”的法则以后,如老子讲“道”的存在“象帝之先”(《老子》第 4 章),庄子讲“道”的“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师》),其为“天”的存在,其为“天道”或“天理”,已成中国文化最高形而上学存在了。三代之后,中国文化中虽然仍然有鬼神的存在及其信仰信念,特别是在民间,但就中国文化的主流而言,就国家政治教化而言,鬼神存在及其信仰信念,已经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是礼教文化,而不是上帝鬼神的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不仅儒家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不语怪力乱神” 之事 (《论语·述而》),即使道家也是不相信鬼神的,老子讲“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 60章),就是这样。晚周虽有墨子尚鬼神,试图恢复宗教,汉代以后也有道教兴起与佛教传入,但从中国文化主流来说,占统治地位的基本上不是宗教,而是是礼教。尽管它在不同时期也有兴废,但解决信仰信念一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主要是靠礼教,靠天道形而上学的最高存在,靠这个真实无妄之理的存在,而不是像西方宗教文化那样依赖“上帝”的价值设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这道也”(《中庸》第20章);“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即客观实在,即实有是理,即真实无妄,即天道法则之本然存在。故程子说:“无妄之谓诚”(《河南程氏遗书》卷6);故朱子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第20章注)。张子更说:“诚,故信”(《正蒙·天道篇》);“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正蒙·诚明篇》)。此即《大学》所讲“知至而意诚”者也。有此无妄之理,人明之诚之,以为性命之理,才能各正性命,建立信仰信念及道德精神世界,才能不虚不妄。故伊川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 1)没有天的诚,何来人的诚?此中国礼教不同于西方宗教形上本体论者也。不懂中国文化“天道”的真实无妄之理,不懂中国以天道义理设教,妄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无知也。
礼教与宗教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们形而上学本质,而且它们所建立的人性论基础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礼教以天道义理为教,是承认人的先天道德本性的,其为教理是立于性善基础上的。《周易》文王《乾》卦辞,讲“元亨利贞”四德,讲天道本体的美好大用,周公爻辞九三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设定人性之美好而建立道德修养之教的。它是作《易》之本义,亦是周公制礼作乐,教化天下的心性本体论根据。中国文化讲人的气质之性,虽然承认有阴阳、动静、清浊、善恶,但讲人的良知,讲先天道德本性,则是纯粹至善的。因为这种本性是天生的,是皇天上帝赋予人的。《尚书》讲“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汤诰》),即指此本性也。衷,善也。皇天上帝,降衷于民,即上天赋予人的永恒道德本性也。《诗经》讲“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孟子讲人有“非外烁”的“仁义礼智”之性,以及后儒王阳明讲“天理良知”,皆是承认人之先天道德本性。先天道德本性乃是人最为本质的规定性,是人区别动物的本质差别,尽管这种差别很小,用孟子的话说,是人别于动物的“几希”存在,但是,正是人有此本质的规定性,才能追求美好事物,追求信仰和信念,追求道德精神世界;有道德本性,才可以教化,故明之诚之,才可以成圣成哲,成为尧舜。中国礼教就是建立在此种性善论基础上的。然有西方宗教,并不是以性善论而设的,而是立于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基督教就是这样。若以基督教教所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是有神性的,属于性善论的,但它讲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让其看管伊甸园,因其受了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又是犯有原罪的,因此基督教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恶的,是充满贪婪、物欲、情欲一类邪恶本质的。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这种性恶论基础上立教,拯救人性罪恶的。
由于礼教与宗教所建立的人性论基础不同,因此它们的教义宗旨也是各异的。由于中国礼教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承认人是有“仁义礼智”的先天道德本性的,所以其立教主旨就是以“仁义礼智”教化天下。《礼记》所说乐正掌国子之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就是这种礼教教义与主旨。 以《诗》《书》《礼》《乐》为教,就是以仁义礼智为教。《周礼》讲以乐德教国子,使之“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使之培养起“兴、道、讽、诵、言、语”的能力(《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使之懂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宗伯·大师》)的诗义与境界,其为礼乐教化,也是以人的道德本性为基础的;没有这种心性基础,礼乐是不可能以此立教,造就人才,使之成为有道德、有学问的存在者的。此即中国礼教立于性善建立自己的教义主旨者也。即使它承认人的气质之性有阴阳、动静、清浊、善恶,持此心性有陷入非理性的时候,但礼教也是教之以仁义礼智,使人去掉非理性,归于理性的,使天下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皆有一颗仁爱之心,惟此,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此即孔子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者也。由此可知中国礼教是如何立于性善论,建立自己的教义与主旨了。而西方基督教是以性恶论立教的,所以它最为根本的教义,就是拯救人的罪恶。而人信仰上帝、接近上帝,虽然有追求美好存在之意义,但主要还是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既然人性本质是恶的,所以不管怎样对其教化,人也成不了尧舜,成不了圣贤明哲,除了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成为上帝或上帝之子的存在。既然人性是恶的,所以不管西方17世纪、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怎样把人性之恶合理化,他们所设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终是不能实现的;同样,既然人性是恶的,不管西方19世纪思想家怎样试图将基督教天国理想搬到世俗社会中来,所设计种种乌托邦世界,终究也是不能实现。因为所涉及的理想社会再美好,只要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私、贪婪、争斗、物欲、情欲一类邪恶本质基础上,最后会被它所构成邪恶力量破坏掉。
礼教与宗教的教化形式也是不同的。礼教教化内容与形式,是极为广泛的,它并不像宗教那样只是通过遵守教规、过礼拜、唱颂神诗、默想、念经、祈祷、修道等形式与上帝或神的存在相交通,达到对教徒施行教化,建立宗教信仰的目的。礼乐之教,从车、服、冠、冕之制,到冠、昏、丧、祭之礼,无不有礼教要求,尽管这种要求夏商周各代是不同的,但是,大从班朝治军、涖官行法,小到乡饮乡射、民间细行,其为礼教之数,皆有明确规定。故以“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第27章)。不管其礼数怎样繁,规范怎样细,但它最根本的要义,核心的内容,则在于人性的教化。故曰“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所以制定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之礼,所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皆在于“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自然,这也不是说礼教只是停留于社会教化层次,而不能达于形上世界。不是的。若是那样,也就不能建立最高的信仰信念了。礼教不仅在 “钟鼓喤喤, 磬管将将”(《《诗经·周颂·执竞》》;“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诗经·周颂·有瞽》),郊祭天帝的礼乐中,祭神若神在,与天帝祖先神相交通,更为普遍的形式是通过道德修养,知觉天道至精至神的存在,获得信仰信念与性命之理的。周子讲 “主静立人极”(《太极图说》);陈白沙讲“静中养出端倪”(《与贺克恭黄门》);以及朱子讲“今而后,乃知宇宙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答张敬夫》)等,就是讲的通过道德修养获得道德精神境界,获得最高知觉主宰与性命之理,而建立起理性自觉之信仰信念的。
最后,由于礼教和宗教的形而上学存在及人性论基础不同,它们所引申出的伦理道德精神,也是各不相同的。由于西方宗教基于性恶论,而且信教还要交恕罪券,所以由新教伦理引申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把赚钱看作是天职。而中国礼教以天道立教,而且是立于性善论基础上的,所以它所引出的伦理道德精神,不是视赚钱为天职,而是以养民为天职。 “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天子养万民,企业家职工,皆是天命所在,皆是“天工人其代之”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要求的!因此,中国礼教伦理道德精神,要求有国有天下者,代天理民,不是藏天下于筐箩,而是藏天下于天下;要求企业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养好你的职工,为天下人创造更多更好的服务。此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也。礼教者,经天地之大经,立人道之大本者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庄不敬”(《礼记·曲礼》);夷夏之分,人兽之别,以及君子异于小人,全部在于此,礼教岂是可以废的?天秩即人伦,天命即人性大源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显诸仁,藏诸用,“缘仁制礼,则仁体也,礼用也;仁以行礼,则礼体也,仁用也”。故整个礼教,乃“仁之经纬斯为礼”(王船山《‘礼记’章句序》),全部贯通一个“仁”字,所谓礼教“吃人”云云,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礼记》讲命“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王制》),乃在于提高人的理性,使其不至于陷入非理性为非作歹,此乃人道之正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 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礼记·乐记》)。唯礼以教之,乐以化之,人才能贞正性命之理!中国的礼教,从根本上说,乃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人性教典。中国自古即是礼仪之邦,言谈举止,动静语默,皆有礼数,皆有规范,最高的信仰信念,也是赖此建立的。中国的礼教,虽不是宗教,然却有宗教之大用。然而发展到今天,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流行,富强之说、功利之求、算计之谋,亦纷纷籍籍,争奇斗巧,成了最为时髦的东西。以知物为哲代替知人为哲,小知小识代替天道性命之理,于是遂使天下心失良知,性无主宰,以为这些功利之学就是知识,就是学问,就是高明的理论,就是最好的主义,于是相争以利,相倾以势,相高以技,功名利禄之求嚣嚣于天下,使天下耳目为之眩瞀,精神为之恍惚,信仰信念莫知其终,莫知其所是矣!发展到今天,更是梦想代替理想,金钱代替信仰,以至于连吃饭、喝汤、如厕一类行为,也要请西方教官来培训!天理良知丧失如此,礼教文明不复存在如此,一个以天为本,以天道义理为最高信仰的民族,以至于被人指责为无信仰,岂不哀哉!因此,恢复礼教,乃是恢复仁义礼智的人性教典,而“高呼还我礼义之邦”乃是重建华夏文明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