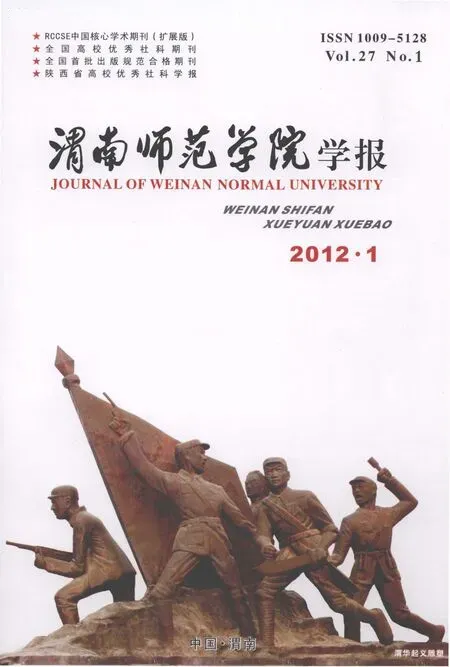司马迁历史观的时间解读
2012-03-20崔康柱
崔康柱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司马迁历史观的时间解读
崔康柱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从时间的路径进入司马迁的思想世界,就会发现时间是社会的二元结构——天与人之间的中介。时间的变化,既是天的变化律,也是人的变化律,二者的交互作用,就构成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改朝换代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任何一次“革命”都在“承弊易变”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革命”的时变律就是“三五之变”。
司马迁;中介;革命;三五之变;历史观
司马迁的《史记》首先是一部雄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历史著作。这里的“历史著作”有两层意思:一是司马迁根据他所考证的资料所描述的西汉以前三千年人们以政治为核心的生活活动史,二是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即历史哲学。后者是从前者概括出来的,是司马迁写作《史记》要表达的主旨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又主要是通过前者表达出来的。同司马谈意欲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不同,经过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表达以“变”为核心的历史观。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司马迁意识到:古今之变的动因和规律都是复杂的。新的认识需要一套新的概念来表达,由于历史的局限,司马迁感觉到了概念的贫乏,“我欲著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在当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把司马迁历史哲学从历史叙述中解读出来的条件已经具备。但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的力作至今还未出现。本文认为:问题出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能指导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在对《史记》一书的研究中逐渐显现的。本文认为:司马迁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是时间。以时间为线索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就是本文的旨归。
天与人——司马迁理解的社会二元结构
读《史记》,不难在《史记》一书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例如,司马迁一方面认为汉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称刘邦“非大圣孰能当次受命而帝者乎?”;另一方面又斥项羽“天亡我”为缪。一方面认为刘邦称帝是上天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借刘邦之口指出,刘邦所以得天下,是能任用萧何、张良、韩信等人才的结果。一方面在《本纪》、《世家》中把一个家族的得天下、封诸侯,说成是累世积德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伯夷列传》中又对“天道无亲,常施善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研究《史记》的学者,或者依据前者断定,司马迁认为“天命神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第一推动力”;[1]146或者依据后者,认为司马迁是“人性论的历史观”,人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因素。[2]285由于《史记》本身对天的强调和对人的强调都很充分,任何从一元论的角度对司马迁历史观的概括在理论上都难以两全。其实,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考,必须破除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例:一方面把经济看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把各个个人意志的合力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当然,更科学的表述是把历史描述为人合规律性(经济)与合目的性(意志)相统一的活动。司马迁当然做不到这一点,他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上,只能做到对社会历史的二元结构理解。
历史是一条长河,河床是经济,那奔腾不息的河流则是以政治为核心的人们的生活活动。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前,历史学家看到的不是那决定河流形状和趋势的河床,而是着眼于河流本身,司马迁也不例外,占据《史记》中心地位的还是以王朝兴衰为纲的改朝换代史。表面看来,《史记》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叙述了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中的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活动。但历史哲学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叙述,它要追寻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为此,他就必须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道路,从历史中概括最抽象最单纯的概念,这也就是殷商以来各家各派所反复讨论的“天”和“人”。“天”和“人”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司马迁既在思想史中接受了这两个关键概念,又把撰著的目标定位为“成一家之言”,当然自有他的学术底气:一则天文历史是他的家传之学;再则他把天人放在“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考察,从而要在一个新的角度下,给天人以新的解释。天的概念,据张岱年先生考证,上古时有两重意义,一指有人格的上帝,一指与地相对的天空。[3]97在汉人眼里,犹人有形体和精神,天空是天的形体,人格神是天的意志,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持这一观点,但在具体的解释中,司马迁却与董仲舒大异其趣,本文将在下面说明。人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更为复杂,中国哲学史上对人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秦,“人”和“民”是相对的,有着鲜明的阶级分野,只有君主、诸侯、大夫、士和统治者家族的人才称作人。春秋时期周内史叔兴所说的“吉凶由人”,这里的“人”就指的是统治者,儒家把“仁”“义”“礼”“智”当做人和禽兽分野的标准,显然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是上流社会的统治者,至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民”,到了秦始皇当政时期还被称为“黔首”。直到西汉的董仲舒,仍然赤裸裸的把“民”排除在“人”之外:“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董仲舒在论及人性的时候,明确的把民排除在外:“斗莦之性,不可以明性”。[4]212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统统都看做“人”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惟给董仲舒所说的“人”做传,而且首次把农工商虞纳入“人”的范围,为他们在神圣的历史中树碑立传。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人”就是所有在历史舞台上一展风采的人。司马迁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真正有民主意识的人,单是他扩大人的范围,把民称作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而把人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始因和动因之一,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据可以考察的史料推测,是从《周易》开始的,春秋战国以来成为哲学的主题,直至西汉汉武帝给思想界提出的任务还是“究天人之故”。这就是说“天”和“人”两个概念不是司马迁提出的,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也不是开始于司马迁,司马迁的贡献首先在于破除了一元独断论的传统思想,在历史哲学领域对天与人做了二元论的解释。他的《史记》一书考察的就是人能做什么和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当然天仍然是人的行事的基础和条件。在思想史上,从一元独断论到实践的唯物主义之间,二元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今人所以视《史记》中的天人之论为思想矛盾,乃在于所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一元论的思想,总要在天和人之间选择一个第一原因,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而在司马迁看来,社会就是天和人构成的二维结构,它们是历史发生的两个始因。司马迁叙事从黄帝开始,天是黄帝成为天子的始因,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是上天之子;而黄帝所以能开五帝之先,又是他“习用干戈”武力征伐的结果,他自己的“行事”是他成为天子的又一原因。天和人也是历史发展的两个动因。例如,“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另一方面,也是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于内”的结果。
天人之际与历史时间
天和人是社会政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司马迁的著述目的是考察天和人怎样相互作用而导致了社会历史的“古今之变”,从而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做出自成一家的概括。那么,在社会历史中天和人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周易》特别是《易传》就成了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论的总原则。
《周易》一书给后世思想史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天人之间的中介体系,即六十四卦的卦象,殷周之际的人就是通过卦象理解天意决定人事的。卦象分阴爻和阳爻,因此这个中介亦可以简称为“阴阳”,战国以来的“五行”说就是按《周易》的这一思路的发展。《易传》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就是对《易》的中介地位的说明。《史记》中作为天人中介的符号是很多的,据陈桐生检索,包括了星象、祥瑞灾异、预言、卜筮、梦异等,司马迁写《史记》在材料上本来就要“整齐百家杂言”,归纳这些迷信思想本来是不奇怪的,当然这也是他思想不纯的反映。但这些都不是司马迁自己的一家之言。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司马迁没有摆脱传统影响的地方,而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使用了哪些新的而且是“整齐”全部材料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易传》对司马迁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周易》。同《周易》不同,《易传》把殷周以来天人中介的理论从神学发展为形而上学。司马迁父子研究《史记》的方法论原则是“正易传”。《易传》的思想方法就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5]570“时变”,既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又是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5]226“时变”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就体现为“化成”、“革命”。可见,时变才是天人之间最主要的中介。《易传》的这种时间观就成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总的方法论原则。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司马迁在历数从《左传》到董仲舒推春秋义的所有著作后评论说:“儒者断其义,驰者骋其词,不务综其始终;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意思很明显,要考察王朝的“始”和“终”的“要”旨,就要把王朝的行事放到时间的框架内观察其由盛到衰的变化,然而历人、数家和谱谍之人或仅仅记载年月,敝于天而不知人;儒者、驰者限于人而不知天,司马迁则要在年表的形式中,以时间为纲,总括天人,叙述王朝的兴衰大旨。司马迁要记述西汉以上三千年的历史,必先制表,作为叙述的纲目,表也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旨归。
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说的时间决非仅仅是历人所取的年月日,而是集年月、义理、神运和世谥于一体的历史时间。时间问题向来是哲学中的一个难题:“时间是什么?无人问我时,我很明白;每当有人问我而我想要解释一番,却茫然了。”[6]115在近代自然科学视野中,真实的数学时间,以其本性,是均匀流逝着的,与任何外在于时间的东西无关。但在中国的哲人眼里,作为年、月、日、时辰计量单位的时间从来都不是纯客观时间,而是天人关系中的时间,或曰“关系性时间”。华夏民族是中华大地最早进入农耕生产的地区,对年的确认十分重要,故时间的重要性随年月日而递减,而不同于西方日月年的时间价值递减率。上古结绳而治恐怕首先是计时间的,“西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及确定一年的春天,以便适时播种,以后通过观察天象,确定了正朔和闰余。由于直到司马迁的时代天都保持着对人事的至上崇高性、神秘性和制约性,所以这个天文时间又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同时是一种人文时间。“江畔何年初照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一种对时间始源的追问,这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司马迁对此没有兴趣。他的“原始察终”,固然也是一个时间的始和终的问题,但却是历史的和特定王朝的始和终,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人文时间具体地说就是历史时间。在《史记》中,人的历史在时间中,因为时间来自于至高无上的天,司马迁在时间的框架里叙述了三千年历史;同时时间也在人的历史之中,人确定王朝年月的正朔,人也决定了王朝历史的始和终之间的时间长度和改朝换代的节奏。
时间意味着变化,历史时间意味着人的历史有始有终,一个王朝是这样,整个历史也是这样,“始终古今,深察时变”。承认这一点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尽管“《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提出了“变”的哲学世界观,但要把这一世界观落实到历史领域却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问题,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认为改朝换代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法则,即使圣明如五帝三王,也不能保证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在司马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据说孔子为《易》作《十翼》阐发了“变易”的思想。但在《论语》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本人对社会的变异持批判态度:“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28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之士研究“天人之故”,也是希望汉家天下“传之亡穷”。即使对时间性的历史著作《春秋》,今文经学也要超越时间,把它形上化:“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8]1认为孔子的目的不是历史叙事,而在于阐发微言大义:“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8]2司马迁以后的古代史学家一般都只做断代史,批评前朝为本朝提供借鉴,还没有人敢于“通古今之变”的。
历史时间的概念为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依据不同的时间单位(如日、月、年……千年……)加以分割,与此相承接,利科尔把历史时间划分为“在时性”、“历史性”和“深层暂存性”。其中的“历史性”描述为在重复中时间的延伸。[9]210可见历史时间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方向上是可以弯曲的,在节奏上是有快慢的,总之时间作为历史的存在方式,是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用科学的时间去衡量,更不能把基督教目的论的时间作为唯一的历史时间。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变异的历史观建立在一维时间观上,时间的方向无法逆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建立在三统论和五德说的基础上,是历史循环论和非历史的观点。[1]147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一维时间观是近代的观念,是一种科学时间观,而不是历史时间。在历史领域内,如同利科尔所说,时间是可以在循环中延伸的。司马迁不但描述了改朝换代的始终之变,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统循环,但在不同时期“忠”、“敬”、“文”的含义是有变化的,例如,周的文治和秦的文治就是不同的。司马迁不但描述了三统循环中政治体制具体的变化,还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世”,表示历史在循环中的时间延伸,怎么能说司马迁的历史观是非历史的观点呢?
在时间中展开的历史阐释
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史中时间现象的讨论都放在自然哲学里,与空间并列为自然过程的规定性。他认为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时间和应用于历史科学的时间是不同的,为此他提出了“时间性的概念”来解释历史现象,当然他是要在时间的地平线上解释此在的生存意义,即存在。而在中国文化中,哲人们早就意识到了人的生活的时间性,需要从历史时间的角度解释人的历史的规律和意义,司马迁就是这样的历史哲学家。
历史是人的历史。考察历史的发展动因和规律,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各个个人的历史活动。不是每个人的活动都具有历史性的,判断那些人属于历史人物,其标准是历史时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活动仅仅是自给自足的重复性活动,那么即使他活了一百岁,历史时间也等于零。但如果他的生活是创造性的活动,有超出维持简单的生命延续的意义,那么在他的生命活动中也就体现出了历史时间,即他使人类的某一项活动发展了,从而进入了历史。而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是创造性的,关键取决于他对未来的态度。不错,每个人生命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都要满足自己衣食住这些基本的需要,但有一部分人却能在满足基本需要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作为未来的理想,投入当下的生活当中,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以秦汉之际为例,项羽欲取秦始皇而代之,刘邦欲成为另一个秦始皇,陈涉贪求富贵,结果都成为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可见,历史时间作为人的历史性活动的时间,本身是有一定方向和长度的时间。从方向上看,个人对时间的领会是从未来到现在,而历史事件本身则是从现在发展到未来,方向正好是相反的。从长度上看,尽管由于个人提出的理想有大小远近的不同,属于个人的历史时间也就不同,例如孔子提出的人文理想,至今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孔子的历史时间就很长。但一般来说,历史人物只是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意义,属于短时段的历史。
一个王朝的兴衰属于中时段的历史。司马迁“稽其兴坏成败之理”,就是考察王朝盛衰的规律。在司马迁看来,王朝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终也可以归结为“人”和“天”两个方面。从人的方面来说,又包括人性和文化两个方面。贪生悲死,好逸恶劳,是人的自然天性,它当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给百姓以谋生存得富贵的承诺,自己又励精图治,这样就可以动员百姓夺取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在取得天下以后,率先“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有的甚至“肆意极乐”。来自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影响到普通百姓,欲望迅速膨胀,贫富差别增大,各种矛盾潜滋暗长,又会引发新的改朝换代。文化属于对人的欲望的制约力量,“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股指礼仪养人之欲”,礼仪、刑罚等文化都是为了制约人的“欲”、“忿”、“争”而制定的。但实施这些政治措施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做践行礼仪的典范,必须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否则,自己“肆意极欲”,而让中间层次的官吏守“礼”,让下层的老百姓守“法”,那一个王朝土崩瓦解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德治”的核心就是用“仁”的道德标准对君主加以约束,尽管这是自律而非他律,难以约束在和平年代里最高统治者日益膨胀的情欲,但在封建社会里这也是文化所唯一能够起的作用。为什么国之将兴,贤人进,佞人退?那是因为开国之君本身都是贤能之人,为了得天下,他们需要贤能之人和他们一起对老百姓“立德”、“立功”,这时候,他们还不能发展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什么国之将亡,贤人退,佞人进?那是因为取得了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当初的对手已不复存在,又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欲望开始膨胀了,贤人作为他们腐败的抗拒力量当然要排除,而佞人作为他们腐败的同谋,而得到宠幸。由于统治者从贤明到腐败的演变同人的自然情欲的发展趋势国家的兴起和没落是同步的,呈现出时间性的节奏变化,个中的规律,司马迁归之于天。前文已经说过,汉人把天分为形和神两部分,董仲舒用形去附会天意,具体地说,天有阴阳、五行、四时,这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王者行政应法天以治人,王道之三纲,合于天地之阴阳;王者庆赏罚刑,合于春夏秋冬。司马迁走着相反的道路,把神秘的天意规律化,具体地说,就是把天的变易规律化,把规律时间化。王朝的兴衰变化从表面看是统治者没有实行德治,缺乏道德自律,从实质看,是人性在和平年代因情欲蜕化使一定的文化丧失约束力的结果,而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来看则是在时间性的三五循环中天命的转移。司马迁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为:“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记,三记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这里的“三十岁一小变”、“五百载大变”,都属于中时段的历史。应该指出,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新王朝的诞生,需要一个家族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在旧王朝的母体内才能孕育成熟,脱颖而出;而一个旧王朝从兴盛到腐败也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就呈现出改朝换代的节奏性。司马迁用天运来概括尽管是不科学的,却也符合王朝变革的实际。
长时段的历史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三大变”、“三记”。根据《史记》的描述,西汉以前的历史,已经历了三次大变,司马迁分别用“上古”、“中古”和“近世”做以区分。五帝时期是第一时期,这是神人统治的时期,从黄帝到尧舜。都既是人又是神。例如,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而制义”,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三王之时是第二大变,这是英雄统治的时代。禹虽有高贵的血统,但他之所以践天子位,乃是因为“劳心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治水有功的结果。契亦是贵族出身,佐禹治水有功,到了成汤伐暴安民,平定海内;任用贤人,德及禽兽。周后稷善耕农,“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后世复修后稷之业,家族势力得以扩大,至西伯和太子发终于推翻商朝,建立西周政权。这时期的统治者有这样一些特点:出身贵族,累世建立功勋,德洽百姓,用武力夺取政权。秦汉以来进入了第三个时期,代表人物就是秦始皇和汉高祖。司马迁对秦始皇出身的描述是有深意的。秦始皇没有高贵的血统,刘邦则是普通平民出身。他们都是凭着任用人才,自强不息,乘势而起,以狡智和武力夺取天下。由于这三个时期政权的性质不同,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同,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文化也各不相同。五帝时期当属中国的原始社会,国家实际上是部落联盟,政权交接实行禅让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是在向自然的学习中改造自然的,法天则地,适时播种,驯化动物,疏通河道,开凿道路,制造器具等,就是当时的主要文化创造。在虞舜任命的二十二个官吏中,大部分都是掌管物质生产的,这些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三王之时已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建立家天下了,此时当属中国的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大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小奴隶主才有条件聚集力量夺取最高权力。这时的文化有一个“忠”、“敬”、“文”的演进过程。五帝时期的文化当属于“忠”,禹延续了这种文化,结果败给了殷商。商统治者不从夏王朝的腐败上找原因,而是一味的神话自己的政权,宣扬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思想,这就是“敬”。周王朝制定了等级森严的“礼”,把血缘关系中的高低尊卑关系扩大为国家中的天子和诸侯、君和臣的关系中;同时,又用“仁”、“德”的道德规范来制约君主,这就是文治。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人治社会,执掌权柄的是既没有高贵的血统,又没有重大功德的平民,在经过百家争鸣的激烈争辩之后,统治者选择了法家的思想,对来自社会下层的反抗,还是刑法最为有效,儒家的德治思想仅仅是对法的约束,使之不至于严酷到“法”逼民反的程度。由此可见,司马迁描述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三大变,绝不是董仲舒所说的循环,也绝不是表面上的“改正朔,易服色”那么简单。那种认为司马迁持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也是没有认真考察司马迁所叙述的“行事”古今之变的结果。
司马迁历史观的一家之言
梁启超指出:司马迁“著书最大的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言’乃借史的形式发表尔”。[10]3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建立在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基础上的,司马迁不但吸纳了“异传”中经过他考证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在不同的语境中引用了各家的“杂语”,特别是今古文经学的观点。由于司马迁是在整合中超越并借史的形式发表,我们研究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就不能拘泥于司马迁所引用的各家言论,而要在把握司马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他的历史叙述中解读。
司马迁的研究方法就是《易传》中的“时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天地万物的损益盈虚,是与时间的变化同步的。《易传》是借天地之文言人间之事的。继承了《易传》方法论原则的司马迁,把时间视为天人共同的变化规律,即天人以时间为中介“偕行”。社会历史的中轴线——改朝换代,既是顺乎天的时变,也是顺乎人的时变。改朝换代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司马迁历史观的第一个原理。改朝换代之所以是必然的,从天的方面来看,是年的“闰余”要求规律性的改正朔;从政的角度看是一个王朝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弊政,其文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在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也产生了恶劣的国民性。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新王朝“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弊通变”。这是司马迁历史观的第二个原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呈现为政治文化在继承中的创新,例如从神治时期的物质文化到英雄执政时期的礼乐文化再到人治时期的法治文化,就是文化的线性发展过程,这是司马迁历史观的第三个原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才的作用也越来越彰显出来。神人生而知之,法天则地,人才起作用的空间很小;英雄功业卓著,他们的地位是历史的形成的,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礼乐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就是崇拜仪式,人才对取得政权的作用有限;而到了人治的时代,政权的取得和巩固就需要大批人才的襄助。人都是有缺点的,皇帝也不例外,需要大批各有所长的人才,形成一个领导集体,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成功,秦王政和刘邦都是得人才而得天下的。有人把人治和法制对立体来,从中国历史来看,其实是不对的,人治是和神治、英雄政治相对的,到了人治时期必须在文化上实行民主和法制。人才要发挥作用,君王就须从善如流,这是古代的民主。由于这种民主是没有对君王的约束作用的,因而只能叫开明政治,这样没有民主的法制是随时可以发展为暴政或多欲政治的,这是司马迁对秦汉政治的批评,我们不难从这里推出司马迁历史观的第四个结论。
“承弊通变”就是“革命”。革命是消除弊政,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是大批的人才从社会底层涌现出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描述的西汉之前三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史。《史记》就是一部“革命”的壮美诗篇。
[1]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2]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张岱年.释“天”“道”“气”“理”“则”[C]//中国哲学范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山东:齐鲁书社,1979.
[6]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5.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
[9]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0]韩兆琦,周旻.史记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Time Implication of Sima Qian’s Conception of History
CUI Kang-zhu
(School of Humanities,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From the path of time,this paper shows that in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time is the medium between the heaven and the people in the society.The change of time is the change of the heaven and also the change of the peopl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leads to the change of the dynasties which is realized by revolution.Any revolu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Any revolution is the change of time.
Sima Qian;medium;revolution;the change of time;conception of history
I206
A
1009—5128(2012)01—0033—06
2011—07—12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09JK074)
崔康柱(1954—),男,陕西西安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记研究。
【责任编辑 詹歆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