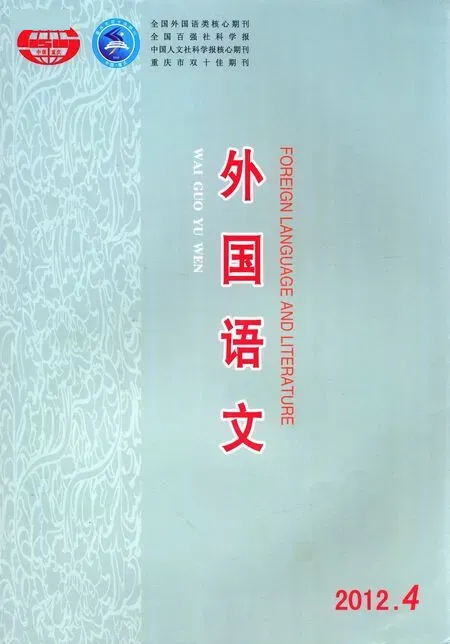约翰·斯坦贝克的旅行书写
2012-03-20田俊武
田俊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 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一、引言
在美国文学史上,约翰·斯坦贝克曾经是一位与福克纳和海明威齐名的作家(Fontenrose,1964:1),也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关于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近几十年来已经有各种视角的评论,例如,关于他的作品中的社会抗议主题、生态主题、道德伦理主题等。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评论界对斯坦贝克的旅行书写的论述却少得可怜。这对于一生都在旅行和写作的斯坦贝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研究的缺憾。事实上,斯坦贝克一生丰富的旅行阅历,不仅使他创作出《科茨海日志》、《俄罗斯纪行》和《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等脍炙人口的非小说类旅行文学作品,而且旅行在他的主要小说中也成了一个或隐或显的母题。
二、斯坦贝克的旅行生涯
杰克逊·本森在评价斯坦贝克时这样说过:斯坦贝克“本质上是一个记者——他喜欢旅行”(Benson,1984:793)。斯坦贝克从小就对旅行怀着渴望,20岁时他想效法心目中的英雄杰克·伦敦穿越太平洋,但是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并没有实现。1925年秋天,斯坦贝克进行了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乘轮船从旧金山出发,穿越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到达纽约。如同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莲·斯坦贝克所说的那样:“约翰本来可以像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一样去巴黎,但他没有钱支付旅费。”在纽约,他得到了第一个有薪水的记者职位,就是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主办的日报《美国》撰写报道。关于这份工作,斯坦贝克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记者怎么当。我想他们每周付给我25美元可是赔本了。他们总是让我去采访发生在昆斯与布鲁克林的故事,而我总是爱迷路,几个小时都回不来。当一家人拒绝我照像的时候,我也学不会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偷偷抓拍。而且我也总是情感用事,为保留题材而损害了整个故事。”(Steinbeck,1953:26-27)斯坦贝克坚持干这份工作,因为他想给该报社的一位女孩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过斯坦贝克并没有与那位报社女孩发展出一段恋情,在他被报社解聘的前两天,那女孩与一位来自中西部的银行家结婚了。斯坦贝克只得打道回府,靠在轮船上打工,一路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这次旅行虽然无果而终,却成为他一生通过旅行来叙事的序曲。
斯坦贝克第二次重要的旅行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那时候,无论是作家还是人民,都在经受某种困厄。从作家本人来说,他正在为写作小说《俄克拉荷马人》找不到好的切入点而苦恼。从社会处境来看,1937年秋俄克拉荷马州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尘暴。尘暴所到之处,溪水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萎,牲畜渴死。尘暴的袭击给美国的农牧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俄克拉何马、德克萨斯、堪萨斯等州的农民被迫到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逃难。为了摆脱自己写作的苦恼,也为了表现这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学上已经崭露头角的斯坦贝克决定亲自跟随俄克拉荷马州的农场工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实地考察尘暴对农业工人造成的影响。他跟工人们一起住在“胡佛村”宿营地,并和他们一起到大农场主的田地里摘水果和棉花。在漫长的旅途中,斯坦贝克看到和经历到的情景使他非常震惊。他在给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伊利莎白·欧迪斯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有一个帐篷里,隔离了20个出天花的人,而同一个帐篷里,这个星期有两个妇女要生孩子……州政府和县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提供,因为他们是外来人。但是,没有这些外来人,州里的庄稼怎么收获?”(Elaine,1975:158)在这次跟俄克拉荷马州农业工人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旅行途中,斯坦贝克如实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终于在1939年发表了震惊美国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
斯坦贝克第三次重要的旅行是与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联合进行的科茨海旅行,时间是在1940年3月。当时,斯坦贝克正因为《愤怒的葡萄》给他带来的盛名而烦恼不已。全球都在希望这位贫苦大众的编年史家再创作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批评家也寄希望于这位“普罗”作家回归30年代的主题,希望再听到振聋发聩之声。而斯坦贝克从不愿意重复自己旧有的风格和主题,他需要逃避民众和评论界的期望。里基茨也面临着人生的问题,那就是与蒙特雷湾一个有夫之妇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他们都愿意通过一次科学和文学之旅来摆脱双方面临的困厄。起初,他们打算乘卡车到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去旅行,但很快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从半岛的原始小路上去探索海湾的沿岸。于是他们决定乘船去。他们在蒙特雷湾租了一只沙丁鱼船Western Flyer号,除了斯坦贝克和里基茨外,船上还有其他四人,包括斯坦贝克的第一任妻子卡洛尔。斯坦贝克希望借这次探险之旅来修复他与妻子卡洛尔紧张的关系,但事与愿违,六周海上旅行结束以后,斯坦贝克就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分手了。不过这次海上之旅无论是对科学界还是文学界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行结束以后,斯坦贝克发表了著名的《科茨海日志》。
斯坦贝克第四次重要的旅行是俄罗斯之行,这次是跟美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柏一同前行的。像1940年与里基茨结伴进行的科茨海旅行一样,斯坦贝克与卡柏的这次俄罗斯旅行,一半是逃避生活与政治的困厄,一半是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首先,国内的政治环境使他倍感压抑。他在日记中写道:“举国被拖到愚蠢悬崖外坠入毁灭深渊莫此为甚。愿上帝保佑我们!……时代越来越复杂,已经到了人连自己的生命也看不到的地步,遑论要掌握它……所以,我继续写无关紧要的小说,小心地避开时事。”(席林格罗,2006:9)然而,虽然斯坦贝克想躲进小楼不关心窗外事,他却无法躲避来自家庭内部的烦恼。虽然斯坦贝克在第二任妻子葛雯的劝说下在纽约购买了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却在走下坡路。在外人面前,斯坦贝克仍然逞强地自诩跟葛雯的四年生活很美满,为自己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而骄傲,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与妻子的冲突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小说《任性的公共汽车》的创作。当《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赞助他到苏联旅行时,他愉快地接受了。他一是想摆脱家庭的烦恼,二是想看看铁幕后的俄国的真实现状。“我终于想到在俄国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写份详实的游记,一本旅游日志。还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它既是人人都感兴趣,也是我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席林格罗,2006:10)于是,在1947年7月31日,斯坦贝克与卡柏踏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开始了为期40天的俄罗斯旅行,其结果就是出版了著名的旅行文学日志《俄罗斯纪行》。
斯坦贝克最后一次重要旅行是在1960年9月23日开始的探索美国之旅,历时11个月,其结果就是1962年出版的《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像斯坦贝克的历次重要旅行一样,这次旅行也具有探索未知世界的目的,那就是探索当今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斯坦贝克在致朋友的信中毫不隐晦地告诉了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我打算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国家的情趣、味道与声音了。真正体会到这些感觉,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就这么决定!我要买辆载着一个小公寓的卡车,有点像拖着一间小屋子或小船的卡车,屋子里有床、炉子、书桌、冰箱、厕所——不是拖车,而是称为客车。我要一个人旅行,取道南部的公路往西走……将从这趟行程中得到我亟需的收获——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语言、观点、看法以及改变。”(Elaine,1975:666)与以往的坐轮船、汽车和飞机旅行不同,斯坦贝克在他人生的暮年决定亲自开汽车横越美国。出于纪念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作品《堂吉诃德》中的坐骑,斯坦贝克给自己的汽车命名为Rocinante。为了解除漫长旅途上的寂寞,斯坦贝克还决定带上自己心爱的伙伴,一只叫查利的法国鬃毛狗。斯坦贝克从纽约的萨格港出发,一路经过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最终在弗吉尼亚州结束了自己的旅行。
三、斯坦贝克的非小说旅行叙事
《科茨海日志》是斯坦贝克的第一部生动的旅行日志。像其他类似的旅行日记一样,这本书也首先叙述了作家到科茨海旅行的初衷、旅行的工具、随行人员以及沿途所见的科茨海风光。但是,不同于其他作家所写的旅行日志的是,这部日志不仅详细记录了作家和科学家里基茨采集海洋生物标本的过程,尤其是表现了斯坦贝克从里基茨和科学探险中所习得的哲学思想,那就是群体与个体以及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关系等。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了斯坦贝克后半生的创作。比如,斯坦贝克这样阐释非目的论思想:“非目的论思维将事件看作一种发展,一种表现,而不是结果。它们还将事件看作是一种对迫切需要的东西的有意识的接受,当然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非目的论思维主要关注的是生活‘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Steinbeck,1990:198)在斯坦贝克看来,非目的论将生活看作一个无限的整体,只有成为它的一部分,只有介入它,才能认知它。换句话说,斯坦贝克的意思是,非目的论是一种对生活的思考。它通过关注生活是什么,而不是回答为什么或应该怎样的问题,试图避免对拘谨和势利的道德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排斥,并且通过接受生活的方式,以实现对生活的热爱。另外,日志还夹叙夹议地阐释了人类在环境中的地位(Beegel,2006:26-28)以及旅行与归家(Tamm,2004:195)等母题。这些母题在斯坦贝克以后的写作中经常出现,“人类在环境中的地位”母题昭示着斯坦贝克在今后的创作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旅行与归家”母题则成为贯穿他小说创作始终的“旅行”母题的潜在注脚。
斯坦贝克赴苏联旅行并写作《俄罗斯纪行》的时候,正值冷战时期。对于苏联,美国国内的看法相当混乱。但在里基茨非目的论思想指导下,斯坦贝克对自己与卡柏的这次俄罗斯旅行还是设定了基本的立场,那就是避开历史脉络、政治立场和对时事的分析,只用文字和图片记录所见的现实场景。荒谬的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旅行者只能看到官员细心安排的景象,那就是莫斯科、基辅和第比利斯等橱窗城市的美好景象。但即使在这些繁荣的景象背后,斯坦贝克还是能看到战争对这个国家造成的破坏。例如斯坦贝克这样写斯大林格勒:“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大片瓦砾、破砖和已成粉状的灰泥,以及废墟中常见的怪异黑草。”在这场景之中,“几码外有个好像地鼠洞口似的小丘,每天一大早有个少女从洞里爬出来。”(斯坦贝克,2006:126-128)斯坦贝克从这迷茫恐惧的孩童目光中,看到了战争对这座城市造成的创伤。在俄罗斯,斯坦贝克发现团体控制着个体的创造力、思想和行为。“我们所到之处,所碰到的问题都有若干雷同之处,后来我们也逐渐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出自单一的来源。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学问题,都是根据他们在《真理报》所看到的文章。因此,过一阵子之后,他们还没有开口,我们就能预期到问题所在,因为他们立论根据的那些文章,我们已经了然于胸。”(斯坦贝克,2006:113)这种团体对个体灵魂的戕害现象,对斯坦贝克的思想触动很大。1949年,他在给朋友奥哈拉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深信一件事——个人孤寂的心灵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创造性的东西。两个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孩子,但我知道团体创作不出别的东西。团体不由个人思维支配是极为恐怖的破坏性原则。”(Elaine,1975:359)斯坦贝克的这次俄罗斯之行,也标志着他从20世纪30年代《愤怒的葡萄》所致力于探究的从“我”到“我们”逐渐转移到后来《伊甸之东》等小说中所关注的个体良知的一个重要阶段。
若从旅行文学的角度看,《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无疑是美国旅行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为了认识真实的美国,斯坦贝克刻意避开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而走偏僻的沙土路,因为这种路上有更多的自然景色,可以让他联想起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光。无奈美国领土如此之大,为了在较短的时间跨越美国,斯坦贝克也不得不将车开上美国第90号高速公路。事实上,斯坦贝克越往西行,他对大自然壮丽景色的描述也愈抒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在他心中交织得愈激烈,孩童时代社会的淳朴与当下美国的物质主义盛行对比使他愈加伤感。尤其当他来到自己的故乡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市,发现昔日的剧院居然更名为“约翰·斯坦贝克大剧院”的时候,他感到一股强烈的沮丧。他说:“托马斯·沃尔夫说得没错。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因为除了记忆中的樟脑丸外,家不再存在。”(斯坦贝克,2005:181)那么,整个路程下来,斯坦贝克发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呢?他在给出版社编辑派特·柯威奇的信中这样说:“我看到的是一种病态,一种浪费的疾病。大家都有欲望,却没有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建立起来的力量都像是存在尸体里的瓦斯。我不敢想像一旦瓦斯爆炸,会有什么结果。我一直觉得我们缺乏令人强壮的压力以及让人伟大的痛苦。现在,压力是负债,欲望是为了更多的物质玩意儿,痛苦是无聊。加上了时间的酝酿,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满之地。”(Elaine,1975:702)这种对美国现代荒原的认识,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烦恼的冬天》的主题。
四、斯坦贝克小说中的旅行母题
斯坦贝克一生的旅行生活和叙事也不可避免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旅行的烙印。不管是他的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具有一种显性和隐形相结合的旅行母题(journey motif)。显性主要体现在地域层面上的旅行,即作品中的人物通过徒步跋涉或乘坐某种交通工具,离开原来物质上困厄的地方,经历一系列陌生的旅途,到达另一个陌生化的地域;隐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旅行,即由于社会邪恶环境的阻遏和个人心理向度的张力,旅行者在经过一系列陌生的富有挑战性的事件后,有的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有的则陷入精神的迷宫而无法自拔。
在斯坦贝克表现旅行母题的小说中,《愤怒的葡萄》无疑是最杰出的一部。首先,它突出地描绘了作为旅行载体的汽车和公路。从小说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几乎每章都有汽车的叙述。斯坦贝克不仅侧面描写了汽车业在美国的发展以及汽车在美国旅行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浓墨叙述了约德一家驾车西行的过程:“那辆装载得过重的旧哈得逊车咯吱咯吱地哼叫着,在萨利索开上了公路,转向西去;太阳晒得刺眼。但是奥尔却在这混凝土的公路上加快了速度,因为压扁了的弹簧再也没有什么危险了。从萨利索到戈尔是二十一英里,那辆哈得逊每小时却能跑三十五英里……”(斯坦贝克,1982:137)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旱,使俄克拉荷马州的佃农纷纷破产。他们把没有受到干旱袭扰的加利福尼亚州当作希望之地,于是举家西迁,整个66号公路变成了一条蜿蜒而行的长龙。斯坦贝克这样描述俄克拉荷马人西行的公路:“六十六号公路是主要的流民路线。六十六号——这条横贯全国的混凝土的长路,在地图上从密西西比河一直蜿蜒通到贝克斯菲尔德……然后又越过沙漠通到山区,再通到加利福尼亚的富饶平原……逃荒的人们在六十六号公路上川流不息地前进,有时候是单独的一辆车,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车队。他们沿着这条大路终日缓缓地行驶着……”(斯坦贝克,1982:131-132)
其次,斯坦贝克通过以约德一家和牧师吉姆·凯绥西行的过程和在加利福尼亚的坎坷遭遇,一方面揭示了人生历程的艰难和曲折,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类心理的自我认识和灵魂的升华。历经旅途的千难万险,约德一家和其他的俄克拉荷马人终于到达了他们梦想的加利福尼亚。然而此时的加利福尼亚,并非他们所想像的迦南圣地,这块盛产葡萄的乐园,早已变成了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那里的工作很少,大农场主还联合起来压低工资标准。面对这一困境,牧师凯绥领导工人与农场主抗争,并因此被农场主杀害。凯绥的死教育了约德家的汤姆,使其从个人主义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将自己的灵魂融入集体的大灵魂中,成为一个人民的领袖。汤姆在灵魂深处完成的巨大转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母亲。约德妈妈对儿子的转变感到由衷地高兴,也不再为儿子的事业担惊受怕了。为了躲避暴风雨的袭击,约德妈妈和家里其余的人迁移到一座山上。在那里,一个行将饿死的男人吸引了他们的同情。因为母腹中的孩子死亡而伤心的女儿罗撒香,主动走到那个挨饿的男人身边,顾不得羞怯,将奶水喂给这个快要死的人。这一举动表明,罗撒香从一个极度自私的女孩变成了人类的伟大之母。罗撒香的转化,标志着约德一家完成了他们的人生之旅。他们在物质上陷入艰难的困厄,在精神上却进入了崇高的境界。
正如作品中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任性的公共汽车》也是一部表现旅行母题的作品。作品虽然表面上描写现代人的一次现实意义上的旅行,但由于斯坦贝克在小说扉页上题写了中世纪道德剧《每个人》诗句,它就从现实层面的旅行转化成揭示人类精神上的失落与救赎的旅行。小说中的公共汽车“甜蜜之心”(sweetheart)和道路代表旅行的物质载体,汽车上的旅客是旅行的“每个人”。司机朱安·季璜(Juan Chicoy)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的名字本身就像耶稣名字的缩写。车上的乘客来自美国的各行各业,例如小商贩厄内斯特·赫敦,脱衣舞女卡米尔·欧克斯,学徒工匹姆珀利斯·卡尔森,女大学生密尔德拉德·普利查德,她的父母亲普利查德夫妇以及老头范·布伦特等。普利查德先生是一个大商人,他是整个现代商业社会及其与生俱来的虚伪道义和性空虚的代表。范·布伦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经常聆听时间在他的脉搏里流逝,既希望死亡的到来,又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诺玛是一位餐馆服务小姐,是好莱坞男明星卡拉克·盖贝尔的崇拜者。她希望进入好莱坞,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与男人作爱的经历,但是在想像中总是与她的崇拜者神交。密尔德来德·普利查德小姐是普利查德夫妇的女儿,生活在一个高度浅薄、虚假和精神上贫瘠的世界,自幼受到父亲的控制,内心里充满了人性中的反抗意识。由此可见,汽车上的乘客都具有道义上的缺陷、精神上的疾病、性方面的饥渴和感情上的压抑,这些可以看作现代人类的通病。为了逃避艰难的现实、生活的无聊并追求欲望的满足,他们坐在朱安·季璜的公共汽车上旅行,就像摩西率领古犹太人出埃及,也像安·波特的《愚人船》上的人物那样去远行。他们希望通过旅行得到自己的幸福和乐园,因此,他们的旅行就象征着现代人类寻求救赎的历程。
然而,他们的旅行是任性的,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因为生活的喧嚣、肉体的享受、道义的放纵巨大地影响了他们追求救赎的意识。同时,他们旅行的的历程也被砾石、被河水冲塌的桥梁、泥泞的公路和泥潭所困扰,他们要不断地穿行在山岭和沙漠之中,这实际上是现代荒原的象征。尽管他们在旅行途中不断看到指引他们通向救赎的正确道路的启示性招牌,像 Repent(忏愧)、Come to Jesus(到基督那里) 、Sinner,Come to God(罪人,到上帝那里去)等,他们仍然不能到达目的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机朱安·季璜不喜欢他的乘客,就像耶稣或摩西不爱他的庶民一样。他有意将车往坏路上开,致使汽车在途中抛锚。他借故找人修车而离开了,并躺到山岭上的一间草屋睡大觉。在季璜离开汽车的一段时间里面,车上的其他乘客就像贝克特荒诞戏剧《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他们一方面在等待季璜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在漫无目的地闲谈或沉溺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他们不考虑旅行的目的,也不想在今后的人生中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女大学生密尔德拉德具有一种叛逆精神,她出于对季璜的兴趣而离开公共汽车去寻找他。她终于在山岭上的一间草房里找到了正在睡大觉的季璜,并在半推半就的状态下与他发生了性关系。性满意足的季璜这才下山,继续开着他的破旧的公共汽车带着他的乘客前行。他要带着这群毫无人生目的的乘客到何方去?如果人们的领袖和先知都堕落了,人类还能到达他们精神的乐园么?人类还有救赎的希望吗?这是斯坦贝克对现代人类危机的深深思索。
五、结语
斯坦贝克的其他小说《金杯》、《人鼠之间》、《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珍珠》、《小红马》和《逃亡》等,也都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旅行的母题。这一方面是斯坦贝克一生旅行在作品中打下的原型烙印,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旅行历史和现实对斯坦贝克创作深层意识的影响。从历史上讲,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为逃避本国天主教的迫害,曾搭乘“五月花号”轮船出行到新大陆,这是历史的原型。而在20世纪初,由于汽车、轮船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使美国成为一个“坐在车轮上的民族”,旅行成了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在旅行历史、现实和自身实践的影响下,斯坦贝克自始至终赋予自己作品旅行的母题就丝毫不奇怪了。借助这种旅行母题,斯坦贝克成功地将人物的性格发展与作品的结构发展结合在一起。通过旅行,主人公获得了知识,发现了自身,他要么获得崇高的人生顿悟,要么陷入悲剧性的毁灭。
[1]Fontenrose,Joseph.John Steinbeck: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M].Barnes& Nobel,Inc.,1964.
[2]Jackson 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 Writer[M].New York:Viking,1984.
[3]John Steinbeck.Autobiography:Making of a New Yorker[M].New York Times Magazine,1,February,1953.
[4]Elaine,Steinbeck & Robert Walsten.John 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5.
[5]苏珊·席林格罗.俄罗斯纪行·导读[Z].杜默,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Beegel,Susan F.Foreword[C]//Katherine A.Rodger.Breaking Through:Essays,Journals, and Travelogues of Edward F.Ricket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7]Tamm,Eric Enno.Beyond the Outer Shores[M].Four Walls Eight Windows,2004.
[8]Steinbeck,John.The Log from the Sea of Cortez[M].London:Mandarin Paperbacks,1990.
[9]约翰·斯坦贝克.俄罗斯纪行[M].杜默,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10]约翰·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M].麦慧芬,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1]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Z].胡仲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