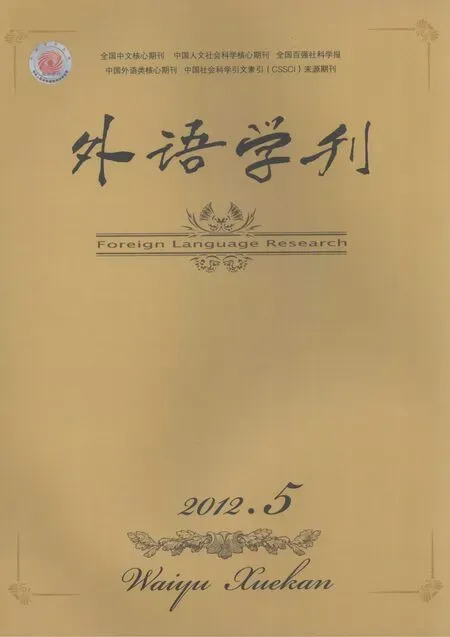上帝的性别:《秀拉》对上帝造人神话的改写
2012-03-19张宏薇
张宏薇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上帝的性别:《秀拉》对上帝造人神话的改写
张宏薇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在《秀拉》中,托妮·莫里森从性别角度对上帝的形象进行颠覆,对上帝造人的神话进行了大胆彻底的改写,塑造了富有创造力、智慧与尊严的新夏娃形象,把女性被基督教父权神话所剥夺的创造力、主体性地位交还给女性,而小说中令人失望的男性群像图则是对西方“阳物”崇拜的巨大嘲讽。作家通过改写夏娃和亚当这两个原型人物颠覆了传统基督教女性观和西方传统女性观,尤其是通过秀拉的反叛形象表达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
上帝;原型;女性主义;秀拉
《秀拉》发表于1973年,是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它篇幅短,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是引起的反响和震动却很大。它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任何黑人女性形象都不同的新女性形象——秀拉,也正因如此,中外学者一致认同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力作。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秀拉这一人物形象入手,通过探讨秀拉对自我身份和主体性的追寻以及她的反抗精神对黑人群体的影响,探讨这部小说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从宗教、神话与文化、文学的关系入手,剖析《秀拉》对《圣经》创世神话进行改造的女性主义内涵,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解读《秀拉》这一女性主义文本。
1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圣经》创世神话
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社会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之间历来联系紧密。传统基督教与西方女性观之间的关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传统基督教的女性观呈现出一种二元性——尊重与歧视并存,而犹太先知们对于人类起源这一神话的父权式改造和反对男女平等的神学家及哲学家们的片面阐释使歧视女性的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刘文明认为,“早期基督教对于男女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基于现实社会,而主要是出于神学的思考,这种神学理解的思想根源,则来自于犹太教及其《圣经·旧约》”(刘文明 2003:2)。我们知道,基督教最初起源、脱胎于犹太教,而犹太传统对男女关系的基本定位便是男尊女卑。《旧约》中成为男尊女卑思想依据的主要是《创世纪》中关于男女受造的描述以及关于“原罪”起源的传说。
《创世纪》中关于男女受造的描写有两处。一处在《创世纪》第1章第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的所爬的一切昆虫。”英文《圣经》的原文是:So God created humankind in his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这里,in his image(以他的形象)重复了两遍,而且created(创造)的宾语有2个,共出现3次:humankind(人)和them(他们),显然上帝在造人时把男人、女人平等对待,并没有特意的区分,唯一的区别是人在生理性别上的差异male and female(男人和女人)。
另一处在《创世纪》第2章第7-23节: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版本。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先造了一个男人——亚当,并让他看守、管理伊甸园。上帝觉得亚当独居不好,所以又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夏娃。后来夏娃在蛇——撒旦的引诱下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实,然后让亚当也吃了。
这两处明显存在着差异。第一版本的上帝造人说提供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绝对根据,具有丰富的伦理学意义。既然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人的本性具有共同的基础和来源,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是“神造”和“天赋”的,因而“生来平等”,不论地位的高低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尊严。然而,显然早期的神学家们和释经者们对后一个版本更感兴趣,他们利用《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两处记载的分歧,极端夸大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故意忽略了其中平等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圣经》的父权化。
上帝造人神话和人类始祖犯“罪”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方传统女性观。造女人在男人之后,而且女人取自男人的肋骨,这就注定了女人先天不足,低男人一等。女性的卑微还远远不止如此,她还被看成是“人类堕落”与“原罪”的祸首。正是夏娃的犯“罪”行为决定了人类的悲苦命运——人类不仅从此再也不能享受伊甸园中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要终身劳作,在种种苦难中煎熬,而且还失去了不朽的生命,不得不经历生老病死的痛苦历程。夏娃被认定是“原罪”的肇始者,后来的父权主义者利用这一神话故事,为他们的菲勒斯中心思想找到了宗教神学上的根据,推导出女性是祸水,是理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是导致男性犯罪的邪恶的淫欲,这也就成了西方“厌女症”和歧视、贬抑女性的渊薮。
女性主义者认为《圣经》的上帝造人神话完全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产物,根据有二。第一是它肯定了以上帝为父权象征秩序的男性权威,确立了男性优于女性的地位,从神学与宗教上为父权统治找到了合法的依据。上帝至高无上,因为他是万物的造主,世界的主宰;夏娃要遵从亚当,即女性遵从男性,因为她取自于他,属于他;他是她的“头”。这就形成了西方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第二是它否定了女性的创造力,极度夸大了男性的创造力。人类的母亲本来是女性,结果却人为地编造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男性上帝凌驾于人类之上,凌驾于女人之上。罗伯特·麦克艾文在他所著的《夏娃的种子》一书中说,“《创世纪》第2章,通过听着都难以置信的女人出生自男人的故事,来申明男人的创造力”(麦克艾文·罗伯特 2005:16)。用美国女性主义作家、思想家、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凯特·米利特的话说,“这是男性侵夺女性权力的典型事例。他让上帝在不享有女人协助的条件下创造了世界,从而专横地将生命力据为己有了”(米利特·凯特 1999:80) 。 其结果必然就是抹杀了女性的创造力,压抑了女性的地位。
女性主义对传统基督教的批判还表现在对上帝性别的质疑。“原始人在尚未了解两性的结合与怀孕生育的因果关系之前,仅凭直观看到的经验就认为女性母亲才是唯一的生育主体。因此,产生一种叫做“孤雌繁殖”的原始信念,表现为许多民族神话中的女性创世主和原始母神(the Great Mother)”(叶舒宪 2001:27) 。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最初的创世神话中生命的创造都是由大母神来完成,希腊神话如此,埃及神话如此,中国神话也如此。据此推断,《创世纪》中上帝的原型应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家族领袖——母亲。《创世纪》中上帝性别的人为转移是父权统治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对于创世神话中两处存在的矛盾,刘文明也认为,“这种矛盾的出现,主要是父权社会中的希伯来先知们对母系社会流传下来的创世神话进行了改造的结果”(刘文明 1999:61)。
2 《秀拉》对“夏娃”的女性主义改写
对于上帝性别和种族属性的不同认识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治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一个人对上帝形象的解读,对其种族属性和性别属性的偏好,代表了这个人的种族和性别的政治立场。因此可以说,上帝形象是一种文化符号。
在《圣经》中,在西方神学家的眼里,夏娃和圣母玛利亚犹如“妖妇”与“天使”,分别代表着淫乱、堕落和圣洁、高贵的女性品质的两极,前者遭人唾弃,后者则受人尊敬。但是,在莫里森的笔下,《秀拉》中的夏娃(Eva,即Eve 的变体)与创世神话中的夏娃毫无共同之处,两个夏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1 夏娃是一家之主,受人尊敬和爱戴
首先从夏娃和她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来看,小说和《圣经》的描述截然不同。基督教的婚姻观总的来说提倡夫妻互敬互爱,但基于上帝造人的神话,基督教认为男女在灵魂上平等,但在肉体上却不平等。因此,在家庭中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服从丈夫。虽然基督教强调丈夫要爱惜自己的妻子,实际上妻子对丈夫的顺从还是被摆在第一位的。保罗关于夫妻关系的论述,最典型的言论是《以弗所书》第5章中的一段话:“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在小说中,夏娃,而不是“亚当”,是一家之主。夏娃的丈夫,本应是一家之主、妻子的“头”、儿女的靠山的“亚当”,在生活处于困境的时候抛妻弃子,临阵脱逃了。夏娃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担,并且在困境中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没钱,没吃的,却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艰难的生活摆在她面前,就如那个要挨过的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夏娃没有低头,也不怨天尤人,更不像有些女人那样扔掉孩子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出路。夏娃——一个单身母亲,不仅让自己的孩子都活了下来,而且还使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与那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只能任凭上帝和命运摆布的夏娃不同,小说中的夏娃用智慧和才力建立起了自己的伊甸园。她既是这个以女性为首的王国的创建者也是统治者,指挥着她的子孙、朋友、流浪汉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房客的生活。与《圣经》中横遭指责、卑微谦恭的夏娃不同,小说中的夏娃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时刻保持着尊严。她坐在轮椅上,使得成年人要和她说话,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得弯腰俯首。男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簇拥在她的周围,她显然是这个不断扩大的“王国”中至高无上的“女王”。
2.2 夏娃是母性的典范,富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
夏娃还是母性的典范。当生活处于绝境中时,她选择了牺牲身体的方式求得一家人的生存。她为了孩子有饭吃而不致饿死,不惜故意让火车压断自己的一条腿,以获取保险金。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生活相对安逸的时候也没有减弱,为了救身上着火的女儿汉娜,她从三楼纵身跳下,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死。要知道她是坐着轮椅只有一条腿的老太太。在危机时刻,她能冲破用木板封住的窗子,破窗而出,只有母爱才会有如此的力量。夏娃的母爱也表现在她对其他男性人物的态度上。她收养了三个弱智的孩子,还供他们读书,她对其他来访的人亲切、热情,充满关爱,所以受到大家的普遍喜爱和尊敬。
2.3 夏娃身上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
夏娃身上还体现出旺盛的创造力。按照《旧约》律法,古代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工作了六日,第七日便休息。所以摩西十诫中有“当守安息日”的训诫。基督徒在周日也要停止工作,到教堂做礼拜。这也是“礼拜日”的来历。然而,夏娃却从未停止过创造,在夏娃的指挥和管理下,她家的房屋不断地得到扩建,这接一间房,那开一个廊。夏娃家的门牌号是木匠路“七号”,这意味着她的“王国”是在上帝休息的时候——第七日创造出来的。这也是对遗忘了像她这样孤苦无靠的,住在“底层”(bottom)的黑女人的上帝的无言的反抗。
综上所述,小说中的夏娃是一家之主,而不是亚当的奴仆,是以女性为主的世界的女王,男人是她的臣子。夏娃独立自强,极富创造力,她带领女儿和外孙女顽强过活。夏娃身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和女性魅力,深得大家的喜爱。这就推翻了《圣经》创世神话对女性的歪曲与贬损,当然也就有了离经叛道的意味。
3 《秀拉》对“亚当”的女性主义改写
如果说夏娃具有上帝一样的创造力,具有上帝一样的地位、权威与慈爱的话,那么生活在她的王国里的男性们则是懦弱、无能、没有责任感的,甚至是弱智和白痴,小说中呈现出一幅令人失望的男性群像图。这样的写作策略是对《圣经》上帝造人神话的彻底翻转,也是对西方“阳物”崇拜的巨大嘲讽。
小说中的男人似乎都缺乏责任感。无论是在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上,还是在艰苦的生活当中,他们都是没有责任感、意志薄弱的懦夫和逃兵。当生活遇到困境时,他们都选择了抛弃妻儿,离家出走。夏娃的丈夫波依波依是这样,奈儿的丈夫裘德是这样,秀拉曾经爱过的阿杰克斯是这样,这些男人既不可依靠也不可信赖。
夏娃的丈夫叫波依波依(BoyBoy),夏娃和他在一起度过了五年令人伤心失望的生活。他好色、贪杯而且欺侮夏娃。在夏娃的房客中还有一个叫柏油娃(Tar Baby)的。他们俩名字中的Boy和Baby都暗示着他们缺乏成年人应有的责任感,是没有长大的孩子。人如其名,事实也的确如此。柏油娃虽成年了却非常瘦小。他每天醉生梦死,只会用酒精麻醉自己,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等待死亡,但是又害怕孤独死去,因此来到夏娃的王国寻找庇护。
男人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还表现在战场上。22岁的夏德拉克在参加一战的时候手被炸残,在战场上他亲眼见到了身边的人如何被炸死倒下,战争的残酷不仅给他带来了肉体的伤残,更带来的心灵的创伤。他的神经几近崩溃,变得疯疯癫癫。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逃避,他在回到底层后创立了全国自杀节。夏德拉克的故事既说明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也说明了男性神经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被战争吓破胆的还有夏娃的儿子“李子”,比夏德拉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战场回来后一蹶不振,不仅不能替辛劳一生的母亲分担,还要像婴儿一样躲到母亲的怀抱中寻求安全与庇护,甚至在毒品中寻找慰藉,精神与意志陷入沉沦。
在西方传统思想看来,男性气质总是和强悍、进攻和占有相关,而女性气质总是和顺从、懦弱和宽容等相联系。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女性没有男性的生殖器官,是被阉割的“男性”,因而在本质上是“匮乏”,天生有一种“缺失”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是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
小说《秀拉》可以说是对男性所杜撰的“缺失”理论的巨大反讽。有着雄性生殖器的男人都是匮乏的,要么在精神上脆弱,要么在心智上贫乏。离开了女性的庇护他们成了在精神上无法立足的残废,可不可以说他们是被阉割了子宫的“女人”呢?!作家借夏娃的手,用她犀利的笔杀死了那些“匮乏”和“缺失”的男人。在这群软弱、自私、无责任感的男性群像当中夏娃的形象自然突显出来,作家对女性的讴歌与赞美,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可谓独到而深刻。
4 秀拉——反叛的魔鬼,堕落的“夏娃”
秀拉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以她命名,可见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和灵魂。秀拉的额头上有块胎记,这块胎记看起来既像“带梗的玫瑰”又似“响尾蛇”, 魔鬼撒旦曾经化身为蛇,玫瑰的刺会扎人,这显然标志着她的桀骜不驯和反叛精神。在黑人居住区——小镇梅德林,秀拉的确被看成是“魔鬼”和“巫女”,是上帝的“第四副面孔”。
非洲传统宗教中对上帝的认识和基督教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同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至善,与魔鬼代表的“恶”构成了二元对立。而在非洲传统宗教中,上帝与“恶”脱不开干系,上帝既有“善”的一面,也要对“恶”负责。(Alexander 1998:303)因此上帝的“第四副面孔”也就是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之外的第四个侧面——恶,即魔鬼“撒旦”。 秀拉的反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 对上帝的大不敬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基督教著名的使徒信经十二句话的第一句。上帝观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基督教的使徒信经不仅陈述了上帝存在这一信念,而且阐发了对上帝的属性及品格的独特理解。上帝是父,是“信实”和“慈爱”的;上帝是造物主,人类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
在小说当中,上帝不是仁慈、正义的化身,而是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帮凶。上帝跟白人站在一起,跟男人站在一起。从黑人居住区的来历看。白人农场主对黑人奴隶许诺,只要他完成一项艰巨的工作就给他自由和一块低地,但是当黑奴如约完成了工作时,白人农场主却给了他一块高居山顶的荒地,还狡辩说;“(那块土地)从我们这里看是高高在上,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啦。那是天堂的底层——有着最好的土地呢”(Morrison 1982:5)。这里,白人农场主完全自诩为上帝,他的话语如上帝创世时的语言威力一样,可以黑白颠倒,却不容黑人质疑和争辩。
在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并存的年代,黑人女性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无辜的牺牲品。古代犹太人崇拜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仪式是向上帝献祭,而献祭的牺牲就是牛羊。羊曾顶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使他不必成为父亲向上帝表示忠诚的祭品。在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更是要宰杀替罪的羔羊。人的“罪”得以豁免,但是羔羊却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就是“替罪羊”一说的来历。
秀拉不愿意像小镇里的其他黑女人那样“被动等死”,她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秀拉对代表白人和男性利益的“上帝”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对他的权威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夏娃先后收养了三个孤儿,她一律管他们三个叫杜威。她认为没有必要区分他们三个。而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夏娃的观点,三个人合在一起成了使用一个复数名字,彼此之间不可分离,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杜威。这显然是在影射基督教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小说中三位一体的杜威是弱智的、爱犯错的,秀拉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他们经常受到秀拉的惩罚。这是对上帝多么大胆的嘲讽啊!
4.2 在自由的性爱中确立自我
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类的堕落始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上帝允许他们吃伊甸园中的果子,却独独不允许他们吃知善恶树(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上的果实。然后夏娃没有经受住蛇的引诱,而她又引诱了亚当也吃了。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他们吃这棵树上的果实呢? 难道真的像蛇说的那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实以后,人就会心明眼亮,具有了跟上帝一样的智慧?为什么当上帝回来,看到亚当夏娃用树叶蔽体,羞于出来见他时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偷食了“禁果”?上帝究竟“害怕”的是什么呢?
米利特认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具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是讲述人类如何发明了性交。这个故事表现的重大主题——人类简朴的丧失、死亡的来临和对知识的首次体验——都以性为中心。在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前,人类处于蒙昧状态,尚不知性为何物,亚当夏娃赤身露体,并不感到害羞,快乐而无忧。但是夏娃偷食了禁果并且引诱亚当也吃了以后,“知晓”了性事,懂得了害羞。在希伯来语中,动词“吃”也有“交媾”的含义;在《圣经》全书中,“知晓”(knowing) 是性欲的同义词,是与阴茎接触后的产物。因此,伊甸园的丧失,生命中邪恶和苦难的产生都源自性欲,而夏娃是性欲的化身。
这实际体现了远古时男性对“性”的矛盾心理——好奇与恐惧,和对自己在与“性”有关的犯罪中的责任的推诿。无论是赫西奥德的《神谱》中的潘朵拉还是《圣经》中的夏娃,都被看成是淫欲的象征。赫西奥德认为是潘朵拉向人类赋予了性的欲望,并从而结束了一个黄金时代。自从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后,邪恶充斥人间,人类不再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地上,人要终日劳作,经受疾病之苦。因此,女性等于欲望,而性欲为人类带来了所有的祸端,那么女性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因此,一旦女人与性,与欲望挂上钩,就意味着堕落、邪恶,万劫不复和十恶不赦。在男性对女人,对性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悖论。女人是他们欲望的对象,同时又是指责的对象。当他们需要规约、教化女性的时候,把圣母玛利亚树立为榜样,但是当他们要鞭挞、贬损女性的时候就把夏娃拉出来当靶子。
性不仅涉及生理因素,还涉及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继而文化问题。任何对于身体的言说和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它所对抗的文化代码。(王玉括2005:122)凯特·米利特在她的著作《性政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它(性行为)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根植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米利特·凯特 1999:36) 。
凯特·米利特认为,“现今文学中有关性行为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强权和支配观念发挥作用的结果”(米利特·凯特 1999:1) 。她在书中以大量的实例(男作家如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作品中对性的描写)说明性关系鲜明地反映出了男女两性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在男作家的笔下,女性在性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总是作为客体(object)而存在,她的感受与快乐从未得到过关照,她只是雄性的猎物、甚至是玩物。
在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上,在性关系当中,秀拉达到了自由的极致。秀拉则完全不具有父权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女性气质,如被动、顺从和柔弱,她对黑人社区的任何道德规范都不信奉。她不是温柔可人的“天使”,而是一位无视成规习俗、特立独行、令人畏惧的“妖妇”。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把男人勾引过来,然后再一脚踢开,她对男人不屑一顾,男人成了她的猎物甚至是玩物。恐怕文学作品中没有一个黑人女性甚至包括白人女性在性上占有如此主动和高高在上的地位。这对传统道德是一个最胆大妄为的颠覆。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倡身体写作,因为女人身无长物,身体是她唯一的武器。把身体的快乐和写作的快乐等同起来,让一直被书写、被言说、被压迫的她成为书写和言说的主体,既掌握了自己的身体,也掌握了话语的权力,这就解构和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两性关系。秀拉在性爱上表现出绝对独立的人格,她把支配和屈从的两性关系彻底地颠覆了过来。
《秀拉》出版于1973年,当时正值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高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方兴未艾之时。莫里森是把《秀拉》置于黑人女性争取精神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对人物的行为做更深入的考察和思考,以体会作品深刻的内涵。如果用简单的传统道德的眼光来评价秀拉的是与非,就无法看到其中作家对父权文化的激烈批判。秀拉在性行为上的放纵与自我是对传统基督教“女性即淫欲”的观念的大胆挑战,也是对西方女性处于服从和被支配地位的大胆反驳。这充分反映了莫里森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尽管她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莫里森归结为女性主义作家。
5 结束语
莫里森在《秀拉》中援引了基督教《圣经》的符码——上帝、撒旦、夏娃与亚当,但赋予了它们与传统基督教截然不同的文化寓意,从宗教的角度对父权文化、种族主义进行批判。她大胆质疑上帝的性别,把传统基督教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男性上帝进行解构与颠覆,通过改写上帝造人神话,尤其是改写夏娃的形象,塑造富有创造力、智慧与尊严的新夏娃形象,莫里森把被基督教父权神话所剥夺的创造力、主体性地位交还给了女性,并且通过塑造秀拉这一反叛的撒旦形象表明了自己鲜明而且激进的性别政治立场。
刘文明. 论《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女性及其女性观[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9(10).
刘文明. 上帝与女性[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麦克艾文·罗伯特. 夏娃的种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米利特·凯特.性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王玉括. 莫里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叶舒宪.发现女性上帝——20世纪女性主义神话学[J].民间文化, 2001(1).
Alexander, Allen. The Fourth Face: The Image of God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J].AfricanAmericanReview, 1998, Summer: 293-303.
Morrison,Toni.Sula[M]. New York: Plume Books, 1982.
【责任编辑郑 丹】
TheSexofGod:TransformationofEdamandEveinSulaby Toni Morrison
Zhang Hong-we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Toni Morrison subverts the sex of God and transforms the myth of God’s creating Adam and Eve inSulaboldly and completely. She endows women with creativity and subjectivity which have been deprived by Christian patriarchal myth of women by portraying a brand new image of “Eve” who is creative, wise and dignified, and satirically criticizes penis-worship in western patriarchal society. S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al view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view of women are overturn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archetypal characters-Adam and Eve, and the author’s radical feminist thought is conveyed through the image of rebellious Sula especially.
God;archetype;feminism;Sula
I106.4
A
1000-0100(2012)05-0135-5
2011-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