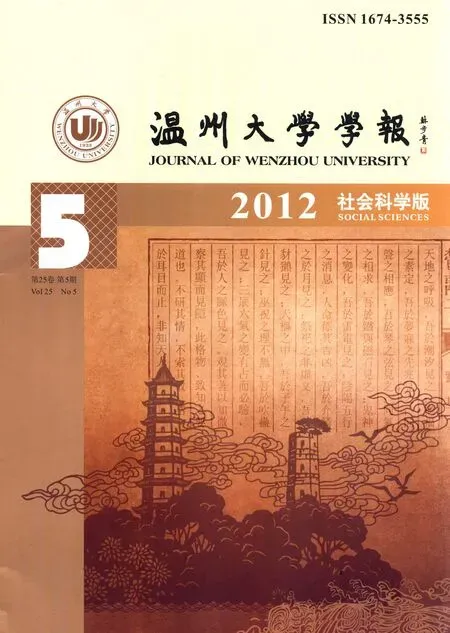论安世高的译学思想和翻译方法
2012-03-19杨超标
杨超标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论安世高的译学思想和翻译方法
杨超标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安世高可以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他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对汉末佛教的迅速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分析安世高的身世、佛经理论和汉译,可以发现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及其译学思想。
安世高;佛经翻译;译学思想
一、安世高的身世
关于安世高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他是安息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僧者;也有说他是安息国的质子①质子其实就是人质.纳质与和亲一样, 是维持国与国关系稳定的一种外交政治手段.;还有说他是木鹿地区安息宗室旁支[1];但国内普遍认为他是安息国宗室成员:据《出三藏记集》[2]508及《高僧传》[3]4记载,安世高是西域安息国正后所生的太子,幼有异能,通五行星象之术,能医,又懂鸟语,因不愿为王,让位与叔,出家修道,游历四方,于汉桓帝时到达中土,不久即通华言,并开始译经,20年间出经三十多部,其中大多为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定理论。另外,还有国外学者依据考古实物(多是中亚地区考古资料),认为他是木鹿高僧:经过苏联学者在中亚地区进行的长期考古发掘,在安息国内只在马尔吉安那首府木鹿城狄亚乌尔·卡拉区发现一座公元2世纪佛教寺院遗址,其中有残存的佛塔、佛像及若干佛典(说明这里曾有一个佛教团体)。苏联学者Yarshater据此推测安世高的传说很可能就和木鹿的这个佛教团体有关[4]。对于这一说法,我国著名学者张广达在谈到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时也有提及[5]。
二、安世高的佛经汉译
佛教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公元1世纪左右)至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进入中国时,正值谶纬神学泛滥,巫风炽热,理性遭贬抑的时期,佛教抓住这个机会,先以神灵迎合图谶,继以学说依附道术,很快在中国内地传播开来。因为佛典只有译成汉语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所以,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
佛经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与阐释的工作。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一百多年后,在宫廷中和上层社会里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普通人更好地了解佛教,信仰佛教,“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就开始从事译经活动”[6]: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来到洛阳并学会了汉语。之后,安世高着手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至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年-172年),安世高从事了长达20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与东汉时期大量大乘经典译经者支娄迦谶相比,安世高是小乘佛经的首译者,他译出了大量小乘经典。可以认为,在般若经(大乘佛教的经典)译入以前,佛经最大的翻译家是安世高[7]。
安世高的译经比较杂。因为“禅数”(包括“禅”与“数”两个方面)是安世高的专长,所以“其所出经,禅数最悉”[2]245。据镰田茂雄所称,“安息国盛行说一切有部小乘佛教。安世高出身于安息,精通禅观、阿含、阿毗昙学。从此佛教法相宗的基本教义开始传入中国”[8]。安世高的佛典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有特点。从内容上说,他所译传的都是印度小乘佛教十八部中“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理论。重点是用“说一切有部”的说法解释的小乘的“阿毗昙”和“禅”(简称“禅数”)。据《出三藏记集》,“禅”(又称“禅定”)是佛教的一种宗教修养活动,其要点是运用宗教教诲所得的信仰力量,以限制来自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欲望的引诱,令修习者的精神乐于集中在被规定的观察对象,并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对治烦恼,达到心绪宁静、心身愉悦的境界[2]246。在安世高所译的这类禅法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安般守意经》。“数”是指《阿毗达摩》的事数。(《阿毗达摩》又译《阿毗昙》、《毗昙》,意译为对法、无比法或胜法。)它以数字对不同佛教基本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十八界等等)所以它也可译为“数法”。“数法”包括《阿就毗昙》的经和论,讲的是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2]247。安世高所译的数法或阿毗昙经典,以《阴持入经》为代表①阴、持、入为佛教的三科.“阴”分为五种, 指人的肉体和精神两重要素.安世高译称为色、痛、想、行和识.“持”有十八要素, 安世高所译称为“十八本持”.这“十八本持”分为六根(眼、耳、鼻、舌、身和意)、六境(色、声、香、味、触与法)和六识(眼、耳、鼻、舌、身及意识).“入”指六根和六境.。从形式上说,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言,所以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表达出来,措辞准确、不粗俗、不铺张而且恰到好处。但因为是首创,没有经验,无例可循,翻译中有些术语还不够通俗易懂,有些文句过于照顾原结构,有重复、颠倒的现象。实际上,在译事的草创阶段,安世高所翻译的经典语言艰难晦涩,十分难懂。“其语言古怪、粗俗,有许多土话,常常混乱到无法理解的程度,其风格明显是‘非中国式’的”[9]。
对于安世高译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佛教史上历来有很高的评价。南朝梁代僧人僧祐说,安世高“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其译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4-5。另一梁僧慧皎认为安世高的佛经译文:“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质从文,或因质不饰。”[3]267换言之其译文是音韵文字,文质两宜。例如安世高所译经典《安般守意经》,其译文“自浅至精,众行具举,学之先要,孰踰者乎”[10]158。不过安世高的译经也有“贵本不饰”[10]156的时候,“所译出百余万言,探畅幽赜,渊玄难测”[2]247。总的说来,安世高的译经“文质平衡”,即僧祐所说的“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三、安世高的译学思想和翻译方法
(一)安世高佛经汉译并非“格义”
“格义”分为狭义的格义和广义的格义。狭义的格义特指佛学上的格义。根据已知的史料研究,“格义”概念首见于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舆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3]152与狭义的“格义”基本同义的是“连类”。陈寅恪先生便认为,“讲实相而引庄子义为连类,亦与‘格义’相似也”[11]。广义上的“格义”则可以意味着所有那些通过概念的对等,“用原本中国的观念来对比外来的思想观念——以便借助于熟习的本己中国概念逐渐达到对陌生的概念、学说之领悟和理解的方法”[12]282-294。这个意义的外延还可以再扩大,可以将所有运用新旧概念的类比来领悟新学说的方法都称为“格义”。因此,广义上的“格义”不是指“简单的、宽泛的、一般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比较”,而是指“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12]284。在这个意义上,将一种文字转化为另一种文字的翻译也是“格义”。
目前中国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对安世高的认识主要来自几本翻译通史。其中提到他的译经工作都集中在其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上,材料来源也多半依赖翻译史或资料汇编,鲜有直接接触译文的,因此翻译史对其译经活动的描述就成了认知安世高的基础,甚至还成为建构所谓中国翻译理论和探讨古代翻译方法的素材;这可以说是安世高佛经汉译与“格义”拉上关系的主要原因[13]。有人认为安世高做佛经汉译的时候非常注意寻找印度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讨论安世高如何引入佛教基本概念时,有两个代表性的译例:《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属禅法类经,所重的禅修法门是数息观。“安般”是两个梵文或巴利文音译词的略写,即“安那”(ana)与“般那”(apana),后世音译为“阿那波那”,是指意守出呼入吸之气,它是学习禅定的入门基础。“守意”实际上是对“安般”概念的意译,指念呼吸出入,数息。因此可以称其为数息观,它主要对治多念之心。数息观的具体修行方法分为十个阶段(即数息、相随、止、观、还、净和四谛)。这称为“十黠”,即十种智慧。前面的六种,被称为六事四禅,四禅是指六事中的前四事。六事也与三十七道品相配合,数息为四意止,相随为四意断,止为四神足念,观为五根五力,还为七觉意,净为八行。所言四谛,是指“识苦、弃习、知尽、行道”[2]242(后译为苦、集、灭、道)。在《安般守意经》中,安世高用音译来处理了里面最重要的观念。《阴持入经》是毗昙类经,以阴、持、入三科组织,阐述了小乘佛教的“苦谛四行相(非常、苦、空、非身)、十二因缘和三十七道品”[2]248的基本教义。“阴持入”则是佛学的基本观念“三科”,后世译为“蕴界处”。在这里“阴”字并无“阴阳”色彩,而是“荫覆”之意,即后世的“蕴”;“持”是“界”;“入”是“处”。“阴持入”虽是汉字,但如果不加解释,则不懂佛理者绝对猜不出其中含义;至于“安般”,不但是音译,而且用略语,更非没有佛学常识的人所能理解。如果安世高真的为迁就本土读者有意引用道家术语来做翻译,似乎就不会作出上述的选择了。再说安世高是成年入汉后开始学汉语,其文化参照系仍会以其早已熟习者为准,也没有可靠纪录说明他对汉本土学术有深入认识,我们就该实事求是,不要再把他的翻译冠以“格义”或类似的说法了。但安世高的译经能够相对忠实于佛教原本的思想,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即清净无为思想)担纲来曲折传达所谓“活”与“生”的美学主题,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幸事[7]。
(二)安世高的译学思想是重“质”而不是主“文”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文”、“质”两派之争在我国译经史上始终存在着。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出三藏记集》中就有对译者安世高的“质”和支谦的“文”的评论,认为“质”能得“本”,支谦等人“文”的结果是损害了经旨[2]290-291。同时,该书还说“然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也指出了“质”的弊端[2]254。安世高为何重“质”,究其原因是译者一般用自己最熟悉的文化作参照系。第一代译者大多数是西域来华的人,入境后始学汉语,对佛教的所谓“外学”(亦即汉本土学术流派)所知有限,要灵活运用本土的思想概念绝非易事。但到了年代稍后的译者如支谦,生长于中土,除佛学外亦熟知中国本土学说,要利用中国学术思想作为参照系,则自然感到得心应手。再者安世高不像道安那样受到了译场①译场就是高僧讲经、译经与传法的场所, 同时也是一个各种力量汇集, 各种声音竞相争辩的场所.影响而导致其译论从主“文”到重“质”,他没有加入过任何译场,所以其翻译策略没受到政治权利的干扰或左右。
(三)安世高的翻译方法与策略
由于阿富汗内战等因素,不少早期佛教残卷得以面世,不能不说是学界之幸事。例如 1996年在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某个佛教遗址中发现了《佛说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询安世高的译经风格提供了以往传世文献所欠缺的重要线索。此梵本残片虽短,也不是汉文本的翻译底本,但有巴利文对应文本的帮助,所以对理解安世高汉译本的词汇及其句式等,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9]。就具体的翻译方法与策略而言,安世高在佛经汉译时主要采用了包括仿译、音译、反译、增译、略译、语态转换等方法与策略,这些可从其译经一些例子中得以证实。
1.仿 译
“无有”是梵语,意为“没有、不存在”。“无有眼”梵语是acaksus。前缀a表示否定,caksus为名词,意为“眼睛”。方庆之对汉译佛经中“否定前缀类+梵语词根”这一类仿译现象进行了讨论,否定词常见的有“不、非、未、无”。此处“‘无有+名词’这一表示法,与‘无+名词’格式意同。‘无有’是安世高的译语偏好之一”[14]。
2.音 译
“安般”是两个梵文或巴利文音译词的略写,即“安那”(ana)与“般那”(apana),后世音译为“阿那波那”,指呼吸时的出息与入息。“乘”是梵文yāna的意译,音译为“衍那”,意思是承载(如车,船),也有道路的意思。“大乘”是梵文Mahāyāna的意译,音译为“摩诃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小乘”是梵文Hinayana的意译,音译为“希那衍那”,“希那”是小的意思[15]。
3.反 译
“莫折减”,梵语为sphītīkuryāt,意为“应该增多或增加”。可见汉本“莫折减”是用反义词的否定方式来表达的。
4.增 译
在“一辈眼不见,二辈一眼,三辈两眼”这组汉译中,因其原句式极为简练,其中也没有量词,由此“一辈”、“二辈”、“三辈”均为增译。再如在“意无有眼为何等;一眼名为何等;两眼为何等”这组汉译中,汉文本则分别加了“为、名为、为”[9]。在《六方礼经》在论述父子关系时,“安世高通过具体添加孩子的义务:‘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时做饭食,三者不益父母忧,四者当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师治之’,强调了父母的绝对权威,孩子对父母的绝对恭顺,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念对汉译佛典的渗透和影响。”[16]
5.略译和语态转换
在“是名为无有眼;是名为一眼;是名为两眼人”这组汉译中,汉文本第三句直译出了“人”,前两句则略译之;另外梵本是被动句式,汉文本译作“名为”,有用主动的形式来表示被动的意味。安世高译经中的被动式情况,高列过有过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东汉佛经的被动式的使用中,“为R所V”、“为R之所V”式运用较为频繁。而安世高译经中使用的被动句式中,“为R所V”式占73%,高于支谶的57%,也高于整个东汉译经中72%的比例[17]。“再比如在《六方礼经》对父子关系的描述中,早期汉译佛经将原经中的‘母和父’语序统统改成‘父和母’,有的地方还增添上‘孝诸父母’的一类话。而对原经中关于父母不尽义务就不能得到孩子的赡养的观念,安世高选择不予以翻译以适应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念。”[16]
四、结 语
从安世高翻译的经典中,所呈现的学说思想,几乎是属于部派佛教上座部的系统,故安世高翻译的经典以禅法、数法最为完备。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了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传播佛教时,一边译经,一边聚徒开讲、传授。他的翻译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他口述解释,由他人执笔成书,但安世高的翻译仍以笔译为主。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所以,安世高的佛经汉译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安世高所译的经籍,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当时汉译佛经尚属创举,没有其他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安世高的译文难免有不适当之处。总之,安世高的译经无论是在研究汉传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还是在中古汉语史与中西交通史等方面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9]。
[1]李铁匠.安世高身世辨析[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9, (1): 63-66.
[2][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3][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 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4]Yarshater E.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57.
[5]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4): 1-13.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8.
[7]赵建军.安世高禅空观美学新解[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14-18.
[8][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郑彭年,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22.
[9]陈明.新出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平行梵本残卷跋[J].西域研究, 2003, (4): 59-65.
[10]朱志瑜, 朱晓晨.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11]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C]//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90-116.
[12]汤用彤.理学, 佛学, 玄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3]孔慧怡.从安世高的背景看早期佛经汉译[J].中国翻译, 2001, (3): 52-58.
[14]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J].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2000, (1): 247-262.
[15]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7.
[16]佚名.出世之道与入世人伦[EB/OL].[2011-02-01].http://www.ebud.net/teach/renbudd/teach_renbudd_20051201_1.html.
[17]高列过.从被动式看东汉西域译经者的翻译风格[J].西域研究, 2002, (2): 77-78.
Exploration on Ashigao’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Translation Ways
YANG Chaobi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Buddhism was first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pproximately during the 1st century).Quantities of translation of sutras didn’t come about until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Ashigao was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and important translator to translate sutras into Chinese.His translation was original and peculiar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xpansion of Buddhism in that period.Through analysis of Ashigao’s background, Buddhist theory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his translation ways,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thought could be explored.
Ashigao; Sutra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hought
H315.19
A
1674-3555(2012)05-007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5.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周斌)
2011-03-16
杨超标(1978- ),男,湖南祁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