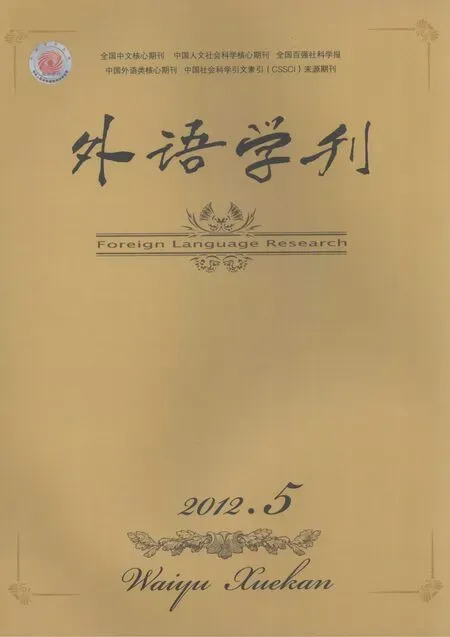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与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
——从钱冠连和陈嘉映谈起
2012-03-19杜世洪李菊莉
杜世洪 李菊莉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与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
——从钱冠连和陈嘉映谈起
杜世洪 李菊莉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围绕格赖斯合作原则,钱冠连和冯光武所持的不同观点颇有启示作用。这启示就是老问题需要新理解,即有必要重新审视格赖斯合作原则。格赖斯合作原则并不具有强制性。作为描述性原则,格赖斯合作原则自然有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格赖斯合作原则在维特根斯坦自然理解观审角下暴露的问题,可以通过陈嘉映理解的合作原则来解决。会话含义的衡量固然与话语形式及语境相关,但是会话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话语双方在理解上合作,而理解的合作却以共晓性为基础。
格赖斯合作原则;理解的合作原则;自然理解;共晓性
格赖斯合作原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这个老问题却需要新理解。要理解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自然要考察“合作是不是原则”。对此,钱冠连和冯光武二人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观点的差异颇具启示意义。钱冠连关于“合作不必是原则”的论点反映合作原则的“缺陷说”(钱冠连2002:152)。在缺陷说看来,合作原则存在“不足”,出现“危机”而需要“拯救”。冯光武强调“合作必须是原则”折射的是合作原则的概念问题,可以称为“概念论”(冯光武2005)。“缺陷说”和“概念论”代表的是对格赖斯合作原则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的焦点在于理解“原则”的差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从维特根斯坦自然理解观的角度出发,利用陈嘉映提出的“理解的合作原则”来思考“格赖斯合作原则”与“维特根斯坦自然理解”的关系。
理解的合作原则虽然与格赖斯合作原则不尽相同,但是从话语互动的研究维度看,二者却具有相同的研究旨趣:都试图为会话意义的衡量建立客观尺度。然而,格赖斯的客观尺度却遇到来自话语主观理解的挑战。这正是格赖斯合作原则引起国内外学者争论的问题所在(Sperber & Wilson 1986;Travis 1991,1997;钱冠连 2002;冯光武 2005)。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深入思考“原则”与“理解”,然后才能揭示格赖斯合作原则所存问题的实质。
1 对“原则”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考察“原则”一词,为如何看待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做准备。
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与褐皮书》开篇就说,追问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就要追问“解释意义的方式是什么”。他说,这好比要理解“什么是长度”就要弄清我们“怎样度量长度”(Wittgenstein 1998:1)。同理,要明白原则是什么,就要弄清我们怎样看待原则。
我们就“原则”具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从执行主体来看,原则可分为“强制性原则”和“非强制性原则”。强制性原则是硬性规定。作为硬性规定的强制性原则,不允许破坏,不允许违背。强制性原则往往是刚性的,不容改变,而如果一个原则可以任意改变,那么这个原则就是非强制性原则。非强制性原则是柔性的、商讨性的、任意约定的。比如,象棋开步的红先黑后、围棋的黑先白后,这是一种约定。任意约定的“非强制性原则”可以分为无道理的约定和有道理的约定。围棋开棋的黑先白后,这种约定没什么道理可言,但围棋的打劫却有点道理。无道理的约定容易更改,而有道理的约定不宜更改。有道理的约定接近于强制性原则,而无道理的约定不具有任何强制性。
从建立依据来看,原则可分为“描述性原则”和“规定性原则”。描述性原则往往不是行为当事人轻易意识到的原则,而是观察者发现、归纳、建立的原则。描述性原则是一种尺度,是一种检验手段。描述性原则就好比化学实验用的PH石蕊试纸,它可以用来检验溶液的酸碱度,但溶液的酸碱度并不按PH试纸的要求来改变。这就是说,即便没有PH试纸,溶液仍然有它自己具体的酸碱度。描述性原则以客观事实为建立依据,而在没有事实作为根据时建立的原则就是规定性原则。规定性原则可能是强制性的,也可能是非强制性的。
从原则所反映的事理来看,可以分为“事实性原则”和“概念性原则”。世界既有事实也有道理。纯粹描述事实的原则是事实性原则;而揭示事实背后的道理,揭示人类活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极限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概念性原则。如烫伤了手是一个事实,而引起烫伤这一事实的发生可能是另一个事实,如打翻了一杯滚烫的水,但烫伤这一事实的道理却不是打翻了开水这个事实所决定的。事实性原则关注的中心是事实,而概念性原则则是对道理的推导和确立。
所以,提到原则,人们大致会有以上不同的各种心理设定。围绕格赖斯合作原则出现的理解上的差异,正是出于对原则的不同认定。钱冠连关于“合作不必是原则”的观点,其根本道理在于把格赖斯合作原则当成强制性原则。冯光武称“合作必须是原则”,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把格赖斯合作原则当成概念性原则。钱、冯二人都在同一个术语“格赖斯合作原则”下展开论说,但他们的观点瞄准的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对此,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加以评价。钱冠连讨论格赖斯合作原则时,关心语言现象,指出格赖斯合作原则在运用上的缺陷。这种“缺陷说”以具体话语现象为例来反观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解释力,虽然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但没有追究问题的成因。冯光武从概念考察出发,把格赖斯合作原则当成哲学问题加以思考,指出,“合作原则试图揭示言语交际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理性的,合作性是理性的一种体现”(冯光武 2005,2006)。这样的断言属于概括性的观点,但仍需掉转方向从纵深处思考格赖斯合作原则。不同于钱、冯二人,我们的观点是,格赖斯合作原则属于描述性原则,旨在描述会话含义产生的各种情况。
至于合作“必须是”或者“不必是”原则,这样的提法多少带有矛盾的意味。我们觉得,原则总是与遵守和违背相关。如果断言某原则“必须是”原则,那就意味着这个原则至少在某个层面、某个范围必须遵守。然而,遵守又是以违背为存在条件,没有违背就没有遵守,有“遵守”自然就有“违背”。说“遵守”与“违背”,这是从行为主体角度而言的。从客观分析角度看,特别是从分析者视角着眼,“遵守”与“违背”原则对应的是“符合”与“不符合”原则。于是,格赖斯合作原则在“遵守”与“违背”中遭到的质疑实质上成了分析者在讨论“符合”与“不符合”合作原则的具体案例,而不必是对格赖斯原则本身进行是破还是立的讨论。
由此考察,格赖斯合作原则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合作原则是不是原则,而是作为一种理论所必然遇到的解释力问题。只要一个理论不具备普适性,即只要承认格赖斯合作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力,该理论或原则存在不足或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2 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解释力问题
格赖斯从语句意义的表达方式出发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自然意义是事实性的,指语词或语句所携带的意义具有自然属性,与某种自然符号直接相关,如“乌云密布意味着倾盆大雨”等。非自然意义是非事实性的,是指交流中的意图,如语句“他的手势意味着他吃撑了”,这话的意义并非以事实为基础(Grice 2002:291)。非自然意义是格赖斯关注的重点,他的会话含义理论旨在说明为什么在“说话者意义”(相当于非自然意义)与“句子表面意义”之间会出现不一致。(Levinson 2001:16)
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就是他的会话含义理论,就是说发话者所说的与发话者所意图的并不一致,说出的字面意义往往携带含义。比如,我对一个不愿他久留的不速之客说:“左边是出口。”这话的意图是“你可以走了。”
不难看出,格赖斯对会话含义的考察应该以理解为基础,以行为参照系和“共晓性”(common intelligibility)为检验尺度(Rhees 1998/2001)。“左边是出口”和“你可以走了”的关系在理解中确定;没有理解,两者就不会有联系。试想,你对一个疯子说“左边是出口”,那疯子能明白你在逐客吗?所以,说话者可以设置含义,可以用不同话语表达式来传递自己的意图,但是含义传递依赖的不是话语本身而是受话者与发话者之间的共晓性。格赖斯不是从行为参照系和共晓性角度鉴别含义的种类,而是从话语组织方式分析含义何以产生。
格赖斯提出会话的合作原则,旨在分析含义产生的种种可能。在格赖斯看来,一次成功的交谈是参加交谈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要促使交谈成功,参加的人必须是有一个共同交际目的,他们通过交谈要达到某一目标,或者至少有一个被双方或多方都接受的大方向(何兆熊 1989:146,Grice 2002:26)。格赖斯假定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他把这原则称为合作原则。
格赖斯合作原则大致规定话语双方讲真话,不要说假话;说恰如其分的话,不要添油加醋;要直截了当,以事论事,而不要说毫不相干的话;要简洁明了,有条不紊,而不要转弯抹角、语无轮次。在理想情况下,假定每个人说话都这样遵守合作原则,那么会话就没有特别含义,交流就容易成功。相反,对格赖斯合作原则任何一条准则或者几条准则一起违背,交谈就明显伴有含义产生。虽然,在格赖斯看来,遵守与违背合作原则及其准则都可能产生 不同含义,但格赖斯特别关心把what our words say or imply同what we in uttering them[our words] imply区别开来,而且格赖斯认为奥斯汀完全忽视了这一区分,而维特根斯坦似乎否认有这样的区分(Grice 1986:59)。
实际上,格赖斯合作原则并非是一个强制性原则。格赖斯提出合作原则的首要目的不是规定人们会话应该遵守那4条准则,而是假定人们要遵守,在遵守与不遵守的情况下来考察会话含义的生成与理解。应该说,严格遵守合作原则而进行的对话有如在理想语言中进行交流,或者有如数学语言那么精确无误。在实际话语互动中,虽然有倾向于遵守合作原则的情况,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遵守原则。程式性对话中含义较少,容易让人明白。如顾客与店主进行买卖交易的对话,多在合作原则下进行,但我们仍然不能说顾客与店主都在精确遵守合作原则。格赖斯提出合作原则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双方交谈有一个共同目标或有一个共同谈话方向,双方都愿意有成功的交谈。这是一个貌似有理但实为奢求的主观想法。什么叫共同目标,什么叫同一方向,是双方都朝百米赛跑的终点奔跑那样的共同目标或方向吗,还是双方迎面跑向中间某个共同目标吗?如果是后者,那么双方如何知道汇合点刚好就在他们所谓的共同目标点上呢?注意,这些问题正是格赖斯合作原则解释力问题的实质所在。
格赖斯从话语组织方式来计算含义的种类,同时也为含义的产生机制提供解释。在格赖斯看来,在特殊的语境中,公然违背合作原则某项准则产生的含义属于特殊会话含义,而在遵守合作原则各项准则的情况下产生的含义,特别是在一般语境中从用词本身推导出的含义则可能属于一般会话含义。这样一来,违背与不违背合作原则的准则,语句都有不同含义产生的可能。同样,放在不同语境看,所谓违背合作原则的对话其实也是出于真正合作,而有时的合作却成了真正违背。沿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找出许多话语实例来验证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解释力。
莱坎说,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得到普遍认同,但也出现一些批评(Lycan 2008:86-97)。这些批评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斯波博和威尔森(Sperber & Wilson 1986)、莱文森(Levinson 2000)以及戴维斯(Davis 1998)。戴维斯对格赖斯的批评几乎与斯波博和威尔森同出一辙。戴维斯认为,格赖斯的含义推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开始的否定阶段和紧跟其后的肯定阶段。在话语开始的肯定阶段中,受话者探测到发话者意义与字面意思背离,但紧接着受话者得出结论而肯定发话者的真实意义。根据格赖斯的关联准则,会话含义的推导应该始于“说话者不可能是那个意思,因为那话明显不对。”我们知道肯定有某种意义出现,就有运算什么意义将出现的肯定成份。戴维斯认为,格赖斯正是对肯定成份缺乏解释。换句话说,对于发话者明显违背合作原则的话语,受话者要加以快速运算,要推导出他的含义。受话者如果明显感觉到有含义,那么受话者就要计算出正面、肯定的意义来。格赖斯未能指明受话者依据什么肯定成份来推知含义,他的合作原则只是旨在说明什么样的否定成份会导致含义产生。
在我们看来,戴维斯批判格赖斯时所关注的实质就是发话者的语句如何与受话者对听到语句的理解问题。于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是否恰当和它们同说话者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制约主观理解。为此,须要指出,评价格赖斯合作原则及会话含义,应该从理解角度切入,从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论切入。
3 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论
自然理解论的核心观点是,“理解是一个自然的、直接的、无中介的过程。当然,有时需要解释,需要中介,但最终要来到直接理解”(陈嘉映 2003:209)。话语互动中,受话者听到一句话,通常直接就理解了。在所听到的话语与理解之间,不需要什么中介。自然理解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维特根斯坦倒转各种意义理论关于理解的思考方向。指称论、观念论以及图象论等意义理论希望在语句与理解之间搭建桥梁,跨越从语句到理解的鸿沟(陈嘉映 2003:208)。
在《哲学语法》中,维特根斯坦集中讨论语言的理解问题,所表达的观点与后期著作《哲学研究》的相应观点一致。他认为,“科学和数学使用命题,却没有谈到对这些命题的理解”,而对命题的理解恰好是哲学应该关心的重要问题。对于“理解”一词,维特根斯坦看到了它的双重意义:“在下棋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再一次地看到‘理解’一个词的双重意义。当一个会下棋的人看下棋时,他下棋的经验总是不同于某个不会下棋但正在看下棋的人。(他的经验也不同于一个根本不知道下棋的人的经验。)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这种关于下棋的规则的知识使两个看下棋的产生了差别,而且同样正是关于规则的知识使那个看下棋的会下棋的人有他所有的特殊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有关规则的知识。可是我们乐于把它们叫做两种“理解”(维特根斯坦 2003a:40)。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两个观棋者的差别在于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如果理解就像下棋,那么真正的理解在于会下棋。这就是说,理解一个词语就是知道如何使用这个词。“应用始终是理解的一个标准。”(维特根斯坦 2001:89)维特根斯坦说,“请记住,一个人不理解一个词,这事情是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明的:这个词对他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拿这个词干什么。也有‘他以为理解了这个词’的标准:把某种含义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不是正确的含义。”(维特根斯坦 2001:144)这话可以用以下话例来说明。大毛、二毛两小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零食,三毛眼馋地问:“你们在吃什么?”大毛冷冷地回答“甭管”。听到这话,三毛跑去向妈妈告状:“妈妈!哥哥在偷吃‘甭管’,我也要吃‘甭管’”。显然,三毛在没有学会“甭管”时而接受这个词,于是没有真正理解。他误把“甭管”当成一个指代某种零食的名称而误用。这说明理解发生在语言中,发生话语互动中。语言理解是话语互动的关键。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解论,弄清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是弄清语言的实际使用。
维特根斯坦利用语言游戏来考察我们的语言理解情况,为话语分析提供新的意义分析单位。传统分析中,语言的意义单位要么是词、话语片断,要么是句子等,这些都是出自语言学的考察手法。立足于语言使用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发现,人类、世界和语言这3类因素紧密交织。即简单的语言游戏就是这三类因素交织而构成最基本的复合体,是我们考察语言意义理解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2001:8)。语言游戏视域中的意义问题和理解问题具有活生生的特性,语词离开具体的使用和理解,就失去生命。
语言意义的理解问题就是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离不开对语言的具体使用。语言学的传统分类把语言的意义置于语义学内,而把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归在语用学领域。实质上,离开具体的使用活动,“语言的意义问题”和“意义的理解问题”就不能紧密关联起来。维特根斯坦打破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分界,从而使语言意义的理解成为语言意义研究的合理内核。语言意义的单位也就是意义理解的单位。
“以语言游戏作为理解语言意义的原初单位,为我们洞察使用者如何理解语言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张学广 2003:175)我们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以系统整体方式建立起来的。一个词的意义和理解并不是单个地被确定的,而是系统整体地确定。行为和生活是理解语言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的逻辑基础,是我们能够理解和使用语言的原始保障,给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以确定性,使我们的理解活动成为原始现象。这里所谓的原始,是指先于语言的行为方式,“语言游戏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原型而非思考的结果”(维特根斯坦 2003b:241)。
话语互动的双方如何就一个词或句子达成相互理解呢?如果按照洛克的说法,受话者理解发话者所说的话语片断或语句,其基础就在于两个人心中拥有同样的观念。这一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但话语互动并不是单纯地进行观念对等的核对,就是说如果我指着餐桌上的盐瓶说“盐”,我并不是在指物命名,你也确实明白我需要给汤里加盐而顺手把盐瓶递给我。话语互动不是追求观念的一致,而是在共晓性的基础上相互理解。显然,一个人对一个语词有正确的理解或者两个人能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来自语言的原始根基——行为参照系和话语共晓性。没有行为作为参照,我们无法学会语言,无法理解听到的话;没有共晓性,我们无法就某一个语词或语句形成相互理解,我们之间就没有话语的可能。理解说出的一个词或句子,就是理解一个特定的行为,而不是理解他人心中的观念。
一个人能理解语言,因为他有与这种语言对应的生活形式,而这种生活形式赋予语言共晓性。同一种生活形式让同一种语言具有理解的可能。对理解的可能性的研究就是逻辑研究,而对词的可理解性的研究,即对一个人如何能恰当地使用一个词做事的研究,就是概念研究。一个词的可理解和可恰当地用于做事,归结于它被安置在许多圈层的其他语词中,即被安置在一种语言中,它来自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在生活形式中呈现什么特性呢?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里蕴含的道理是什么呢?在维特根斯坦的学生里斯(Rhees)看来,这里蕴含的是语言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合。话语互动的基本成分是语词,同一语词可能会在不同对话中出现,但却不能就此推断说,使用同一语词的不同对话就有必然联系。为什么呢?我们的语词隶属于同一种语言与我们的语词隶属同一个对话,这两种隶属关系虽然相似,但却有根本的区别。隶属同一语言是形式关系,而隶属同一对话却根本不可能,因为根本就没有同一的不同的对话。对话在本质上是联合,是思想或生活的联合,而不是一种语言形式的联合(Rhees 2001:108)。语言的联合,即各种语句汇聚一体,不是积分式的联合,也不是游戏规则式联合,而是共晓性的联合,其本质就在于话语参与者能相互明白(Rhees 2001:241-243)。
话语互动中的正确理解并非仅仅依赖于命题之间的形式关系,并非一味关注这一句是不是出自那一句,这一句是否可以取代那一句等逻辑演算问题。正确的理解,一方面强调的是话语参与者在互动中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正确的理解并不能完全离开对话语本身的理解。既然话语互动是以共晓性为基础,那么要揭示人们相互理解的实质,就是要弄清各种语句在实际使用中如何汇聚成统一的整体,即要弄清话语互动的双方何以达成话语连贯。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论指明理解的原始基础——理解语词用法所依赖的行为参照系和基于共晓性的相互理解,同时还指明理解的流动性——由于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语言联合的不完备性,话语双方纵有理解的原始基础作为保障,理解也不可能总是按既定模式发生。也就是说,即便是自然理解,话语双方达成的理解是在话语互动的实际情况中产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这真是意外之喜”等话语的产生,就是基于意外理解达成后而发出的感叹。话语互动的相互理解既可能是把话语朝共同期望的方向推进,又可能是产生不同方向的推进。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双方都可能达成理解。维特根斯坦说,“理解等于把握,等于从对象获得一种规定的表达,让它自己作用于自己。让一个句子影响自己;考察句子的结果,就是想象它们”(维特根斯坦 2003a:75)。
4 陈嘉映理解的合作原则
人有追求理解的天性,否则人就不会理解任何事情。如果一个人总是抬杠,其目的就是抬杠,除了抬杠别无他事,那么这个人可以永远找到可以质疑的东西,即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认同可言。理解虽然是流动的而且没有终极标准,但是理解终究可以达到。陈嘉映把理解的这一特征称为“理解的合作原则”(陈嘉映 2003:210)。虽然陈嘉映没有具体分析理解的合作原则,但他就该原则的基本原理作了大致说明。在他看来,理解的合作原则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原则而是一个描述性原则,旨在描述我们事实上怎样达到理解。
人们在话语互动中怎样达成理解,这正是话语意义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们沿着陈嘉映的路子力图发展与补充理解的合作原则,以解释话语意义的理解机制。
格赖斯从话语的组织方式入手提出会话的合作原则,并以合作原则为尺度来检验会话含义的产生情况。然而,格赖斯的客观尺度却遇到来自话语主观理解的挑战,即对于话语互动的一些现象,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解释力失去应用效用。为此,钱冠连分别从质、量、关系和方式等4个方面提出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反例,从而断言“合作不必是原则”。他说,“合作不必是原则的最后依据是,说话本来就是在目的-意图的驱动下实现的,与双方是否持合作态度基本无关”(钱冠连 2002:158)。钱冠连提出的“目的-意图原则”与其说是对Grice合作原则的拯救,还不如说彻底抛弃它。在我们看来,“目的-意图原则”与斯波博与威尔逊的关联理论一样,企图对格赖斯留下的问题另求它解。面对格赖斯问题,换种解法固然可取,但重要的是充分剖析问题的实质。
格赖斯关注的是一个给定语句由于信息的真假、信息量的多寡、信息组织的言说方式以及信息的相关性等语句自身的特点,可能传递不同的意义,甚至可能导致交际失败。于是,格赖斯假定会话双方具有一种合作的默契,从而避免交际失败。应该说,格赖斯已经注意到“语句的意义”和“语句意义的理解”问题。在维特根斯坦自然理解论的视域中,这两者紧密联系成一体,而格赖斯却强调二者的分离。仿佛在格赖斯看来,语句的字面意义具有存在的地位,受话者对语句的理解又可能出现另外的意义,这个另外的意义也有它的存在地位。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冲突,要消除这一冲突,就需要双方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在格赖斯看来应该体现在话语的组织方式上。然而,话语双方赖以对话的基础并非话语形式,而是双方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话语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对于一个语词的理解,就是双方知道这个语词的具体使用;对于一个语句的理解,就是双方知道,这一语句在具体的使用场合中与哪些另外的语句汇聚成联合体,这联合体就是共晓性的联合。孤立的一个语句,即未进入实际实用的语句,根本无意义可言。对语句的理解就是对语句用法地位的界定,而语句的用法地位就是具体场合中语句在共晓性联合中占有的地位,是理解的产物。试看钱冠连所举的关系上的不必合作的话例:
① 语境:1961年,华中师范大学学生餐厅,学生向厨工递碗打稀饭的同时必须自报所需分量。但一学生忘了报告分量。
厨:(气势汹汹)怎么不开腔?
学:(反感于厨工的凶恶态度)开枪?开枪把你打死了怎么办? (钱冠连 2002:156、157)
这一话例没有格赖斯和钱冠连所讨论的合作但却有理解的合作。这里凸现的话语脉络贯通,是“情脉”与“语脉”的贯通(杜世洪 2008:203)。学生理解到“怎么不开腔”的使用情绪,于是在“腔”字上“借音脱跳”,转到“枪”,而使用“开枪?开枪把你打死了怎么办?”这样的语句作答,同样是在情脉上达成共晓性。这里,厨工和学生语句的字面意义不起主要作用,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去解读,二者的对话确实不相干。
当我们说这例话语具有理解上的合作而不具有格赖斯和钱冠连所谈论的合作,这就出现了对“合作”的不同理解。总体上讲,“合作”趋向同一。合作容易让人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去理解。说某人很合作,多半指出他的行为、话语等符合我们的要求。说大家必须合作,就是要求每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再各执己见,放弃原来的分歧。格赖斯的“合作”概念是指话语双方都遵守同样的原则,在同一个话题下组织话语,会话服务于同一目的或者符合同一方向。而我们所说的理解的“合作”,是指话语双方在同一语言联合中指向话语共晓性。
从格赖斯合作原则出发,结合陈嘉映对理解的合作原则的界定,我们发现应该从理解的合作原则来揭示话语互动过程中会话双方实现交流、达成理解的机制。
话语互动具有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脉络贯通,而话语互动的脉贯可能由语脉、或意脉、或情脉、或理脉的凸现来实现,也可由多种脉络的结合来完成。正常的话语互动都有脉络上的连贯,因而话语理解是在把握话语脉络连贯的基础上,话语双方在凸现的脉络上追求最大的共晓性。为此,理解的合作原则就是——理解是话语双方在凸现的脉络层面上追求话语最大的共晓性。这是理解的合作原则的总原则(杜世洪 2008:202,208-241)。
理解的合作原则不是强制性原则,而是描述性原则。理解的合作原则作为一个检验理解程度的尺度,不是要规定如何理解,而是要考察理解如何围绕这个尺度进行。“自然理解”以追求最大共晓性为目标。
因此,回到常识层面,可以说话语互动的理解就是话语双方顺着某种凸现的脉络进行剖析。话语理解的合作就是在某一脉络层面上追求最大的共晓性。试看下例:
② 刘备: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赵云: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三国演义》,第42回)
从格赖斯合作原则看,刘备与赵云二人的话毫无关联。虽然违背关联准则可以产生含义,但前提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会话的共同方向。字面上、语境中都看不出刘备与赵云的这一轮对话具有明显的目标,所以利用格赖斯合作原则无法充分分析这一对话。另外,从衔接理论的角度看,刘备与赵云的对话也没有衔接点,衔接理论对此无法解释。然而,从理解的合作原则看,刘备那“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在其场景中起的作用是情感的表达,字面意义或者语句意义不是交流的核心。赵云理解刘备的恩情,也及时表达出感恩之心而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刘备与赵云在情脉凸现的层面上相互明白而达成共晓性。(杜世洪 2008:203)
钱冠连在论述“合作不必是原则”时,分析了信息量的多寡情况,称人们有时具有“多余消息欲”,有时要求说话人多给点信息(钱冠连 2002:155)。如果把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奉为交谈的铁定标准,那么生活中反而会出现交谈失败。格赖斯合作原则是描述性原则,并不具备普适性。况且,量的准则虽然明确指出会话双方应恰如其分地给出信息量,但是什么叫做恰如其分,什么叫做不多不少给出适当的信息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信息量的恰当只是一种感觉,信息量的多少是双方在交谈中的感觉,而且是一个动态概念,具有弹性,没有刚性标准。比如说,“阿拉木罕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这也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和一种感觉。你要是说56公斤重,1米65高就叫“身段不肥也不瘦”,那么从这一个案中提取出来的数据并不具有普适性。
钱冠连举出的那一言语交际事件,虽然不能从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角度得到充分分析,但可以从理解的合作原则层面进行揭示。
③ 顾客:有瓶胆卖吗?
卖主甲:没有。
卖主乙:没有。您晚了一步。
卖主丙:没有。您晚了一步。南京东路三号有的,您快去。(钱冠连 2002:155,156)
按钱冠连的分析,卖主甲的回答符合量的准则要求,可以得满分。而根据人有“多余信息欲”的要求,卖主丙的答复最佳。应该说,钱冠连的分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我们觉得这一话例更适合用理解的合作原则来分析。从理解角度看,那可以得满分的卖主甲的话虽然能让顾客明白,但却不能让顾客对“没有”瓶胆卖这一事实得到最佳理解。你说“没有”,我当然明白“没有”二字的符号意义,但我不理解“没有”在此处的用法。维特根斯坦不仅说理解一个语词就是知道它的使用,而且还强调“理解是一种解释关系,”“对于意义的解释可以消除与意义有关的任何不同意见。它可以消除误解”(维特根斯坦 2003a:51)。由此看来,卖主乙和卖主丙的答话却具有理解的合作态度。他们分别解释“没有”,帮助顾客理解“没有”。卖主丙不但解释“没有”,而且还按事理的发展指明哪里还有。卖主乙或卖主丙同顾客产生的买卖中,双方在话语互动中的理脉层面上达成理解,形成理脉连贯。这里的理脉之理就是合乎事情发展之理(杜世洪 2008:204)。
5 结束语
追问话语的意义是什么,势必追问衡量话语意义的手段是什么。格赖斯合作原则作为检验会话含义产生的衡量指针,能够指出符合该原则解释范围的具体话语的可能性含义,但不能完全揭示意义产生的理解原理,因为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基本前提是语言和逻辑的充分分析,把意义的产生锁定在语言组织的形式规律上。如果在语言组织的形式规律上出现明显的违背原则的情况,在格赖斯看来就有含义的产生,而即便在遵守原则的情况下,也有含义产生。格赖斯能在形式上指明话语产生含义的可能性,但却不能揭示含义产生的内在机制。格赖斯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自然理解论角度加以剖析。理解的合作原则关注的焦点不是语言形式,尤其不是以语言形式为分析单位,而是认定“语言形式所代表的共晓性的联合”。话语双方如能在共同的脉络层面组织话语,双方就有共晓性的达成。共晓性是话语双方的内在贯通,在语言形式上以语句的匹配关系来显现。根据理解的合作原则,可以通过揭示理解层面来衡量话语的意义;话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在语言的形式单位上,而是在话语双方的理解中显现。总之,检验含义产生情况的有效途径就是查看这句话在话语共晓性联合中的具体使用情况以及查看这句话会与什么样的其它话语发生匹配关系。会话含义的衡量固然与话语形式相关,但是会话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取决于话语双方理解上的合作。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杜世洪. 脉辨——论话语互动的连贯基础[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冯光武. 合作必须是原则——兼与钱冠连教授商榷[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5).
冯光武. 理性才是主旋律——论格赖斯意义理论背后的哲学关怀[J]. 外语学刊, 2006(4).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维特根斯坦. 哲学语法[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a.
维特根斯坦. 纸条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b.
张学广. 维特根斯坦与理解问题[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Davis, W.Implica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ice, P. Reply to Richards[A]. In Grandy, R. and R. Warner(eds).PhilosophicalGroundsofRationality[C]. Oxford: Clarendom, 1986.
Grice, P.StudiesinthewayofWord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Levinson, S. C.Pragmatic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Levinson, S. C.PresumptiveMeaning:TheTheoryofGene-ralized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Lycan, W. G.PhilosophyofLanguage:AContemporaryIntroduction. 2nded.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Rhees, R.WittgensteinandthePossibilityofDiscour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2001.
Sperber, D. & D.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 London: Blackwell, 1986.
McCarthy, T. & S. C. Stidd.WittgensteininAmerica[C]. Oxford: Oxfro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ravis, C. Critical Notice: Annals of Analysis [J].Mind, 1991(100).
Travis, C. Pragmatics [A]. In Hale, B. & C. Wright (eds).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Language[C]. London: Blackwell, 1997.
Wittgenstein, L.TheBlueandBrownBooks[M]. London: Blackwell, 1998.
【责任编辑李洪儒】
Grice’sCo-operativePrincipleandWittgenstein’sNaturalUnderstanding:A Response to Qian Guan-lian and Chen Jia-ying
Du Shi-hong Li Ju-li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Qian Guan-lian and Feng Guang-wu have differed insightfully from each other in interpreting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ir inspiring insights manifest a need for reexamining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Being descriptive rather than compulsorily prescriptive,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suffers a problem of inadequacy in accounting for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ttgenstein’s natural understanding, the inadequate accountability of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can be satisfied by Chen Jia-ying’s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understanding. Thus, a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that although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an be calculated through the linguistic form in terms of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meaning of conversation is never fixated on linguistic forms but generated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scourse participants, whose cooperation in understanding is grounded in their common intelligibility.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understanding; natural understanding; common intelligibility
B089
A
1000-0100(2012)05-0009-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话语理解中他心语境与语义连贯的互动关系研究”(12BYY122)的阶段性成果。
2012-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