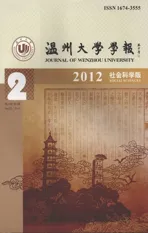生与死的辩证法
—— 论方方近期小说对生存哲学的思考
2012-03-19姚慧
姚 慧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生与死的辩证法
—— 论方方近期小说对生存哲学的思考
姚 慧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方方对死生这个哲学命题的思考,已经融入了她的创作中,而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作家对死和生的态度也并不相同。如果说在“新写实”时期,方方以死亡为视角,以零度写作的叙述态度来窥探生存的琐屑和人性的卑微、丑陋,那么在她近期的作品中,她则以人道主义视角为我们还原了人类生存的本相。方方在创作中,关注的焦点、叙述态度和哲学思考都出现了转向。这三个方面的转向分别是:从消解生命的价值到对生命韧性的关注;从悲情主义到温情主义;从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
方方;近期小说;生存哲学
方方对于生与死的模式的关注,贯穿了她大部分小说。《风景》①参见: 方方. 风景[C] // 方方. 祖父在父亲心中.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下文中《白驹》、《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行为艺术》、《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和《暗示》均出自同一文集, 不再一一注出.中以死去的小八子的眼光,窥见七哥的生;《白驹》以王小男为了1 500块钱毫不崇高的死,来反衬麦子和春夏秋冬百无聊赖的生;《祖父在父亲心中》中以祖父壮烈的死与父亲怯懦的死作对比,来反省两代人之间“生”的差异,展现现代人的精神萎缩;《埋伏》中科长身患绝症却坚持埋伏,最后因耽误病情而死,换来的却是一场闹剧;《行为艺术》干脆把人生当作一场行为艺术,以一个复仇故事的了结换取对人生的另一种理解;《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则更加完整地叙述了“僵尸佳丽”黄苏子人生的开始和终结。而方方的近期小说《水在时间之下》②参见: 方方. 水在时间之下[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下文所论同一小说, 不再一一注出.,以一次次死亡事件,推动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和心灵的转变。《琴断口》③参见: 方方. 琴断口[J]. 十月, 2009, (3): 5-34. 下文所论同一小说, 不再一一注出.中,作者更是用桥的崩裂,将死和生紧密相连。
方方对死与生这个哲学命题的思考,已经融入到她的创作中,但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作家对死与生的态度并不相同。如果说在“新写实”时期,方方以死亡为视角,以零度写作的叙述态度来窥探生存的琐屑和人性的卑微、丑陋,那么在她近期的作品中,则是以人道主义视角为我们还原了人类生存的本相。读方方近期的小说,总能感觉到在她波澜不惊的叙述下潜藏着一种尖锐的疼痛。这种疼痛,在社会生活现实冲突的表面,蕴藏着人性与生命的两难对立。她将人物不断地置于各种伦理观念、欲望及人格尊严的对抗中,在保持强劲叙述张力的同时,凸显了一个个无助而又无奈的人生场景。而从新写实到近期创作,方方在关注视角、叙述态度上的转向也是明显的。
一、关注视角的转向:从消解生命的价值到对生命韧性的关注
方方在新写实时期,与同类作家一样,善于在琐屑中描写生存的无奈。她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则比同类作家更加尖锐,她利用小说中主人公们的生命过程向我们表述:一旦丧失了自我精神,人的生存与死亡,就如同自然界的万物的生长和消亡,来去没有意义。人生的价值被消解了,理想主义精神消失了,生命与崇高毫无瓜葛,小说里的人物就开始处于一种不自知的迷失状态,没有精神支撑,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如《风景》里的七哥,《落日》①参见: 方方. 落日[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 下文所论同一小说, 不再一一注出.里的一家子,《在我的开始在我的结束》里的黄苏子,《白驹》里的王小男、麦子、春夏秋冬等等。
以《风景》为例,从死去的小八子眼中看到的奇异世界,不再只是11口人在13平方米内拥挤不堪,粗俗不堪地维持着动物本能的生活,而是沦落的心灵世界。在这个“奇异世界”里,人如行尸走肉一般,于是生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七哥的生存哲学在小说开头就有交代。“七哥说,当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你才会觉得自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你才能天马行空般在人生路上洒脱地走个来回。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七哥把人生当作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过程,道德,信仰,这些人类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主体精神,都被他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于是只剩下一个被生存本能占有的兽性世界。生的外壳下包含的是死的内核。又如小说中二哥的凄惶苍凉之感:“生似蝼蚁,死如尘埃。这是包括他在内的多少生灵的写照呢?一个活着的人和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死者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说他们本是活着的而世间芸芸众生则是死的呢?死是不是进入了生命的更高一个层次呢?”方方把自我精神丧失的人们看成是飘荡在人世的阴魂,“这些阴魂不知道自己死了。他们很自豪地认定自己在阳世而且活得很舒服。”
在《落日》中人生的价值也同样被消解了。《落日》中的祖母死去又活过来,再死去,她的死和生都没有任何价值,更与崇高无关,就像一缕白烟,飘散了就散了,也未能换回儿孙们人性的觉醒。儿孙们卑微地活着,为自己的生存挣扎,不惜碾碎亲情和人伦,把未断气的老太送入火葬场,他们的生同样没有价值。落日就像一个寓言,死亡不再只是躯体的僵硬,而是精神的沦落。丁老太躯体的死,与活着的儿孙们的精神之死融为一体。生的外壳下包裹着的是死的内核。这种死生一体化成为方方这一时期的小说关注的焦点。
而到了近期,方方的小说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向,她对生命积极那一面的关注似乎更加强烈,虽然生命之痛贯穿着她的小说始终,但“人”字开始大写,生命的韧性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正如方方自己所说:“也有一些人,人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好像冲他而去,他痛苦他悲伤他哭泣,但却都承受了下来。依然清醒而理智,依然从容而坚定,依然一丝不苟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如此地活在世上就仿佛是要专门证明给人们看:生命到底有怎样的坚韧。”[1]人生也不再只是无意义的自然界的循环过程,主人公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对迷失的自我的寻找也成为另一个主题。
在《万箭穿心》①参见: 方方. 万箭穿心[J]. 中篇小说选刊, 2007, (4): 49-88. 下文所论同一小说, 不再一一注出.、《琴断口》、《水在时间之下》等小说中,方方对人的生存与死亡问题的探讨有了明显的转向:人物一改以往小说中的麻木和妥协,他们开始积极寻求生的意义,历经磨难之后寻求自我的存在价值,这是方方从新写实的灰暗无奈中挣脱出来的一个标志。人物自我意识开始复苏,生不再是死的另一种载体。
《万箭穿心》中的李宝丽,丈夫的自杀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赎罪般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近乎自虐般地想用拼命劳动来换取内心的踏实。一个如花般的女人,像个男人一样用扁担和卖血支撑起了这个家。为此她还拒绝了能给她爱护的男人,拒绝了幸福的机会。她的坚强和忍耐换来的却是公婆的冷漠和鄙夷,儿子的仇视和残忍。儿子就是她的命,也是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当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供养大,指望着他出息了能让她能喘口气,但儿子回报给她的却是把她一脚踹开。儿子买了别墅,卖掉了她的房子,把爷爷奶奶接过去享福,却让她这个当妈的流落街头。她的心被无数支利箭穿透了,她没有选择去和儿子打官司,房子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幸福的意义。在故事的结尾,李宝丽没有就此沉沦下去,她搬去和其他扁担工挤在几平米的出租房,她苍老而憔悴,痛定思痛之后也就释然了,以往都是为别人活着,为公婆,为儿子,从这之后,她决定要为自己而活着。
《水在时间之下》中,哥哥水文的死,林上花的双腿被炸断,陈仁厚的出家让水上灯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意义,最终看破了欲望和仇恨。方方特地设计了一座桥,桥的这边是“放下着”,桥的那边是“莫错过”。水上灯从桥上走过,从放下仇恨,到莫错过挚爱亲情,心灵得到了涅槃。虽是万箭穿心,终究豁然了。故事的后面,水上灯遇到了引发她仇恨的源头——同父异母的哥哥水武,照顾他成了她活下去的意义。虽然她最终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与街井妇人无异,但活着也成为生命韧性的诠释。由此看出,方方关注的焦点有了明显的转向。
二、叙述态度的转变:从悲情主义到温情主义
方方不仅在关注焦点上发生了变化,在叙述态度上的变化也是明显的。从知识分子审视人类生存本相的零度叙事,逐渐过渡到平民视角下的“有温度”叙事。在对小说中人物生死模式的观照中,方方似乎开始改变年少气盛的尖锐,犀利,予以更多中年的宽容,温情。作家看世界,关注人物生存的眼光,变得更加平和。
虽然,作家一再强调,自己在写作时是个悲观主义者。这种悲情也始终贯穿着她的小说,在新写实时期,方方关注的是:自私、自我的本质使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生存立场上,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而牺牲人伦、亲情、道德,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理想而反抗、挣扎的境遇。在近期,方方则更关注人反抗自身的矛盾和困惑。如《琴断口》和《刀锋上的蚂蚁》都反映了人内心的一种纠结,焦躁不安的状态。人们反抗的不再是社会,他人,而是自己无法平复的内心。《琴断口》中蒋汉的死始终困扰着幸存的杨小北和米加珍。拉康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镜子的关系,人始终妄图在他人这面镜子中找到自己。杨小北和米加珍就是无法忽略看客们眼中的自己,并加以扩大化,从而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们把蒋汉的意外死亡归咎于自身,因此自己的人生成了悲剧。《刀锋上的蚂蚁》更表现了人内心的一种焦灼状态,鲁昌南似乎是在尖锐的刀锋上爬行的蚂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疼痛而小心翼翼。甚至《万箭穿心》中李宝丽的悲剧根源也不再是生存境遇的恶劣,而是她内心把丈夫的死当作自己的罪恶,用赎罪来平复内心。《水在时间之下》的叙述重心也不在于水滴对命运的反抗,而是内心爱恨、善恶的挣扎。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方方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挣扎的冷漠叙述中,转向了对人物爱恨纠缠,自责和赎罪等人物内心情感的有温度叙述。在这种从“他人即地狱”转向“自我即地狱”的过程中,方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述,也融入了几分温情。如《万箭穿心》中李宝丽和万小景之间的友情,建建对李宝丽的关爱,李宝丽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等等。《水在时间之下》中且不说水滴和杨二堂、万江亭、余天啸和菊妈之间的亲情,与林上花的友情,与陈仁厚的爱情,就连她和玫瑰红之间的争斗也偶尔会染上几丝怜悯和惺惺相惜。张晋生对水滴的虚情中也有几分真意,哥哥水文也因血脉相连而倾力保护水滴。人的真挚情感与人性中善的部分在方方小说中得到更多的确认,这是以往她的小说中所回避的。
方方认为人的生命是有张力的,如果这种张力在新写实时期表现为愤懑和颓丧的话,死亡被作为一个与生的无奈相对立的安宁的所在,死亡被看作是一种解脱。如《暗示》中死亡的暗示,“扑通”一声巨响,叶桑最后一线思绪是“纵是下坠也是升腾”。的确,“这个早晨的灿烂需要叶桑横空出现才能完成。”这样的死是从容,是历经心痛后的平静,是决裂,是最沉重的谴责,是最激烈的反抗,叶桑用这种方式实现回归精神家园的强烈追求[2]。死亡被当成释放灵魂的出口。但在近期小说中,死亡则不再被当作一种出路。人们在庸常的人生中的种种无奈,则被当成一种生命过程,不再完全被否定。
三、对死亡意蕴和生命价值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
在关注焦点和叙述态度的转变中,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窥见方方对死亡意蕴和生命价值的思考的转向。
“在死亡的映照之下,出于独特的生存状态,人们总是力求最深刻最彻底地把握自己与世界、生存与价值、生存与永恒的关系,进而希望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解决自身在世界中的命运问题,也正是这种最根本的探索与冲动,才产生了作为对人们命运之问的某种终极关怀与承诺的宗教和哲学”[3]459。对生存意义的探讨,也成为方方小说中一个内在的共同主题。在新写实时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几乎成为方方写作的出发点。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更为深入。“黄苏子生下来那天,她父亲正坐在医院的走廊上读苏轼的词。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对于老婆生不生孩子或这回生成什么性别他都无所谓。”黄苏子是在这种无所谓中出生的,她的名字也因为一个多嘴的女医生而变成了“黄实践”。而在文革结束后,父亲在文革批判会上的发言又使她重新变成了“黄苏子”。在方方平淡的叙述中,我们隐隐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表现为荒谬的偶然性充满人的整个存在,就人作为一个软弱而有限的生灵赤裸裸地‘被抛入’世界而言,荒谬感就是偶然性,一切都是荒谬的偶然存在:死亡、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异化等等,也就是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找寻不到生存的意义,我们猛然发现自己就在这里,没有人‘请’我们来;也没人‘准’我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3]451
黄苏子就是这样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不知道她是谁,她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一切只因为偶然。她来到这个世界,她的性别,她的名字都是因为偶然。“事实上,海德格尔描述这个概念的德语词Geworfenheit直译过来就是‘被扔’的意思。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挑选过父母。我们却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天赋的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完成我们的生活。”[3]451如果非要给生命寻找一个意义,是爱,是精神支撑着我们走下去。而爱的缺失,使黄苏子成为一个牺牲品,她的生命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洞。父母、兄弟姐妹给她的是冷漠,她回报的同样是冷漠和更深的厌恶。青春期的无知毁灭了她年少时第一次被爱的机会,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爱别人的机会。当年少时自尊心受创的许红兵再次找到黄苏子时,黄苏子以为她得到了真爱,然而当她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复仇计划中的报复对象时,她的灵魂被彻底撕裂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最终使角色扮演的游戏变成了一种夜幕降临时的真实生活。“僵尸佳丽”成为真正的僵尸:白天她是冷漠木头般僵硬的白领,到了夜晚她就成了浓妆艳抹的妓女,不挑嫖客,不挑卖淫的环境,不论价格。不为金钱,不为情欲,黄苏子的人生随着心灵的死亡而宣告死亡。她的生存茫然而无目的,她最后躯体的死也只是另一种偶然的结束。“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燃尽的玫瑰留下的一切的灰。悬在半空中的尘土,标志着一个故事的终结之处。”黄苏子的生命“如同尘土如同水珠,无意之间便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一声轻叹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听到。”生出于偶然,死也出于偶然,没有崇高和伟大以及一切理想精神,方方还原了生存本相,也打破了死亡和生存的界限。生存和死亡都变成一种行为艺术,充满荒诞色彩。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可以归为两点:一是把自我意识作为存在的核心。把自我与世界置于敌对的地位。认为人在冷酷陌生的荒谬世界中孤立无援,经受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二是认为只要人认识到这种存在的荒谬。就可以通过行动的选择来使存在获得意义。这两点里包舍了一个‘自我’的‘迷失’、‘寻找’与‘确立’的过程。”[4]萨特等哲学家也正是在这种“寻找”与“确立”中拥抱人道主义。方方近期小说中,主人公也正是在经历了自我的迷失之后,试图寻找和确立自我。《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水上灯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先是在仇恨中迷失自己,造成了身边人的悲剧。后来又在漂泊不定之中寻找,最终确立起来的是由爱和仁义支撑的稳定自我。虽然最终这盏明灯被湮没在时间之下,但这个如花的生命不再只有虚空和弥漫着毒素的美丽。《万箭穿心》中李宝丽也是在迷失中重新确立自我,李宝丽这个泼辣女人,对丈夫刀子嘴,但在内心却是真心实意地渴求幸福。丈夫的自杀,让她的精神处于一种迷失状态,她把所有的罪责都背负在自己身上,通过牛马一样的劳作来“赎罪”,然而当她在心底构筑的充满天伦之乐的乌托邦被儿子彻底毁掉时,她的自我确立也就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具有传统的中国式伦理观念的妇女,毫无怨言地为儿子牺牲一切,换来的是儿子的仇恨和践踏,原本激发她坚强地活着的动力也就不存在了。然而新的动力出现了,即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认可,活着不是为了赎罪,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自我的尊严和价值。当李宝丽毅然扛着一副扁担,搬进了一块五旅馆。我们不禁潸然泪下,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究竟可以承受多大的苦难,而坚强至此。
即便是《琴断口》和《刀锋上的蚂蚁》,作家没有给主人公们找到一条回归之路,作品指向一种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然而,在对主人公精神迷失的探寻上,方方仍留有一些空白,如《琴断口》里杨小北的离开,《刀锋上的蚂蚁》①参见: 方方. 刀锋上的蚂蚁[J]. 中国作家, 2010, (5): 4-38.里的鲁昌南和费舍尔的对比。方方在写作中没再像前期一样,用死亡来使人物解脱,而是暗示这种寻求自我确立的“在路上”的过程。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新写实到近期的小说创作,方方对生命意义,对死亡意蕴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对生存和死亡的辩证思考也从未停止。但小说在关注焦点、叙述态度、哲学思考等方面有了明显转向。如果说方方在新写实时期是一个纯粹的悲情主义者的话,那么在近期,她开始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人生不再被看作完全的荒诞和无意义,她为我们涂抹上几分亮色,几分温暖。
[1] 方方. 生命的韧性[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54-55.
[2] 温惠宇. “暗示”的力量: 评方方《暗示》[J]. 当代小说, 2009, (7): 32-33.
[3] 王志军. 荒谬与超越: 从死亡的视角看哲学和宗教的冲突与融合[C] // 衣俊卿. 哲学之路: 第1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4] 赵利. 自我的迷失、寻找与确立: 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自我”的“确证”过程[J]. 时代文学, 2010, (12): 32-33.
Dialectics of Life and Death—— Study on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in Fang Fang’s Recent Works
YAO Hui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China 230039)
Fang Fang has already integrated her thought about life and death which is a critical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into her creation, and in different creative periods, she take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In the “New Realism” period, Fang Fang explores trivial survival as well as humble and ugly humanity in the way of taking perspective of death and attitude of indifferent writing. However, in her recent works, she restores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uman survival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arian.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Fang Fang has changed her focus, narrative attitude and the way of thought. The three changes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from the digestion of life value to the care for tenacity of life; from sadness to Paternalism; from existentialism to humanitarianism.
Fang Fang; Recent Works;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I206.7
A
1674-3555(2012)02-0042-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2.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1-02-28
姚慧(1988- ),女,安徽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