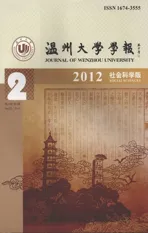“重”与“轻”的两维视域
—— 论新世纪以降迟子健东北地域小说的审美风格
2012-03-19潘海军
潘海军
(长春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重”与“轻”的两维视域
—— 论新世纪以降迟子健东北地域小说的审美风格
潘海军
(长春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迟子健的东北地域小说创作,存在着“重”与“轻”的两维视域。这里的“重”蕴含着苦难遭际、命运多舛、令人窒息的沉沦,同时也昭示着人类存在都要面对的“原初痛苦”和生存困境。“重”之维度集中描摹大地的悲歌与死亡的沉重,而“轻”是集人性思考与构建精神生活完整性的艺术试验,蕴含着对神秘的彼岸世界的无限怀想,在富有地方风情的描述中建构了“神”与“人”的超验维度。“重”与“轻”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互动,建构了迟子健地域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迟子健;东北地域小说;“重”与“轻”;审美风格
目前学界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反思、道德回归以及理想生活模式的建构等方面,重点突出了生态文化意义的审美特色。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迟子建所痛惜的则是一种在生态文化的意义上具有突出价值的原住民文化,在作为现代化象征的汉族主体文化的挤压与逼迫之下,最终无奈消亡这样一种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1]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迟子建显然有某种文化焦虑和寻根意识,文明的推进整合了古老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的消隐则是诗性存在的丧失,“迟子建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构建着人性、生命的意义、以及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寓所和感情的寄托这些诗意栖居之维的核心内容。”[2]关注灵魂的去向以及终极皈依,是迟子建创作的精神底蕴。因此,神性崇拜成了其小说很重要的美学想象,体现出了独特的原始风景。于是,“北方女作家迟子建的笔下诞生了一个遍地精灵的世界。”[3]学者们的研究突出的是文化视野下的萨满教崇拜、现代心灵的诗性构塑以及多元文化的审美解读,一定程度上遗缺了对悲剧精神主导之下两维视域的研究与分析。
新世纪以来迟子健在其东北地域文学中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更为深入的潜在性、广阔的开放性与巨大的包容性。她在描述东北地域风情的同时,思考历史的苦难、人性的本质以及精神的诉求,在文学审美中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延续着东北文学审美中一以贯之的坚韧精神与忧患特征。如果说迟子健的小说中有某种传承性和一贯性的文化因子,那么这和作家内蕴的悲剧意识有直接关系。笔者以为,探讨地域文学固然要论析其地理文化特征,但更要考验作家的人性智慧与吞吐经验的能力,也要检视其心灵的超越能力与对普世性价值的认同程度;从而让我们看到自己未知的一面,探索人类都要面对的生存悖论与终极局限。本论文以新世纪文学视野下迟子健的东北地域写作为个案,探讨其文学审美中存在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特征,集中论析其文学审美精神中“重”与“轻”的两维视域。
一、“重”的美学内涵及呈现
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认为:“种族、时代和环境是影响文学发展的三要素。”[4]抛开“种族”这个大的范畴勿论,时代和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检视一个世纪以来东北文学的审美精神,时代和环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战争以及苦难叙事下生命的坚韧与死亡的挣扎。由于战乱不断,生存不易,在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文学精神自然而然有了“重”的美学内涵,集中表现为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创作风格。新世纪以来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小说创作中,延续了悲剧精神的美学特质,抒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人生挽歌,把东北文化精神系统里的“重”的文化元素阐发的尤为独到与深刻。
笔者以为“重”的美学风格集中表现为死亡悲歌与苦难叙事。在《伪满洲国》①参见: 迟子建. 伪满洲国[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下所论该小说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中,刻画了作为普通生存的悖论以及死亡的悲哀。写人们的生老病死,写各色离奇的死亡。描写死亡,读起来惊心动魄。有的被日本人残杀,有的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死去,如刘麻子死时七窍流血。其女儿刘青也自缢而亡,“她悬空的尸体在黄昏的光线里就像一条体态俊美的青鱼。”一粒蚕豆飞进了善于表演的张家老太的气嗓,死死卡住了她的喉咙,顷刻间就使她气绝身亡。而鄂伦春人乌日楞则倒地后便气绝身亡,死得很干净。……在书中连剃头师傅也感叹:“死亡是件多么平常的事情。”恶劣的生态、悲苦的命运,在对生命不幸与死亡意象的描绘中,突出了一位女作家独特的敏感与细腻。
自萧红开始,“苦难视角”成为东北文学审美中很重要的价值追求。在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中,重在揭示了“底层民众蝼蚁一般的生活状态”,以及“人们乱七八糟的活着以及乱七八糟的死去”的悲惨命运。在迟子健的小说中,描写群众“挨饿受冻不说,人的命就会像蚂蚁一样轻薄,由着人去践踏。”命运凄惨的无助者被大伙视为一堆垃圾、日本人入侵东北后的血腥屠戮、狱中之人虫子般的生活状态……《北极村童话》②参见: 迟子建. 北极村童话[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9. 下所论该小说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中,乡村人同庄稼草芥一样地活着,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以及生存本身的悲哀。《白雪乌鸦》③参见: 迟子建. 白雪乌鸦[J]. 人民文学, 2010, (8): 4-94. 下所论该小说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中,描写鼠疫笼罩下苦难的生命遭际。付家甸一次就死几百人,死亡与苦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死亡就是这样,它以巨大的威力镇压人,让人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地做它的俘虏”,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地沉重下去。
文学审美中这种悲剧意识的渗透,既是东北大地上命运多舛的普通生命的真实写照,也浸透了迟子健对这片土地上满腔的热爱与巨大的悲悯之情。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及人生道路的多艰,要求他们承受更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所频加的各种各样的磨难与辛酸,而且也磨砺出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顽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尘世的沧桑巨变以及生活的不幸赋予了东北文化心灵以深沉而复杂的精神内涵。战火的洗礼、兵燹的肆虐、侵略者杀人的游戏、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承受了各种各样苦难的东北各民族,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出了顽强的精神气质。小说《白雪乌鸦》,既描写了被鼠疫夺取了大量无辜的生命,也展示了瘟疫中的人民在苦难之中超然平和的态度。面对空前的灾难,人们可能一时陷入巨大的惊惶与不安之中,但是过一段时期,那“阴气沉沉的付家甸又有点还阳了。”生命的坚韧来源于长期以来历练所铸就的特殊精神状态。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似乎看透了,既然鼠疫防不胜防,随时可能赴死,索性如常过日子,轻松一点。也就是说,要死就活着死,不能像李黑子那样,死着死。在他们看来,李黑子吓疯后,等于死了。”既然生活之“重负”和恶魔的“美杜莎的头颅”不能战胜,那么天地之间最为朴实的认知就会渗透在人们的精神血液中。自然而然顺应天命去生活,达观之中不乏幽默与智慧是其不变的存在哲学。因此,在作家的书写中,就有了人们面对鼠疫之灾时难得的心灵平和与坚韧的态度。迟子健的小说中,让我们看到了“重”的精神底蕴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这既是属于东北文学审美中独特的美学追求,也是和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相凝结而成的一种文化心理模式。
二、“轻”的审美新态势
文学关注人类心灵,其内质应具有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美学品格反映了作家对文学最高正义的理解。迟子健对这种价值观的坚持和书写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人性内涵与道德深度的探索,体现出了“轻”的美学品格。
“轻”的审美品格在迟子健的笔下首先体现出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人性本位出发来烛照笔下的人物。《伪满洲国》塑造了一位日本军官——“羽田”。作者刻画了这个日本军官深刻的内心感受,他对战争的感悟以及对于和平的渴望。羽田在开赴中国战场之前爱上了一个穿百合花和服的日本女孩,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但是在战争中这个女孩是他最大的精神慰藉。但当后来发现自己梦中的女孩已经成为慰安妇时,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战争的厌恶。在异国他乡的寂寞以及对青春逐渐逝去的强烈感受,使得他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特别丰富细腻的一面。战争不仅摧残着生命和美好的自然,而且还蹂躏着人们心中的诗意与感情。作者通过塑造这位饱满新颖的日本兵形象,细腻丰富地传达出人物心灵深处的感受。羽田在经历了战争的考验,目睹了悲欢离合后,自我的精神得以洗礼与升华,这显然是对人性颇有深度的揭示。
艺术的潜能拓展了人性的空间,艺术形象的生命力也由此而诞生。作家是写人的,是为人而写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把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作为重点予以刻画的领域。歌德在纪念劳伦斯·斯特恩时这样写道:“斯特恩满怀深情地在人身上发现了人的东西……沿着这一轨道继续向前,并且无须思考。”[5]文学的价值来源于对人性的思考。作家在探索人性的同时,能够超越惯性思维而从人性本位出发,从而达到对于人性的全面认识。迟子健憎恶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兵形象,但是同样没有忘记他们身上无法掩盖的人性和人类情感。对待日本兵不再是简单的丑化描写,不仅有了悲喜与共的情感体验,而且折射出了可贵的人道智慧。
“轻”的文学品格意味着一种人性拓展,也意味着对人性心理深层结构的把握与思考,在渊深文学经验的同时,也体现了深切的“文化意识”与“终极关怀”。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①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J].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下文所论该小说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吟唱的是鄂温克人古朴生活陨落的挽歌。作者带着浪漫情调去讴歌渐已失去的童话王国,在寻找那个淡出人们眼帘的牧歌世界。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这些自然而清新的语言背后,触及到的是现代文明演进的“二律背反”难题。
文明与人性的关系、社会现实与道德伦理的矛盾与冲突则是此类小说隐含的母题。作者用诗画的笔触为古朴自然的“地域”文化唱响一曲赞歌。小说对鄂温克人的萨满崇拜予以了虔诚的抒写,崇拜“火神”、敬畏神偶,诸如对驯鹿的热爱、山鹰与主人的默契、以及萨满文化中神对心灵的终极关怀等,让我们领略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感受到的浓烈的文化意识和原乡情怀。笔者以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仅仅要体验到生活的苦难、大地的悲歌,而且还要有一种化“重”为“轻”的审美情趣。“轻”是对苦难、死亡以及无法承受之重的艺术稀释,是作家意识秩序体验到整个人类的匮乏之后的智力游移。当尼都萨满为达玛拉唱了一支送葬的歌,“这首与‘血河’有关的歌:滔滔血河啊,请你架起桥来吧,走到你面前的,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只要让她到达幸福的彼岸,哪怕将来让我融化在血河中,我也不会呜咽。”这是“神歌”,当然也是“人歌”,充满了人性与想象力的凝结,是对神秘世界的畅想,也是对彼岸世界熔铸了谜一般的遐思。
在迟子健的笔下“轻”的价值在于展示出了该地域自然而神秘的心灵渴望。尽管是富有地方风情的描述,却建构起了“神”与“人”的超验维度。“自然、宗教、传统”三者的关系,是该部地域小说富含的深厚意蕴以及“现代性”主题,透露出了作者独特的审美理想,而现代社会则正在不断地放逐或解构这一切。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的内涵在于彰显人类自己的匮乏并返还到传统宗教的世界之中去”[6]。这部小说“轻”的审美品格在于传达这样一层意思,即艺术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兴味关怀”。这种“轻”的“兴味关怀”则超出了家国语境的范围,而上升到哲学乃至于神学的高度。在对“天上世界”的渴望中表达了魂灵的诉求、终极的皈依。面对逝去的生命,他们唱起了古老的歌谣:“魂灵去了远方的人啊,你不要惧怕黑夜,这里有一团火光,为你的行程照亮。魂灵去了远方的人啊,你不要再惦念你的亲人,那里有星星、银河、云朵和月亮,为你的到来而歌唱……”在地域葬礼的描写中,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特而神秘的艺术空间,这是由“重”的心理体验拓展而来的宗教体验,是萨满教信仰背景下心灵的超验追求,其中包含了神秘厚实而神光充溢的人性内涵。
三、结 语
文学创作需要很多悲喜体验,而“重”与“轻”则是其审美体验后的不同艺术表达。勃兰兑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民内心的真实情况。”[7]一国的文学作品如此,对地域文学创作也依然如斯。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歌德的那句名言:文学作品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反过来讲,愈是世界的也愈是民族的,地域的。迟子健系列东北地域小说创作,在悲剧意识主导下,表现了种种深邃而崇高的艺术情感。特别是对人性智慧和道德经验的拓展上,为我们提供了独特而又新颖的文学景观。如果说新世纪文学视野下地域写作的版图中有许多独特的风景,那么迟子健的地域小说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其文学场域不仅深化了东北审美精神系统的精神元素,也开拓了新世纪文学视野的想象空间。
[1] 王春林, 张玲玲. 哀婉悲情的文化挽歌: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J]. 名作欣赏, 2009, (2):104-107.
[2] 梁海. 历史向着自然返回: 迟子建小说的诗性建构[J]. 文艺评论, 2009, (1): 38-41.
[3] 韩春燕. 神性的证明: 解读迟子建小说的“原始风景” [J]. 小说评论, 2009, (5): 104-108.
[4] 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377.
[5] 歌德. 论文学艺术[M]. 范大灿, 安书祉, 黄燎宇,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58.
[6]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1.
[7]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流亡文学[M]. 张道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2.
Two Dimensional Sight of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Aesthetic Style of Chi Zijian’s Novels of Northeast Region in the New Century
PAN Haiju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130022)
There is two dimensional sight of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in Chi Zijian’s creation of novels of Northeast Region. The meaning of “heaviness” not only refers to misery sufferings, erroneous destiny and suffocating depravity, but discloses the “primary pain” and survival difficulties that existed in the survival efforts of human beings. While “heaviness” emphasizes on describing elegy of earth and heaviness of death,“lightness” is an artistic experiment that combines the reflection on humaniti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perfect spiritual life, contains limitless imagination of mystical world of afterlife, and constructs a supernatural dimension of “the God” and “the human” in the abundant description of local customs. The two sight,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supplemented each other and formed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of Chi Zijian’s novels of regions.
Chi Zijian; Novels of Northeast Region; “Heaviness” and “Lightness”; Aesthetic Style
I207.425
A
1674-3555(2012)02-0037-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2.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1-02-28
潘海军(1973- ),男,山西朔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