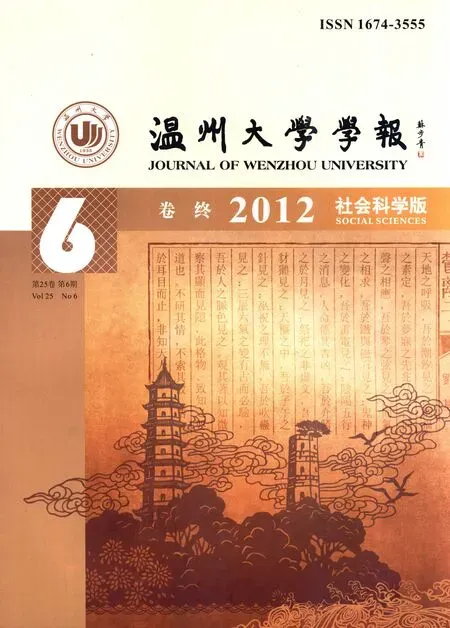认同与协商:街子乡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
2012-03-19安德明
安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认同与协商:街子乡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
安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作为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春节文化符号,社火是甘肃天水地区春节期间举行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艺术表演形式,通常以行政乡(或镇)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流行和表演区域,均属于表现秦腔剧目或演义小说中精彩有趣、矛盾冲突集中之情节的造型戏。这种艺术活动的组织和表演,深刻地表达着人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对于集体的理解,对于村落关系的理解,对于欢乐的理解以及他们的超自然信仰。同时,它也为处于大众传媒及通俗文化多种影响下的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协商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的资源和重要途径。
街子乡;社火;认同;协商
社火是民间节日、庙会期间举行的各种游艺、杂戏活动的总称,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广大农村流行颇广。不过,各地社火,在表演形式、举办时间和功能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甘肃省天水地区的社火活动主要在春节期间的某个特定日期进行,通常以具有这种表演传统的行政乡(或镇)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流行和表演区域。届时,该区域范围中所有的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村或相对独立的社区,都会组织自己的社火队伍,到中心村的庙宇、广场和主要街道来表演。根据方志记载和老人的回忆,这种表演活动至少在清代就已经十分普及[1]。
街子乡是天水地区最著名的社火表演乡镇之一,有着历史久远、影响广泛的社火传统。但同天水其他地区一样,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20多年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的社火表演被当作封建落后的文化形式而加以禁止,处于中断状态。19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逐渐宽松,戏曲、社火表演以及民间信仰活动等传统文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在这种形势下,该乡各村一些对社火怀有浓厚感情并掌握相关知识的中老年,开始在春节期间尝试重新组织村中人员进行表演,最终逐渐促成了全乡表演传统的复兴①在社火复兴的过程中, 充满了村民与国家政策、村民内部的各种力量和不同记忆等之间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今天,街子乡的社火表演,已经发展成了人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过节形式,其主要的社火表演时间农历正月初九,则成了使该乡迥然不同于周围其他乡镇的重要标志。
本文以作者的田野研究为基础,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讨:每一年不同村落的社火队伍是怎样由村民即时组织起来的;组织社火表演对一个村落及其村民有什么样的益处;作为一种表演者姿势固定、既不说唱也不舞蹈的静态造型戏,社火表演是如何在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中达成的;对于个人和社区,它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此外,文章还将对这种表演形式当中体现的宗教信仰、村落之间以及村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加以考察。
一、街子乡及其社火
街子乡位于天水市麦积区中部,包括14个行政村,50个自然村。乡政府所在地街亭村是全乡文化经济中心,也是全乡社火集中表演的地点。其中心地区由东、南、西、北四街构成,为表演社火的主要场所。东街尽头为东山,山上建有规模宏大的庙观群,包括凌霄殿(主要供奉玉皇大帝)、大佛殿(主要供奉佛祖)、城隍庙、娘娘庙(主要供奉送子娘娘)、药王庙(供奉孙思邈)、财神庙等庙宇。各庙除城隍庙外,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1980年代以来,当地人又先后集资重新修建诸座庙宇,并重塑神像。目前大部分庙宇都已得到重建,香火十分旺盛。这一庙观群的存在,使得街亭在周边地区具有宗教中心的地位,也是使它成为社火表演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每年正月初九,全乡各村都要组成一支社火队伍到这里的街道、寺庙和戏场表演。
这种社火表演,可以界定为一种传统的造型戏。它通常选择秦腔剧目或演义小说中精彩有趣、矛盾冲突集中的情节,由村人扮演其中主要角色,组成一定造型后,利用某种工具运载,击钹打鼓,沿街游行。扮演者要依据秦腔中人物的造型和个性,画上脸谱,穿上戏装,手持道具,并摆出固定不动的身体姿势。除此之外,既不歌唱也不舞动。每支社火队伍,称作“一架社火”。
根据表演形式,街子的社火主要可以分为3类①关于街子乡社火种类的具体内容, 限于篇幅, 此处不再赘述,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文献[3].。第一类叫做马社火,其所演剧目中的角色,无论是男是女,均由青年男子扮演。他们在画上脸谱、身着戏装之后都骑在马或骡上,并按照剧情要求顺序结成单行队伍,由专人负责牵着骡马沿街游行。马社火的内容,大多是人们所熟悉的武戏故事,常见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的重要情节。第二类叫做高台,其扮演者为男女儿童,年龄一般在五六岁至八九岁之间。设计者根据选定的故事情节为他们画好脸谱之后,由专人负责,将他们绑扎在特制的支撑装置上,再用戏服遮挡住支撑装置,呈现出各种精巧的艺术造型。过去这种支撑装置需要数名壮年男子抬着游行,现在,随着小型拖拉机和农用汽车在当地的增多,高台都已经改用拖拉机或汽车来运载。在队伍行进过程中,还要有专人在旁边负责照看被高举在半空的小演员。这是当地社火中最具有艺术性且最不易装扮的一种,至今只有中心村等有限的一些村落有能力装扮。第三类是高跷,同马社火类似,它的扮演者也都是青年男子,并以武戏为主。
二、社火的组织与表演
在街子乡,每年正月从初三开始,不少村子都会陆续组织社火在自己村中或关系密切的邻村表演;但全乡最大的社火表演是在正月初九举行。这一天,传说是玉皇大帝的诞辰,全乡各村,凡是有装扮社火传统和条件的,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精心地设计、装扮各种社火到街亭村的街道和神庙表演。每年到了这一天,来自全乡各村乃至邻近其他乡镇的社火队伍和成千上万的观众,都会聚集到街亭村,把这里变成一个节日的海洋。各村秧歌队到达之后,首先要到神庙进香,在庙前广场表演,以示对神的恭敬。当地人相信,唯有这样,社火的表演才能够顺利,表演社火的村落和各人,在新的一年也才会吉祥。由此可以看出,当地社火表演中信仰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而作为一种规律性的定期行动,它也起到了强化信仰力量和人们的信仰观念的作用,并为正月初九这个特殊的日子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天,不仅社火表演者要敬神,大多数的观看者也都会利用机会进香。结果往往使通往神庙的山路上人群络绎不绝,庙里香客盈门。
不过,这种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意义,又往往会被世俗欢乐的取向冲淡。街道上常常是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社火队伍要通过也得花一些功夫。人群的拥塞和社火队伍的不断游行,使村中本来十分普通的地方变得与平常生活大不相同,成了一个表演者和观众共处其间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由于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十分接近,因而能够密切互动。另一方面,表演者的面部化妆、服装、道具等,又使得他们与观众保持了距离,从而保证表演与实际生活相互区别。
每支社火队伍,一般是由一个独立的村子组织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财力等具体条件来决定所装扮社火的类型。要组织一支表演队伍,需要全村的通力合作。当地每个村子长期存在一种非官方的传统组织,为村落内部顺利实现这种合作提供保障。在处理各种非官方的公共事务时,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非正式组织,其中包括了村落的全体成员。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称作会长,由全村各个家庭的男性家长逐年轮流担任,他有责任组织全村的各种传统活动。
要组成一支社火队伍,需要整个村子的参与。不过,村落的成员由于其性别、年龄或对社火知识的掌握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年长的男子会负责相关的事宜,青年男子则会扮演马社火中的角色或照顾其他的表演者和设备,妇女会帮助准备各种用品,孩子们则会准备扮演高台。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装扮社火必须得有至少一位专家。这些专家不仅熟悉能引发当地人兴趣的传统故事,而且掌握着画脸谱、设计和促成社火特别是高台的技巧,因此,他们对自己村子所扮社火的内容和形式,有着绝对的决定权。
这些人也大多是社火传统复兴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就是本社区社火方面的文化专家。正如许多相关研究指出的,文化专家就是那些因其所掌握的特定传统知识而与社区中一般成员迥然不同的人士[2]。他们也许在其他生活领域并不一定有突出的能力,但至少在社火方面的才干,使他们与普通村民有了很大的差别。而对这些文化专家的需要,同人们对社火传统本身的需要是同时产生的。在组织社火队伍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听从文化专家的指导,特别是表演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职业演员。
在社火组织的过程中,文化专家的确比同一个村子中的其他成员掌握着更多的传统知识,他们是传统知识的传承者。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其他参加者同这一知识完全隔绝。如果我们考虑到社火表演为什么又怎样被组织和完成这样的问题,就会明白,其实所有其他参加者是完全明白社火的象征意义、基本规范和功能的。正是由于他们理解这些并与文化专家通力合作,社火表演才能够组织起来,也才能够顺利完成。由此我们可以说,那些一般的参与者,和文化专家一道,实际上都是传统知识的实践者。他们享有同样的传统,并且都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传承和丰富这种传统贡献着力量①有关文化专家和普通参与者在一种文化传统延续过程中协作实践、共同促成文化传承的论述, 可参阅文献[4].。
由于一个村子社火表演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由村中的文化专家决定的,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决定着本村社火表演的艺术质量和表演效果。不过,他们做决定时,必须遵循本村和周围地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这些原则源于宗教信仰、传统民间艺术标准以及村落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比如,一支社火队伍的表演内容应该为神灵或某个家族英雄先祖的耻辱事迹避讳。违背这些原则组织的社火队伍,非但会招致观众的批评,有时甚至还会引起更大的纠纷②笔者1997年春节调查时获悉, 早年北坪村装扮的社火走毛集寨村时, 第一转的内容是“抓潘洪”. 这惹恼了毛集寨村的人, 因为他们多数姓潘. 第二年, 毛集寨村的社火走北坪村时, 第一转秧歌便有意装扮了“抓李良” (北坪村的人多数姓李). 结果惹得双方打了起来, 从此两村关系一直不好.。同时,社火的装扮还要严格遵照传统的脸谱、道具和服装的模式,因为它们是使得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基础。
三、表演中的交流与协商
社火表演所据以取材的传统故事,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对当地人来说,这些有限的故事却构成了他们对于历史和传统价值观——例如忠诚、友爱、英勇等——的基本知识库,包涵着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的丰富象征意义。通过对这些有限的资料年复一年周期性重复地选取和展演,人们能够表达任何有关现实境遇的理解。例如,街子乡1996年的社火表演中出现了几支装扮关于鼠的传统故事的队伍,因为当年是鼠年。其中一架高台表现的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大破白鼠洞的故事。按照设计者的原意,这一表演是要强调当年的生肖,但没想到表演却招来了观众的批评,因为人们认为其表现的当年生肖被杀死的内容不吉祥。
在整个社火表演中,贯穿着观众与表演者以及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簇拥在街道上的观众,除了街子乡各村的成员之外,还有大量从周围其他乡镇——特别是那些没有社火表演传统的地区——慕名而来的人员。对观众而言,社火表演并不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娱乐时刻,还创造了使人们得以交流和学习传统知识的最佳时机。这些传统知识,主要包括戏剧故事和历史传奇,构成了他们对于历史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他们道德隐喻和象征的一个重要源泉。每架社火所表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当地人共同享有的知识库(repertoire)①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现, 个人或群体在某一特定领域都具有专门的知识积累或储备,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用、组合, 为人们实现在这一领域当中的相互交流而服务. 英文称之为Repertoire, 大体等同于“资料库”、“曲库”、“知识库”或“知识储备”. 拥有大体相同的知识库可以说是不同的人之间得以相互理解、沟通的基础. 参阅文献[5].,往往是对传统地方知识中模式化了的某些内容的重复,因此都为本地区人们所熟悉。通过社火队伍中人物的脸谱、服装、道具、姿势以及人物之间所展现的动态关系,人们不必费什么气力就可以辨别出其中所扮演的具体故事。有的观众,特别是孩子和年轻人,也许不一定能够自己理解社火的内容,但人群中随处可以见到的“会看社火的人”以及随时可以听到的评论,却能够让他们及时获得相关的信息。所谓“会看社火的人”,指的是那些热心于传统戏剧和传奇故事、掌握着丰富的戏剧与社火知识、同时也喜欢在人们面前展示自己这方面知识的人,通常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男子,也包括一些青年男子。在社火表演过程中,他们经常起着引导周围观众理解和欣赏每个具体表演的作用。在表演进行的过程中,挤在一起的观众们,无论是否熟识,往往都会就与社火相关的某个话题自然而然地相互攀谈起来。遇到不大清楚某个表演内容的人向那些“会看社火的人”询问时,后者总会十分耐心地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告诉前者及周围的其他人。这样的交谈,一方面为那些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的人提供了展示自己、获得满足的机会,另一方面(尤其重要)使得与欣赏社火有关的技巧得到了交流,使得作为人们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传达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传统故事得到了加强和传播。同时,这种场合也为来自不同村落的人们提供了相互认识的机会。
对于每支社火队伍,观众往往会从这样一些方面加以评论:服装是否新鲜;脸谱是否干净传神;装扮是否巧妙;鼓钹是否响亮,等等。由于相互距离十分靠近,这些议论很容易被表演者和队伍组织者听到,因而会变成每支队伍将来进一步改进自己表演质量的依据,或者与其他表演队伍继续竞争的动力。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所有观众都是传统知识的实践者。
这种来自亲身参与和交流的欢乐,同从其他活动中获得的快乐是大不相同的。社火表演,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作为主角来全身心参与的狂欢机会。这正是街子乡社火活动一个突出特征:它标志了街子地区春节期间的独特性,强调了那些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日子,展示了人们多样的观念。在大众媒体等多种娱乐方式逐渐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主要娱乐方式的时候,街子乡许多人还热心于举办和欣赏社火表演,其原因就在于此。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火队伍是以村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在社火的组织和表演过程中,同一个村子的人们,由于其对社火专门知识的了解各不相同,因此表现也有较大差异。然而,尽管在这些专门知识上可能存在着文化专家与普通参与者之间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差别,但所有人对与这些知识相关的传统却都有着共同的理解和感受,这种理解和感受使得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通力合作,把这种传统付诸实践。就这一点来说,所有人都可以称作传统的实践者。
第二,社火的表演者,与大多数的观众一样,都是普通的村民,生活与文化背景、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为他们共同完成组织表演的多重目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表演过程中,借助道具、脸谱和人物组合等手段,社火以静态的形式,通过充分调动具有相同地方知识背景的观众与表演者所共享的知识库,在表演者与观众的交流中,完成了动态的故事表演。同时,这种互动交流的过程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强化和传播相关传统知识的机会。
今天,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娱乐的手段日趋多样。在街子乡这个距离城市不远也不近的农村地区,电视、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等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新的传媒形式,也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到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位村民,给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使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例如,看电视、上网等各种新的娱乐手段,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社火的延续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协商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的资源和重要途径,正是通过组织和表演社火,人们展示和交流了自己的信仰观念、对于传统的理解、对于集体的理解、对于村落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欢乐的理解。
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对每个村子来说,这种活动实际上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反复强调着村落内部的团结意识,强化着他们对于生活与环境的独特经验,锻炼着他们应对非常事件的能力和技巧。同时,尽管在表演期间也存在着不同村落之间的竞争,但社火表演本身更多要求的是整个区域内的合作。也就是说,通过社火表演,整个街子乡的地理认同与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强化。
同时,对于附近其他一些不具有社火表演传统的乡镇而言,街子乡的社火表演通过吸引这些地区观众的参与,又满足了更广大区域人们对社火相关功能的需求。这一方面使得街子乡在一个更大的地缘格局中保持了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它以这种特殊的区域文化定位与周边地区构成了一个更加统一的有机整体。
[1] 贾缵绪. 天水县志: 卷3 [M]. 兰州: 国民印刷局, 1939: 6.
[2] 理查德·鲍曼. 民俗界定与研究中的“传统”观[C] // 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杨利慧, 安德明,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13.
[3] 杨利慧, 安德明. 街子乡的社火[J]. 民俗曲艺, 1998, (115): 189-210.
[4] 安德明. 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 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77-183.
[5] Hymes D. 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 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 Press, 1981: 6.
Identity and Negotiation: Shehuo Performance dur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Days at Jiezi Township
AN Dem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32)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hehuo is a popular conventional performance held regularly at specific time during the Chinses Lunar New Year Days in Tianshui area, Gansu Province. It is usually organized and conducted in a range of a township, and presented as a traditional posing show that selects the highlight of a classical story of Shaanxi Opera or other traditional legends to represent. It is by organizing and performing Shehuo that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who share a common repertoire,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their perception towards tradition, community, relationship among villages, joy, and supernatural beliefs. Meanwhile, it serves a resource and an entrée for people, who are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to negotiate cultural and local identities.
Jiezi Township; Shehuo; Identity; Negotiation
C912.6
A
1674-3555(2012)06-000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6.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赵肖为)
2011-12-26
安德明(1968- ),男,甘肃天水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间信仰,民间谚语及民俗学的学术史和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