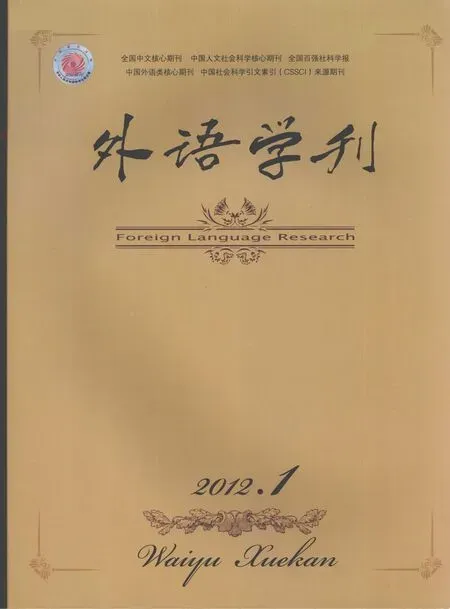边界移动:语言创新的一个动因
2012-03-19刘辰诞
刘辰诞
(河南大学,开封475001;信阳师范学院,信阳464000)
1 引言
语言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语音、词汇、句法等语言形式的各种变化,其动因有很多,例如语用需要、外来语的介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等等。每一种语言的创新方式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本文通过语言结构组织和识解过程中存在的结构-边界现象,观察由于边界移动导致的语言表达式创新,为探索语言发展的动因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2 建立边界是语言结构组织的必要过程
人类要认识世界,就要区分事物,而要区分事物就必须建立个体事物结构的边界。(Frege 1952:56-78)语言做为世界事物,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必然要表现出人类认知的这一基本特征,即通过建立结构-边界把语言单位识解为一个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结构整体。比如我们在实际交际中会用到“他是学生”、“学生不交会务费”这样的表达式,其中的“学生”都是光杆名词,但在理解过程中我们会给“学生”附加上不同的量概念,从而对光杆名词覆盖的语义范围进行一些限制,把它们分别理解成“他是(一个)学生”、“(所有参加会议的)学生不交会务费”等(英语中可使用冠词进行限制,如He is a pupil)。这个过程就是为语义结构确定结构边界的过程。
在对多义词的理解中,也存在着为语义结构建立边界的过程,如英语中的light有多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意义:as light as feather(轻如鸿毛),a light frost(薄雾),light clothing(单薄的衣服),a light attack of illness(不严重的疾病),light music(轻音乐)等,我们在识解中必须加以区分,这个区分过程实际上就是从该词的意义潜势中“圈定”与当前识解有关的一个部分的过程。(Croft&Cruse 2004:109)“圈定”也就是给整个词所表征的意义范围中的某个部分划定意义结构边界。
在句法结构中,要正确理解句子表达的意义,仍然要涉及结构-边界的建立过程,如对同一句子,我们可以作出不同的结构-边界分派,即作出几种不同的解读:
① I heard[the man in the next house].
② I[hear the man in the next house].
③[I heard the man in the next house].
例①中的in the next house被划分为NP的下层成分结构,句子的意义是“我听见了隔壁房子里那个人说话”。例②中的in the next house被划分为VP的补语,意义是“我听到那个人在隔壁房子里说话(但是我接近房子时他从后面跑掉了)”。例③中的in the next house被划分为整个句子的附加语,即状语,意义是“我在隔壁房子里听到了那个人说话(但我离开隔壁房子来到外面时听不到他说话了)”。通过成分划分来进行理解的过程正是方括号标示的结构-边界分派过程,即建立结构-边界的过程。
语言是象征性的,因此结构-边界统一体的属性既是语义的,又是形式的。(Langacker 1987,1991)涉及句子语法结构成分划分时所表现出的结构-边界现象我们称为“显界”,涉及概念的意义限制和意义“圈定”时表现出的结构-边界现象我们称为“隐界”。(刘辰诞 2008a,2008b,2008c)
3 结构-边界移动是语言表达的需要,是语言创新的手段之一
要用有限的语言单位表达无限的交际内容,语言生产者就必须进行多种多样的结构组织。语言结构的每一次重组,都涉及结构成分的变动。就句法表达式而言,不同的识解实际上就是为输入结构建立不同的结构-边界。语言使用中不仅处处可见例①、②和③那样的共时结构-边界移动现象,历时的结构-边界移动现象也俯拾皆是,如语法化过程中的重新分析过程。
结构-边界的移动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导致,都会有两种可能:合理移动和不合理移动。所谓合理移动是指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对结构-边界进行重新分派时,遵守了人类的认知规律。反之为不合理移动。如In these days,few people learn the languages of Homer and Virgil,or indeed see any point in learning them这个句子表达式的结构形式为了某种需要可以变成(1)In these days,few people learn,or indeed see any point in learning,the languages of Homer and Virgil,但不能变成(2)*In these days,few people,or indeed see any point in learning,learn the languages of Homer and Virgil.在(1)中,由于人类认知规律中的对称原则的制约,读者很容易把the languages of Homer and Virgil识解为learn和learning的共享宾语,因此,其结构-边界移动是合理的。而在(2)中,由于or indeed see any point in learning的移动违背了上述认知规律,表达式自然是不合理的。
违背人类认知规律的结构-边界移动会导致结构损毁而不能正常执行功能,在语言使用中就不被接受;遵守人类认知规律的结构-边界移动有可能暂时受到当前语言规约的排斥,但是由于遵守了人类认知规律且服务了某一个使用目的(比如文体新颖或表达经济),这些暂时受到排斥的“非规约语言单位”(unconventional unit)经过频繁使用会被认可,然后会固定下来逐渐成为规约单位(Langacker 1987)而最终被接受并赋予新的表达功能。例如back of the house本来是一个N+NP结构([back]of the house]]),在人类认知规律的相邻原则制约下,语言使用者把这个结构的成分重新分析为[back of][the house]],使其成为一个NP+N结构,结果使back of语法化为一个复合介词。这样的情况在语言的语音、形态和句法层面都不乏实例,其中发生的结构-边界移动导致了新颖表达式的产生,推动着语言的发展。
4 隐界移动与多义性
Croft和Cruse认为,确定意义潜势中某部分的过程可以看作创造意义边界的过程。(Croft&Cruse 2004:109)一个词的全部意义潜势是概念空间的一个区域,当前识解是为其中的一部分确定边界的结果。Langacker的图式范畴化理论认为,范畴化存在于一个“比较事件”:S(tandard)>T(arget)=V(ector value),当 T(目标)满足S(标准)的所有规范要求时,V(向量值)=0,这时S被称为图式。(Langacker 1987,1991)当S和 T不一致时,或者说V的值不等于零时,S可以被看做一个原型,体现为S→T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T很可能偏离S,呈现[S→1→T2→T3→Tn]的形式,如果偏离程度过大,就会出现[S→ T1→T2→T3→Tn]→ [Tn+1→Tn+2...]的形式,这时认知客体就会挣脱原范畴而形成新的范畴。这两种理论所描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形结构-边界的移动过程。
以light一词的多义性识解为例,意义边界理论从“自主意义”出发,在当前识解过程中“圈定”light意义潜势的某一个部分,即确定该部分表征的意义结构-边界。图式范畴化理论则从“标准(S)”出发,根据“目标(T)”偏离“标准”的程度确定意义结构-边界。Light一词从表示重量的“轻”到表示音乐的“轻”,实际上就是T(“轻”音乐)逐渐偏离S(“轻”如鸿毛)的过程。两理论揭示了同一个事实,即语言结构-边界的建立具有认知属性。我们还可以从when的语义变迁看出这个过程:
④ a.He was fond of swimming when yet a child.(时间)
b.We’ll start when the captain comes.(时间、顺序)
c.You know nothing about your history.It’s ridiculous,when it’s all around you.(理由)
d.He usually walks when he might ride.(让步)
e.Turn off the switch when anything goes wrong.(条件)
原始人不理解同义现象,也没有方法使他们确定一个词是不是有多于一个的意义。(Wierzbicka 1994:23-49)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时间和空间概念,因此就频繁地使用这些概念表达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但在实际交际中他们会遇到一些其它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语言表达,这些关系不是精确的时间关系或空间关系,但会以各种方式与时间、空间关系有联系。由于缺乏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诸如让步或条件一类的关系,他们就会用所熟悉的时间关系来替代。比如有人说“你见到老虎时别害怕”,并不意味着说话人肯定听话人一定会见到老虎,而是说“如果你见到老虎”。例4诸表达式中的when就是这样被赋予了时间概念以外的意义。即在when义项中的某一个点上再建立一个意义边界,“圈定”它的这部分意义。when所象征的时间概念结构渐渐偏离图式,以[S→T1→T2→T3→Tn]→[Tn{+1}→ Tn+2...]的形式从它原来的意义结构-边界,即时间概念的结构-边界中移动出来,从而具有了原因、让步或条件意义。尽管这个移动过程经过很长的时期,是隐性的,不能够直接观察到,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到意义结构-边界的移动过程。其它词类的多义化过程,如动词beat的意义演变,也是如此。
⑤ a.I have seen him nearly beat a man to death.(hitting many times to hurt)
b.The rain beat against the window.(hitting but without volition to hurt)
c.We kept working as the hot sun was beating down on us.(expose to the hot sun)
d.He beat the world record in high jump.(break)
e.The Italians beat them to it by about 36 hours.(do it 36 hours before we do)
f.What’s wrong being a shoe salesman?It sure beats making bombs.(be better than)
首先使用动词beat的延伸意义的语言使用者很可能并没有想到要创造什么新颖的表达式,而是因为在某种交际情境下他不得不表达The rain beat against the window所要表达的命题内容,但在现存的表达方式中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式,就使用了他很熟悉的动词beat来组织表达式。而这个表达式的接受人在相邻/相似认知原则的作用下把它作为一个新颖表达式接受了。久而久之,此类表达方式被认可,beat的意义于是就从该范畴中的中心地位向范畴的边缘或边界移动。这种边缘意义在实际使用中会再次被当作“S”.这样的过程多次重复,以至于在It sure beats making bombs中很难在看出beat与其基本意义的联系。
beat的意义不是一下子就从5a描述的意义变化到5f所描述的意义的,它必须从原范畴的中心地位移动到边缘地位,重新范畴化以后(如5c),再次成为中心范畴,再向边缘移动,逐渐产生了5f表达式。如果beat的意义一下子从5a变成5f,其基本意义结构的结构-边界统一体就会遭到破坏,5f会因无法理解而不被接受。语言共时意义创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2008年兴起的网络语“雷人”,意思是出人意料且令人格外震惊,这个意义显然是从“雷”的意义范畴属性“云层放电”、“有骇人的声响”、“会击倒人”等家族成员中通过上面描述的结构-边界移动划定某一部分的意义结构-边界得来的。“雷”虽然和“雨”有联系,但是我们不会把“雷人”理解为“把人淋湿”,因为从“雷”的语义范畴属性家族中可以用“圈定”,即建立意义边界的方式得到“出人意料、使人震惊”的意义,而不能圈定“淋湿”义。复合助动词be going to的语法化历程也涉及这样的过程。
⑥ a.He is going to London next week.(空间域中的移动)
b.He is going to London to work there.(空间域 +时间域)
c.He is going to work in a company(时间域).
d.He is going to like her.(意志域)
e.You’re gonna like her.(功能化)
f.You gonna like her.(完全功能化)
可以看出,be going to的意义变化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从空间域意义经历空间域+时间域再到单纯的时间域才发展到意志域,最后实现功能化或语法化。
上述分析表明,多义化过程是意义结构-边界移动的结果,而支持合理移动的是人类认知特征,如when本意表示时间,时间会有先后,与“顺序”义相邻,那么when在“相邻原则”这一人类认知规律制约下,就有可能从其本意中通过在某一相邻点上建立边界,使when具有表示顺序的意义。beat本意是“(人)击打”,“(人)击打”义与“(雨)撞击”(窗户)义必定在某一点上交叉,即相邻,在“相邻/相似”认知原则制约下,beat就有可能通过在其意义范围的某一点上建立边界的方式使beat具有“(雨)撞击”(窗户)的意义,到了the hot sun was beating down on us中,beat已经没有了实际“击打”的意义,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太阳的照射所导致的“击打”效果,即痛感。be going to本表示空间域的移动,而空间域的移动必然与时间域的先后顺序有联系,其意义相邻/相似,因而蕴含“将来”的意义,这就给语言使用者提供了在其意义范畴内某一点建立一个边界来表示纯时间概念的可能,而意志或意愿也蕴含时间上的“将来”之意,给其语法化为will义提供了可能。
5 O→S移动与作格结构的产生
人类从诞生起就必须认识自己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把自身与世界发生的联系概念化为相应的关系图式,于是就在认知中建立了[HUMAN WORLD]这样的概念关系图式。句法事实上是原始人类在语言表达中安排他们与世界事物间的关系的方式。对于如“人划船”之类的事件,人们会将其概念化为[SOMEBODY SAIL BOAT]这样的S-V-O语义结构图式,Somebody sailed the boat就是精细描述这个认知图式的语言表达式([HUMANDOSOMETHINGTOWORLD])。由于这个事件图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象征这个图式的句法表达式被频繁使用,于是形成了一种共有知识模型存储起来,以至于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表达中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经济表达)使内论元在形式上脱离谓词的直接管辖时,也不会影响语言识解者进行完型建构,即不会引起误解。这样,为了表达经济,在不须要表明施事时,就有可能在句法表层只显示受事,为了与语法规范一致(语法规范不允许主语位置空缺),受事移动到句首位置充当句法主语,这就是O→S移动。汉语和英语都不乏这样的表达式,如船划过来了/The boat sailed to the shore等等。这种表达式出现伊始是新奇的,但因为这个表达式象征的概念结构关系是人们熟知的共有知识,认知的完型特征能够引导表达式识解者填补缺失的概念内容,建立表达式结构的完型,使用中它既经济又能表达与原表达式相同的语义内容,付出的语音努力比原表达式又少,因此人们就渐渐地接受了这种形式,使之成为一种约定的表达式。这种形式被称为作格结构,例如:
⑦ Mary sailed the boat./The boat sailed.
Pat cooked the rice./The rice cooked.
John broke the door./The door broke.
作格结构(包括中动结构)是由完整的S-V-O式经过结构成分的移动而产生的(Radford 2000:446),任何结构成分的移动,必然涉及结构-边界的移动。语法规约本来不允许O向S位置的移动,因为SVO语言要求O处于V后,但是由于这样的移动发生在移动成分O的上一层级结构-边界以内,即“人类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图式以内,语言识解过程不难建立结构完型,且较之完整的S-V-O式结构又可以达到经济表达的目的,因此它在500多年前出现时(Halliday 2000:163),被语言使用者作为创新表达式认可,最终成为规约形式。
作格(中动)结构的O→S移动导致的边界移动,不能违背相邻原则,即O的移动不能越出它上一层级结构的结构-边界,否则就会使识解过程无法进行完型建构,表达式就不被接受,例如:
⑧ I will have someone to cook the rice.→*The rice I will have someone to cook.
I felt sad at the news that the kittens might drown.→*The kittens I felt sad at the news that might drown.
He told me the cloth tore.→*The cloth he told me tore.
在带“*”号的表达式中,斜体标示的S-V-O插入后,原S-V-O中的O不能向句首移动,因为如果移动就要跨越插入的S-V-O,使得语言识解过程难以建立结构完型,表现在语法中,这样的句子就被判定为不合法。
作格(中动)结构的形成是O→S移动的结果,由于这样的移动遵守了人类的认知规律,使得这样的创新形式得以流传,成为一种语法规约固化下来,推动了语言的发展。
6 相邻吸纳:能产生创新方式
Bolinger认为,如果把动词to whet置于[+caus]特征下时,结果必然是 John whetted the knife sharp.(Bolinger 1975)在“深层”结构中,whet和sharp两词几乎可以是一个词:如人们一般不说 John whetted every knife that he could lay his hands on sharp,而说 John whetted sharp every knife he could lay his hands on,也就是说语义相邻使得whet和sharp两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吸纳成为一体。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也是相邻吸纳的结果。先秦汉语中不可能存在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形式,因为那时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如“射共王中目”(射中共王的眼),其中的“射共王”和“中目”分别为两个S-V-O式。随着汉语的发展,表示动作的动词“射”与表示结果的动词“中”由于意义紧密相关而靠拢(石毓智2003),成为“射中共王目”的形式。这样“射”和“中”开始在句法形式上紧邻,久而久之,就融合为一个词,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和英语的whetted sharp一样,汉语动补结构形成的典型特征是相邻的结构-边界由于吸纳而融合的结果。
语法化理论中常常涉及的重新分析现象也是典型的相邻吸纳现象,除前文提到的[[back]of the house](N+PP)[back of[the house]](PP+N)的变迁过程外,Lets的演变过程也经历了结构-边界相邻吸纳的过程:
⑨ Let us go.(Release us.)
Let’s go to the cinema.(Shall we go to...)
Lets give you a hand.(colloquial:I will give you a hand.)
Lets you go first,then if we have any money left I’ll go.(Midwestern American dialect)
let和us的结构-边界由于紧邻并置而吸纳,最终融合为lets,其语义偏离了最初的let us所承载的意义,一个新的表达式由此产生。相邻吸纳导致结构-边界变动,从而产生语言创新的例子不仅在句法层面比比皆是,在形态层面也常有发生:
⑩a cup full of water→a cupful of water
[11]cild-had(OE condition of a child)→ childhood
man-lic(OE likeness of a man)manly
[12]motel(motorist+hotel)
Oxbridge(inclusive term for both universities)例⑩由于成分结构相邻并置引起的语言形式创新在句法层发生,而[11]和[12]则发生在形态层面。这些例子中的边界重新分派现象揭示一个事实:语言结构-边界的重组之所以有可能,是人类认知特征——相邻原则使然。
除动补结构及类似结构(如V(VO)+O(N)构式)外,汉语史上还有许多由结构-边界相邻吸纳而引起的创新表达式,例如“已经”和“甚至”的语法化过程:
[13]a.足下沉痼已 经岁月,岂宜触此寒耶?
b.辞呈已 经领导批准。
c.领导[已经]讨论。
d.我儿子[已经]21岁了。
[14]a.甚嚣,至尘上矣。
b.为君吟所寄,难甚 至忘筌。
c.求功名不遂,甚至穷窘。
d.他们旷课、斗殴、[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
e.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没听说过这部电影。
如[13]和[14],现代汉语中的“已经”和“甚至”在古汉语中是两个词,“已”和“甚”是副词,“经”和“至”是动词,逐渐发展到[已经]和[甚至]的形式,即位置相邻而又可以分析的形式,然后再发展到[13]d和[14]e那样不可分析的形式,成为一个副词或连接词(杨永龙2002),因长期句法紧邻而相互吸纳融合引起结构-边界变动的情况很明显。
7 结束语
语言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在实际语言表达中的稳定状态是相对的,它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要求结构系统必须具有适应不稳定环境,即新环境的能力。就语言表达式结构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就是在结构-边界变动中保持结构完整而不被破坏的过程。如果语言结构适应了结构-边界变动所提供的新环境,一个执行新的表达功能的结构组织形式就会产生,这个新的形式相对于原形式就是一个创新形式。一个新的语言实体能够流传,就是无数个个体创新行为的结果。(Andersen 1989:5-27)语言表达式结构-边界的合理移动导致的语言创新是人类完型建构倾向作用于语言组织的结果,是推动语言发展的动因之一。
刘辰诞.结构-边界统一体的建立:语言表达式建构的认知基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a(3).
刘辰诞.结构-边界统一体:WH移动限制的认知视角[J].外国语,2008b(3).
刘辰诞.结构和边界——句法表达式认知机制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c.
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
杨永龙.“已经”的初见年代及成词过程[J].中国语文,2002(1)。
Andersen,H.Understanding Linguistic Innovations[A].In Breivik,L& H.Jahr(eds).Language Change: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ts Causes[C].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9.
Bolinger,D.Aspects of Language[M].N.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
Croft,W.& D,Cruse.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CUP.2004.
Frege,G.On Sense and Reference[A].In P.Geach& M.Black(eds).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C]:Oxford:Blackwell,1952.
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Hopper,P.& E.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Langacker,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Langacker,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Descriptive Applicati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Langacker,R.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9.
Radford,A.Transformational Grammar:A First Cour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Wierzbicka,A.Semantic Universals and Primitive Thought:The Question of the Psychic Unity of Humankind[J].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