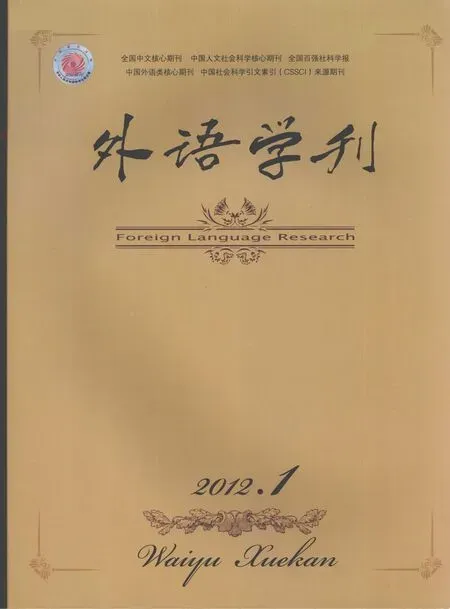论魏晋玄学家对语言形上学的探寻*
2012-03-19袁立莉
袁立莉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1 引言
魏晋时期,作为儒道融合与互补产物的“玄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它以略于具体事物而探求形上学为特点,既主张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又兼顾儒家名教论说,尊崇孔圣。荀粲、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裴頠、欧阳建等玄学家在对语言意义的表述中,对《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的经典解释里,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涉及大量有关宇宙本体名、言表达问题的哲学思辨,从而将中国自先秦开启的语言哲学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语言、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等语言形上学问题的探寻,在此得到系统而充分的讨论。本文以魏晋玄学家的经典著述为依据,梳理其语言形上学的基本思想及其相关语言功能理论。
2 “道”与“言”的沟通与语言形上学的探讨
在魏晋玄学家的思想构型中,“道”是最根本的范畴。“道”的本义是路,经过先秦诸子的论述后,“道”从经验的、有限的“器”层面提升抽象为一种生生不已的本原,具有形上意义的最高哲学范畴。王弼称“道”本“无”是“万物之宗”,所以物、象、音、味这些物象都只是外在的、有限的、派生的,而“无为”、“无名”的形上之“道”才是内在的、无限的本体性存在。裴頠以“道”为万“有”的总体,是万“有”的自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裴頠 2006:289)。郭象虽提出万物独化,突然自生的思想,并得出“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结论。但他也承认,所谓“玄冥之境”,就是“无”或“道”的别称。
形上之“道”是“无名”、“无形”的,那么依靠什么办法才能认知,得“道”呢?魏晋玄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道”的载体——“言”的理解。“道”整合在“圣人之言”中,体现在器化的文字记载里。道在器中,不离不即,治器便可明道。此外,“道体本虚”,把握“道”必须有赖于“言”的充实,而“道”体现于具体事物中的样式,也与“言”的论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荀粲读经典“独好言道”,认为,圣人用以认识世界的语言已超越文字符号所能承载的范围(何劭1982:319);欧阳建强调,一旦“名”、“言”被人们用来认识“物”、“理”,“名”与“物”、“言”与“理”在实际认识活动中就转变为一种二而一的关系,即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欧阳建1982:384)由此,“道”与“言”之间达成共通。
由于“言”与“道”相通,使“言”获得与“道”在哲学探讨上同等重要的地位。语言随即也具有“上可明道”、“下可格物”的工具性或知识性意义。于是,语言应用与分析成为魏晋玄学家必修的功课。他们讲究“重神理而遗形骸”的意趣,“崇本举末”、依据本末、有无之间的内在逻辑,探求语言在遣词造句背后表达的本体蕴意,进而形成几个语言形上学的基本论题。
(1)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关系到超名言之域的形上学的可能性。该论题源自《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 2007:82)。从原文可知,孔子认为“圣人之意”可以通过语言的表达获知,即“言尽意”。但后人却常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提炼出来,大讲“言不尽意”。
荀粲是宣讲“言不尽意”的代表人物。他针对荀俣的观点——圣人言说的“真意”可以通过抽象化的符号“象”与对卦象说明的文字符号“辞”充分理解,指出,圣人之“言”是“系表之言”,圣人之“意”是“象外之意”,作为圣人思想真谛的“性与天道”因语言文字的局限不可得而闻见。(何劭1982:320)随后,何晏、王弼进一步发展荀粲的思想。何晏认为,道是一切万有的终极依据,是一种抽象的本体存在,不可以用任何特定的语言文字指称,所谓“道本无名”。“道”具有“无名”特质,所以其不可局限于任何“有名”的事物,一切幻想通过语言指称探寻世界的作法都是白费力气。(何晏1995:1274)王弼主张“圣人体无”,一切自然现象发生运行的“本”都是不可言说的“无”。“无”的不可言说性决定“言不尽意”。(王弼2007:90)
与上述学者不同,欧阳建是“言尽意”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说,“物”、“理”虽先于“名”、“言”存在,但“名”、“言”对于“物”、“理”却不是不起作用的。正确规定“名”、“言”,分析语言,对于正确认识“物”、“理”十分必要。人们认识客观规律,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概念和它反映的客观对象一致,人们才可以有思想和感情交流。也就是说,由于语言与其指称对象具有同一性,所谓“名”可以“尽物”、“言”可以尽“理”,形上之“道”是在“言尽意”中表现出来的。(欧阳建1982:386)
(2)得意忘言
这一论题来自王弼对于《周易》中言、象、意的解释。王弼用4层意思说明:1)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象的功用在于象征意的内涵,言的功能在于说明象的象征意义。言、象是表意、达意的手段和环节,通过言、象能探求本意;2)源引“筌蹄之喻”,强调言的工具意义。言只指工具和手段,“意”才是最后的目的;3)象是为了表意而产生的,言是为了表象而产生的,但言所表现的内涵毕竟与“本意”是两回事;4)形成结论:只有忘象,才能得意;只有忘言,才能得象。(王弼2011:495)
王弼“得意忘言”的解释提供了理解“真意”的语言学方法。依据言的譬喻、象的象征去探寻圣人的“意”,其前提是承认言、象有承载意义的作用,是“致知之具”、“穷理之阶”;超越言、象的指称而直接领悟体验圣人的意,其前提是相信言、象不过是可以任意置换的工具,是“象之蹄也”、“意之筌也”。(周裕锴2003:128)表达的有形世界的“意”,可以用语言把握。表达的无形世界,即抽象本体“无”的“意”,则不可能完全用语言把握。因为语言符号固然能反映事物的部分特征,但是有很大局限,不能全面反映事物的特性;语言符号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其存在价值仅仅在于引导人们认识事物之“实”;圣人之意超越语言的指称,只可用直接的领悟体验。
(3)辩名析理
所谓“辩名析理”,是通过比较概念的异同,研究概念之间的联系,达到分析事物规律的目的。所以要“辩名”,是因为“名”指“实”,弄清楚指“实”的“名”,自然就会知道“名”的所指,“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王弼1987:609)“辩名”后便可“析理”,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道理,弄清楚“名”的涵义,自然也就有可能对事物内在的理以及相应的理论进行清楚明白的表述分析。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对于声与乐的论述,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辩名析理”个案。他说,“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嵇康区分声与乐两个范畴,指出二者之间没有联系。既然声音与感情器官“心”没有联系,而哀乐的情正是心所发,因此“声无哀乐”的道理便可以自然推导出来。嵇康总结这样的分析方法:“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嵇康1995:1330)可见,“辩名析理”侧重探求事物的规律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着重运用判断和推理。
王弼与郭象也主张“辩名析理”。王弼认为,事物的“实”造就事物的“形”,而事物的“形”又决定事物的“名”,“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王弼1987:605)。在具体文本注释中,应重点关注原文包含的义理,而非主要解决原文中疑难的字音、字义问题。郭象注《庄子》第一条便称:“鲲鹏之实,吾所未能详也”(郭象2004:15),即他不探究鲲鹏这一名称所对应的鱼鸟这一实体,主要关心鲲鹏寓言中蕴含的“逍遥”之理。在解释“天”、“道”等概念时,郭象总是先下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义理,并在整个句子、段落与全文之间的逻辑推理中彰显文字背后的形上之“理”。
实际上,言意之辨、得意忘言、辩名析理等论题的本质均在于“明道”。言意之辩聚焦于道和思想的不可言说,得意忘言探究言背后的“道”的本原,辩名析理则着力探讨“形质”、“形神”关系。言、意、名、理、道之间被系统的体系相联,它涵盖理论与实践的许多层面,表现出“体用不离、道不离器”的特点。显然,其涉及的语言问题已不单纯限定于语言学或逻辑学,更多地具有本体论意义。“意”与“理”在这里表示派生宇宙万物的本原,统摄、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性规律,与老庄哲学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它又超越老庄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式的简单宇宙生成论思想,形成体系完备的宇宙本体论学说,衍生出“无”、“至无”等本体论核心范畴。通过讨论“言意”、“名理”关系,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据成为语言分析关注的焦点,以这个最终根据形成的哲学概括也成为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语言理论基石。
“意”、“理”的形上范畴精深微妙、宏阔广大、深居简出,非言语能表达、包容、统摄与揭示。但作为抽象的客观存在,它们又不能不被言说,否则其只能成为纯粹的“虚无”。于是,不得不通过“言”、“名”加以言说和描述,但又不能执著、拘泥于这种言说和描述,要把言说、描述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权宜手段,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们传达的形上意蕴中。如果以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对其打量,可以发现“言意”、“名理”间的“形上”与“形下”关系问题已触及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理理论的基本命题——语言符号依据什么而具有意义,依据什么确定指称对象,依据什么断定真理等。名称通过指示或者指称外界事物而具有意义;理解名称的指称对象,必须密切注意它的各种不同语境;真理的判定在于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言意之辨、得意忘言、辩名析理等论题直接揭示出,形下“言”、“名”的价值意义本质在于形上的“意”、“理”;言与意、名与理密不可分,言由意生,名由理定,明了“言”、“名”必须通晓“意”、“理”;当“言意”一致、“名理”相符时,语言的“真义”方可得以展现。
3 形上学探寻与语言功能探讨
在魏晋玄学家的视域中,语言之上存在超越语言自身的“形上之意”。荀粲说“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何劭1982:319)。“形上之意”表达的是终极意义,微妙难明,语言对其无法完全表达,所以只能仅存于圣人的心里。王弼称“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王弼 1987:605),语言存在着有限性,无法表达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意”。嵇康也强调,语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1995:1331)显然,荀、王、嵇表达出同一个意思——语言具有局限性或者“语言无用论”。对此,欧阳建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语言指称实在,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名”和“言”都是人的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了解“形上之意”必须通过研究语言实现。语言与形上之“意”同样重要,即“语言有用论”。
为了进一步说明语言的无用问题,荀粲等人将“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有形世界的表达,主要解释定义自然万物与尘世人事方面的内容,这样的“意”可以用语言把握;二是对无形世界的表达,这是一种具有抽象本体意蕴的“意”,属于“超名言之域”,它来自对“道”觉悟,是虚的,但作为“境界”,又真实不妄、确定不疑,是“实”的。它超越语言的指称,语言在此已失去用处。
在“语言有用论”的视域中,“名”和“言”相对于物和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声”与“响”、“形”与“影”之间的关系。“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欧阳建1982:388)物和理的存在决定名与言的出现,其彼此间具有一致性。因为语言指称着实在,它并非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所以“物”和“理”的世界须靠指称实在的语言或自身就是实在的语言来了解。欧阳建指出,“名”与“言”是辨别事物、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客观存在的事物,如不用“名”、“言”加以辨别,人们对它的认识就不清晰;人们心中有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如不用“名”、“言”表达,就无法和别人交流思想。至于语言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欧阳建说,对于不同的对象,需用不同的“名”、“言”固定,以便加以把握。当认识对象变化发展时,“名”、“言”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它们之间仍具有对应关系,“欲辨基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欧阳建1982:388)。基于认识工具和认识对象间存在着对应的统一关系,那么“言”与“意”之间也必定一致,语言的“有用”功能在此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其实,从本质上讲,“语言无用论”与“语言有用论”讲的是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之间的问题。“语言无用论”的重点在于探讨语言与终极意义之间的关系,“意”为体、“言”为用,它突出体现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直觉体悟特征,但同时又过分贬损语言的功能。“无用”对言说者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对于倾听者留下想像的自由空间,语言无法涵盖的“形上之意”,正是语言表意的巨大潜能所在。“语言有用论”将重心定位于语言对认识对象所具有的摹写功能,语言不能揭示对象的原因在于主体认识能力不够或认识方法不恰当。这显然将“意”、“言”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为摹写与被摹写的形式,但它也给语言表达能力的开发留下了新的线索。
20世纪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说,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语言是由命题构成的,因为命题是事实的图式,所以语言与世界间也是一种图式关系。由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的逻辑世界是唯一有意义的世界,除此之外的均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即是澄清无意义的命题所造成的混乱。(维特根斯坦1961:373)按这一推断,哲学中的形上学应被否定。然而,在《1914~1916笔记》中他又写道,“我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是捉摸不定的,而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它的意义”(Wittgenstein 1979:72)。显然,这样的说法让与意义相关的形上学重新获得价值。于是问题出现了:既然形上学是逻辑语言无法言说的,那么它的意义来自何方?
针对此问题,西方学者们曾给出多种解释,但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进而,西方语言哲学中著名的“维特根斯坦难题”出现了。如果将魏晋时期中国出现的语言“无用”与“有用”的争论与其联系在一起,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许多相似性。维特根斯坦难题的关键是神秘事物的不可言说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魏晋玄学家所讨论的焦点是语言能否言说形上事物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看到了语言的遮蔽性,在发现语言不能解释认识对象是“什么”后,他说一个人“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维特根斯坦1961:97)。魏晋玄学家同样认识到语言言说对“形上之意”的表达存在某些局限,不过,其建构出两个迥异的结论:“语言无用论”者认定“意不可说”、“言不及道”(嵇康 1995:1331);“语言有用论”者明确指出语言是为了反映客观存在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同“形上之意”相比,语言是第二位的,但没有语言,“形上之意”也无从表现,人们也无法认识它。因此,言即是意,意即是言。(欧阳建1982:389)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玄学家的“语言无用论”与“语言有用论”间存在彼此调和的可能。王弼曾设计出“立象以尽意”的思路:一方面,他认为语言不能完全地、充分地传达“意”,另一方面,又认为“意”可以通过“象”(意象)表现出来。(王弼2011:492)如前文所述,王弼认为,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形上之意”模糊不可见,但“象”却是虚实相生的,通过“言-象-意”体系的传递,语言作为对万物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其对“意”的传达功能被激活——要充分利用并扩展语言的表现力,通过“象”对“意”进行尽可能地言说。(王弼2011:495)实际上,这样的言说还有另一积极特征,那就是在认识活动中自己展示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对象、属于自己的存在。简言之,言说并不是复制已有的对象,而是对已有对象潜能(意)的发掘、发展的一种现实化过程,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对象。正如王弼注《易》,他并不是在复制《易》的思想,而是借《易》来创造自己的思想。
可见,“言-象-意”体系为解决“维特根斯坦难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路。它既是对出言与无言的辩证,又是对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矛盾的统一。当然,它也存在不足:在肯定言不尽意事实的同时,坚持“立象以尽意”,本身就是理论上的矛盾。
4 结束语
魏晋玄学家对于语言形上学的探寻,使其语言观具有本体论基础。在其影响下,汉代神学思想在语言学中的印迹逐渐退去,语言与对象世界、主体经验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明确。其对语言形上学的建构和语言认识功能误区等问题的解析,为后世学者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资源。
裴 頠.崇有论[A].张连良.中国古代哲学要籍说解[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何 劭.荀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欧阳建.言尽意论[A].(唐)欧阳询.艺文类聚[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王 弼.周易正义[A].十三经注疏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王 弼.周易略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王 弼.老子指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何 晏.无名论[A].全三国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稽 康.声无哀乐论[A].全三国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郭 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J].外语学刊,2008(6).
Wittgenstein.Notebooks 1914~1916[M].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