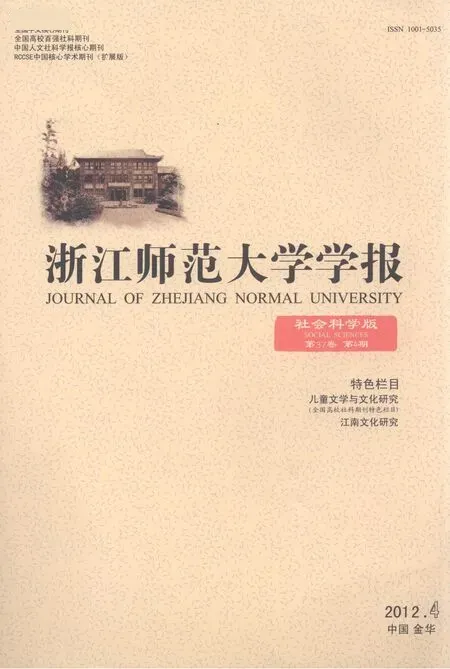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的古今演变
2012-01-29付建舟
付建舟
(浙江师范大学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 金华 321004)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见长,叙事文学则相当欠缺;与此相应,抒情文学理论也比较发达,叙事文学理论则相对欠缺,从而造成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的局面。其实,我国历史著作十分丰富,其中的史传著作也十分发达,史传很讲究叙事法则;而我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传的艺术成就很高,史传又往往被视为叙事文学。另外,古代散文很发达,散文理论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叙事法则,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由此可见,中国叙事文学理论也是十分丰富的,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从上古时代起,我国典籍里就出现了许多叙事,形式多种多样。法国学者罗朗·巴尔特说:“叙事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图象、手势以及所有这一井然有序的混合体来表现;它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图画、玻璃窗彩绘、电影、连环漫画、社会新闻、交谈之中。”[1]许多叙事形式就存在于我国汗牛充栋的叙事典籍中。在文字发明以前,有“结绳记事”,“刻木为契”;文字发明后,“始画八卦,造书契”,后有甲骨问事、青铜铭事和其后的《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地书籍以及诸子书籍,这些都是中国叙事的资源。中国历代的叙事理论资源散存于诸子著作、文学理论著作、历史论著以及大量的序跋、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之中。总体来看,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的古今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发生期、发展期、繁荣期。
一、秦汉时期叙事观念的萌芽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了一些叙事原则。《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书·毕命》曰:“辞尚体要。”《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里的“物”与“序”、“要”与“体”、“志”与“文”都分别是“义”与“法”之意,强调叙事内容与叙事形式的统一。由此可见,早在先秦,“义法”就成为了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受到普遍关注。叙事首先要充实,不能空疏;要真实,不能虚伪。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充实而真实的内容需要富有文采的文辞来表达,缺乏文采就会影响其顺利传播。于是孔子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管是纪实性著作还是虚构性著作都是如此,不过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走得更远,极其文饰之能事。美国学者哈米顿指出:“传记历史之完善者,必用作稗史之方法,其理不难推知。模范史家,其视事实为真理之表示,而彼所企图以艺术手腕表现者,即是真理耳。故史家亦如小说家。”[2]认为史学家和小说家都讲究叙事方法,可谓一言中的。
先秦“言有物”和“言有序”的叙事原则与西方现代叙事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叙事都由两部分组成,即“故事”(histoire)和话语(discourse)。故事是“内容或一连串事件(行为、事件)加上我们称之为存在的东西(人物、环境)”;话语是“表达,是内容得以传达的手段”。[3]简单地说,故事就是描述什么,话语则是如何去描述。“描述什么”要解决的是叙事内容问题,“如何描述”要解决的是叙事技巧问题。写作技巧历来就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与“言有物”、“言有序”叙事原则相应的,是秦汉时期各种政教活动的具体实践。礼官必须按照一定次序来记录各种重要的政教活动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许多典籍中经常出现“序事”、“叙事”等词语的重要原因。这些词语虽然与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有很大差别,但仍然表达了记辨秩序的叙事内涵,尤其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或空间顺序对事件的记录。《礼记》表现出了强烈的叙事意识,尤其是叙事结构意识。该典籍设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天官及地官,前四者以时间为序,后二者以空间为序。他们不仅注重时间,也注重空间,这充分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从感性经验出发,把宇宙和人事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4]礼官们还产生了区别“记事”与“叙事”的朦胧意识。在他们看来,“记事”是对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记录;“叙事”除了“记事”的含义之外,还包括技巧的使用。
先秦典籍中屡屡提到“序事”,频繁地按照一定次序记录各种政教活动。《周礼·春官宗伯下》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予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这句话表明,乐师的职掌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根据礼乐仪式的要求,安排乐器陈设的位置以及奏乐的前后次序。唐代贾公彦疏曰:“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谬。”《周礼·春官宗伯下》又云:“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表明了春官宗伯属下掌管天文星历的冯相氏的职掌范围。“辨其叙事”是次序四则应行的事。《周礼·春官宗伯下》还云:“内史,掌王之八材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讷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吏掌书王命,遂贰之。”这句话表明了内史的职责。“掌叙事之法”即按职务的尊卑次序,接纳臣下谋议,转告国君处治。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叙事”是“记事”的含义,就是把发生的一些事件按照一定的次序记录在案,虽然与现代“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含义相差甚远,但毕竟包含了按照一定次序记录的含义,而这一含义是任何“叙事”都必须具备的。另外,先秦叙事文学初具形态,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以记事为主与以写人为主。前者如《左传》,所记为国家大事;后者如《晏子春秋》,所记为杰出人物的主要事迹。这种叙事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潜在的影响。[5]
到了汉代,叙事文不仅要求按照一定次序记录或叙述,还必须讲究技巧。“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6]把记言与记事分开很重要,对记事的突出使叙事文的叙事技巧大大提高了。“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班彪传》)叙事文讲究次序是很自然的事情,礼官只凭借事件的自然时序就可以了,礼仪制度所规定的各种等级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次序,即封建伦理秩序。但仅仅根据自然时序和礼仪等级来记事还不够,还必须有所选择,有所安排,使事件的“记录”更加有序,更加简洁明了。这是汉代叙事文与先秦典籍相比的一个重大进步。汉代的叙事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概念已经很接近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叙事理论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成果丰硕,其中关于叙事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任昉的《文章缘起》、萧统的《文选序》、刘勰的《文心雕龙》、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等。
这一时期对叙事理论的贡献是从文体分类开始的,通过辨析文体,叙事文体自然而然浮现出来。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7]13这四科八类中,奏、赋、书、铭、诔四类,叙事成分比较重。陆机《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7]147陆机的十种文体中,赋、碑、诔、铭、颂、奏六类的叙事比重较大。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7]179挚虞对诗、颂、铭、诔四种文体进行了阐释,铭、诔的叙事特征十分突出。李充《翰林论》云:“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駮不以华藻为先。……研敷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盟檄发于师旅。”[7]200-201任昉《文章缘起》云:“六经素有歌、诗、诔、谏、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诒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7]311这些文体辨析虽然简约,却为其后的理论著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综其大成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颜子推《颜氏家训·文章》继承了这一思想:“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7]434这些文体分类不仅为明代文体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也为叙事文学理论开辟了道路。
同时,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有很强的叙事意识。刘勰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叙事规律,其《史传》、《定势》、《熔裁》、《章句》、《夸饰》、《附会》、《总术》等篇对叙事文体均有所论述。他认为应该先统观全局:“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作家必须先识“大体”,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事先进行总体安排,从而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他把文章比作一个有机体:“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颜之推也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7]437叙事整体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整体不单是形式上的整体结构,还包括内容上的整体血肉,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此外,这一时期的叙事理论立足于传统的文章学,注重章法、句法、字法,虽距现代叙事理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毕竟具有独自的特色。历代文人十分重视章句之法,它尽管不是专门讨论叙事作品的技法,但许多内容却与叙事作品密切相关。章句之法主要讨论文章的句法章法(也包括字法)。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专门讨论“章句”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章与句体位不同,要求不同。章有章法,句有句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篇幅有长有短,“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清代叶燮的《原诗》分析得较为透彻:“律诗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结,古诗要照应,要起伏,析之为句法,总之为章法。”[8]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三》曰:“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八股文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文字表达方式逐渐极端定型化。“起、承、转、合”是文章结构上的特定套数,是行文的通则,对叙事文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唐宋时期叙事理论的发展
唐宋时期叙事文类术语已经被明确提出。唐代刘知几的历史论著《史通》虽然论述历史,由于历史著作属于叙事文,所以这部著作实际上许多内容是在论述叙事问题。除了内篇中的《致书》、《曲笔》以及其它章节和外篇中的《杂说上》以外,还有《叙事》篇。宋代秦观、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陈骙等人都更加重视叙事。
对叙事文类的区分是唐宋时期叙事理论的重要贡献。刘知几没有专门区分叙事文,秦观则从理论上作了区分。他的《韩愈论》把文体分为五类:“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论理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生死之变。……列御寇、庄周所作是也”;论事之文“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如苏秦、张仪所作是也”;叙事之文“考异同、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实录。……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托词之文“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成体之文“钩列、张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韩愈作所是也”。[9]13-14这五种文体中,成体之文是对前四者的综合,不能称为独立的文体;托词之文是指屈原、宋玉的赋体,是叙事文体的一种变体;论理之文与论事之文都是辩论之体。因此,这五种文体实际上是辩理之体和叙事之体两类。秦观把叙事置于仅次于辩理的地位,其《通事说》云:“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古人皆备而有之。后世知说理者,或失于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于悖理,皆过也。盖能说理者始可以通经,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10]208突出了叙事的地位。张耒把“古之文章”分为记事和辩理两类,“记事而可以垂世,辩理而足以开物,皆同达者也”。[9]14还有人把叙事体与抒情体作了区分。金人元好问说:“诗与文,特语言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明人张佳胤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成篇。”[9]14宋人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专列“叙事”文类,卷首有《文章正宗纲目》云:“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鼉眡视之,二书所录,果皆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今凡二十余卷云。”[10]378《纲目》还专门对“叙事”门类作了解释:“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10]379-380真德秀总结的三种叙事文体,实际上是历史著作的三种叙事体例,即编年体、纪传体和记事本末体。
对叙事特点的辨析是此期叙事理论的另一贡献。《史通》探讨历史著作的编写方法,刘知几提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的观点,把叙事提到一个新高度。叙事之体主要有编年体与纪传体两种,《左传》为编年之始,《史记》为纪传之祖,二体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11]72关于历史著作的体例,刘知几注重以《史记》为首创、以《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1]39这是对纪、传、表、志四种文体的简要概括。纪、传除了历史著作使用外,叙事文学作品也常常借鉴其优长,而表、志则舍弃不用。“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体的特点是纪天子的行事和纪年代月日,将时间和事件融为一体。不过,有的史家也并不恪守这个原则。例如陆机《晋书》,列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祖为本纪,直接叙述他们的事迹,但不编年;《后汉书》与《北齐书》,在帝王篇中夹杂记载臣下的事情,或者兼带叙述其他事情,事无巨细,一起写出。历史著作在表现其对象(尤其表现人物)时,一般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或直接记述才行,或单单描写事迹,或描述人物的语言,或通过赞评而显现:“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作为叙事体的传记,它还存在几种不同的形式,通常情况下是一人一传,但也存在合传、寄传和附出等形式。“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余、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11]75有些不重要的人物,其传记往往附着在重要人物的传记里,“寻附出之为意义,攀列传以垂名”。[11]77合传、寄传和附出等形式远比独传常见。
简要是对历史叙事的一个基本要求。“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务却浮词,注重隐晦,是叙事文要言不烦的基本要求。“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史》、《汉》省要,《国》、《晋》烦碎。“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刘知几对妄饰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对历史著作来说,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对叙事文学则不尽然。陈骙也认为:“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他引用《春秋》记载“陨石于宋五”为例,来论述其简当。《公羊传》解释说:“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12]这的确可谓简了,然而简则简矣,却缺乏应有的信息含量,使叙事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四、元明清时期叙事理论的深化
宋代以后,对叙事文法的探讨逐渐深入,重要的著作有元人陈绎曾的《文说》和《文筌》,明人归有光的《文章指南》、高琦的《文章一贯》、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清人李绂的《秋山论文》、李渔的《闲情偶寄》、刘大櫆的《论文偶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熙载的《艺概·文概》等。
元明清时期,文体和叙事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文体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这两部著作对历代文体进行了认真辨析,认为其中不少文体属于或主要倾向于叙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简要序说了诸多不同文体的特征,其中,记、志、纪事、行状、述、墓志铭等文体以纪事为主。他解说道:“记者,纪事之文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来逐渐杂入议论。“志者,记也,字亦作誌。”大抵为记事之作。“纪事者,记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记时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遗焉;于是文人学士,遇有见闻,随手纪录,或以备史官之采择,或以稗史籍之遗亡,名虽不同,其为纪事一也,故以纪事之。”行状者,体貌本原,取其事实,状之大者也。一般对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言之甚详。“其逸事状,则但录其逸者,其所已载不必详焉,乃状之变体也。”述,是撰述之意,主要撰述人的言行以备考。其文与状同,是状之别名。墓志铭是把古代有德善功烈之人的事迹,在他死后用铸器以铭之,传于后世的一种文体。“其为文也则有正、变二体,正体唯叙事实,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13]这些文体,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简略,详略得当,是《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经史著作叙事技法的具体应用。
吴纳和徐师曾概括的叙事文体基本上属于应用性文体,不是艺术性文体。李渔则重视艺术性叙事文体,尤其是戏曲理论的研究。其著《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与“叙事”相关的主要是《结构第一》和《词采第二》。他认为叙事结构是首要问题,极其重要,它“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为此,他提出要“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至于词采,则要“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此外,这一时期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概括出丰富多采的叙事形式,可谓蔚为大观。元代陈绎曾的《文筌》将叙事形式法则归纳为十一项,即正叙、总叙、铺叙、略叙、直叙、婉叙、平叙、引叙、间叙、别叙、意叙等。清代的李绂在《秋山论文》中也概括出了一些叙事法则。例如:
顺叙最易拖沓,必言简而意尽乃佳。苏子瞻《方山子传》,则倒叙之法也。
分叙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类叙者,本分也,而巧相联属。
暗叙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左传》箕之役叙狼瞫取戈斩囚事,追叙之法也。蹇叔哭送师曰“晋人御师必于肴”云云,暗叙之法也。
叙中所阙,重缀于后,为补叙。不用正面,旁迳出之,为借叙。《史记》巨鹿之战,叙事已毕,忽添出诸侯从壁上观一段,此补叙而兼借叙也。
特叙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志,特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夹叙夹议者,如《史记》伯夷、屈原等传是也。[14]
李绂对自己提出的一些叙事法则作了简要的解释,并举出了相应的实例。这些叙事法则明确道出了中国叙事文的一些特点。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论述叙事原则说:“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在主旨上,他提倡叙事要宗经;在行文上,提倡叙事要行气;在具体叙事时,要大书特书。“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极尽书写之能事。这与唐宋时期的求简相反,实际上是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区别所在。历史叙事要求事实清楚明白,文学叙事除此之外还要求寓理、寓情、寓气、寓识。“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他还把叙事分为十八种之多:“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并强调:“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15]评点家们的叙事意识则更加强烈。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他们根据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概括了许多叙事法则。金圣叹认为《水浒》简直可以当作文法教科书来读。仅《水浒传》,他就概括出了十五种法则:(一)倒插法,(二)夹叙法,(三)草蛇灰线法,(四)大落墨法,(五)绵针泥刺法,(六)背面铺粉法,(七)弄引法,(八)獭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极不省法,(十二)极省法,(十三)欲合故纵法,(十四)横云断山法,(十五)鸾胶续弦法。此外,评点家们还概括出春秋笔法、影灯漏月法、因缘和合法、禹王金锁法、趁窝和泥法、移云接月法、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忙中闲笔法、舒气杀势法、正犯法、略犯法、犯而不犯法、犯中求避法等等一系列的叙事法则。这些叙事法则涉及到了叙事结构、叙事时间以及叙事视角等各个方面。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古今演变过程,该过程表明:中国叙事观念产生于秦汉时期,叙事理论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宋时期,繁荣于元明清时期。每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理论具有不同的特点:秦汉人产生朦胧的叙事观念;魏晋南北朝人具有一定的叙事理论意识;唐宋人则更加自觉地探讨叙事理论;元明清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叙事理论。这一历程表明,中国叙事文学理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前后具有很强的连贯性或者说一致性;它以传统的传记、叙事散文、小说、戏剧等为对象,由批评上升到理论,具有感性批评的鲜明特点。
[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译者前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
[2]哈米顿.小说法程[M].林华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9.
[3]塞默尔·查特曼.故事和话语(导言)[M]//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90.
[4]王利器.文子疏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346.
[5]于淑娟.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4):8-12.
[6]班固.汉书·艺文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13.
[7]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1.
[9]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前言.
[10]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姚松,朱恒夫.史通全译(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2]陈骙,李涂.文则·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6.
[13]吴纳,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45-149.
[1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
[15]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