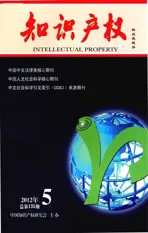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与公共利益维护
2012-01-28王宏军
王宏军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与公共利益维护
王宏军
为切实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法定主义提出应警惕来自司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但针对是否也应防范来自立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既有理论分歧较大。通过对该问题做较细致的分析,以及通过返回法定主义的理论起点,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法定主义理论构想,这是对原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公共利益 新法定主义
依据刘星先生的看法,从法学的实践性出发,法学理论本身并不存在“科学”的问题,根本上看,主要是一个“对谁有利”的探究问题。①刘星著:《法学知识如何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作为一种近年来影响很大的法学理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利益立场无疑十分明确,对此,代表学者李扬总结为,该理论对所涉公共利益表现出的不是一般的关怀,而是充满了某种程度的热情关怀。②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缺陷及其克服》,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2期。可见,尽管法定主义的理论视野十分开阔,广泛涉及了劳动自然权说与功利主义学说、利益平衡机制、部分法院的相关案例等诸多重要问题,但如果一以贯之,或许可以说,法定主义就是要以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作为最重要的理论目标。对此目标,虽然代表学者在其论述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但该目标的丰富理论内涵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下对此详述。
一、法定主义的理论目标
一般认为,郑胜利先生首先提出了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概括而言,在理论上,由于知识的公共性,决定了知识创新者与他人分享其成果的合理性。又由于这两类利益群体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创新知识的利益诉求也必然不同,程序上应该允许他们充分辩论以寻求平衡点,这远非相关行政和司法程序所能担负。因此,知识产权只能由立法层面创设。③参见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在此理论中,有以下三个要点值得关注:一是围绕着知识创新,不但有知识创新者的利益,还存在着相关公共利益,即竞争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二是知识产权法应对这两类利益一并保护,绝不能忽略对所涉公共利益的保护,关键是双方要进行充分的“公共选择”。三是由于法院或行政执法机构不适合作为这样的公共选择平台,因此,知识产权只能由立法层面来创设。可见,不论是法定主义提出的理由,还是其希望达成的目标,都与维护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其之所以反对法院在法外创设新型知识产权,根本上就是为了维护所涉公共利益。
此后,有学者相继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代表者有学者朱理,将法定主义进一步明确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学者李扬对其理论基础予以了极大丰富;学者崔国斌对其案例基础予以了极大丰富。通过这些努力,该理论的内涵更为丰盈,学术影响也更为广泛。虽然上述学者的理论切入点各有千秋,但其理论中无不贯彻了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思想。例如,朱理博士认为,立法者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慎重选择创设权利,司法者应将立法空白视为划界的藩篱而非开放的门户。④参见朱理:《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一种新的认知模式》,载李扬等著:《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学者李扬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使得相关公共利益正不断遭受威胁,因此必须坚持法定主义。⑤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学者崔国斌认为,由于法官造法泛滥,不但打破了法定的利益平衡,而且还轻率敞开了国际保护的后门,致使民族利益受损。⑥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经由这些学者的理论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维护所涉公共利益的理论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批判更多地指向了我国法官的造法泛滥,使该理论的实证及本土色彩更为明显。二是不但强化了所涉公共利益可能会受到不当司法创权的影响,而且该影响也可能来自于立法创权。三是由于部分法院造法泛滥,不但使得法定利益平衡遭到破坏,而且因外方能轻易获得平等保护,更加剧了这种失衡。
二、法定主义应否反对立法创设
虽然为维护所涉公共利益,代表法定主义的学者无不赞成应对来自司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保持警惕,但深入去看,这些学者的观点又存在着明显差异,该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个问题上,即:是否也应同时防范来自立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在郑先生的观点中,只是提到了应该反对来自司法及行政途径的创设行为,之后,朱理博士及学者李扬明确提出了要同时警惕相关的司法创设以及立法创设,而在学者崔国斌看来,或许这并非是一个问题,因为破坏法定利益平衡的是部分法院,而立法原本是平衡的。即便朱理博士及学者李扬明确了不应忽略防范立法创设,但也并未进一步指出,在这两类创设之中哪个应该成为防范的重点。这是法定主义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表述中,存在着较大理论模糊的地方。在此问题上,本文认为法定主义不但应该防范相关立法创设,而且这种防范或许还应该成为重点,否则,其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此外,虽然提出了要防范立法创设,但并未在我国语境下展开,初步来看,可能是出于理论实现策略方面的考虑。原因如下。
第一,法定主义者通过反对司法创设所要维护的特定公共利益,“事实”上、“当然”可能会因为相应的立法创设遭受影响。比如,学者崔国斌曾以禁止反向假冒的权利和网络传输权的确认为例,批判法官造法行为。目前,这两项权利都得到了立法认可。对于这种先经司法、再经立法认可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法定主义或许会面临某种理论上的“两难”。因为如果说批判法官造法,是怀疑所涉公共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害,那么在立法上已经认可了这些权利后,是否还应继续保持怀疑?而如果只是反对法官造法而不怀疑立法者创权,那么就有可能使得所涉公共利益不但可能因法官造法受到损害,还可能因为立法确认受到进一步损害。当然,除非有关所涉公共利益的社会利益冲突本身(不仅仅是因为从司法到立法创权的转变)碰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才会使这个两难不再存在,但这种情形恐怕不会总能遇到。这也许可以说明,不但法定主义不能回避所涉公共利益当然可能会因为立法造成影响,而且,实际上,所涉公共利益只有一个,虽然有可能因未经公共选择的法官造法受到损害,但也有可能会因立法创设而受到影响,尽管后者经过了公共选择,但立法者毕竟不是上帝。
第二,如果相关立法创设完成,那么对于法定主义本来希望通过反对司法创设所要维护的特定公共利益维护起来将更加困难。法院创设新型知识产权,有可能使个案中的相关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进而,如果这些判决具有了先例地位,那么将会做出更多的类似判决,有可能使所涉公共利益在更大的范围内招致损害。然而,即便是出现了先例的情形,但相对于立法认可而言,也仍属个别的、且有可能被推翻的,而立法认可则是一般性的,基本上排除了在类似案件中不会被视为权利的可能,当然,立法也可以被修订,而且还可能较为频繁,但无论如何,这些新权利被否定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此外,从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上看,在司法创设新权利时,权利能否存在被视为是可以讨论的,而在立法认可后,则被视为必要的讨论已经结束,新权利获得了正当性外观,尽管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内在问题不一定得到了解决。当然,如果前述的碰巧机制再次发生,这也将不成为问题。这也许可以说明,在法定主义的理论中,不但无法回避所涉公共利益当然可能会因为立法创设造成损害,而且这种可能的损害还要远大于司法创设的影响,既然对司法创设都要批判,那么对于立法创设更不应保持沉默。
第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立法本身的变动,那么不同时防范立法创设,有可能会使法定主义流于形式。由于立法变动,使得立法有旧法和新法之别,那么法定主义依据立法来反对司法创设,应该在哪个立法阶段上实现?例如,2001年专利法的民事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50万元,如果法院在某个审判中,将赔偿确定为60万元,这样就多判了10万元,法定主义应该提出反对。在逻辑意义上,假定2008年后,又出现了同一个案,由于此时的法定赔偿限额已经提高到了100万元,那么,如果法院在新法基础上,判成了110万元,固然为法定主义所反对,但即使法院不越位,仅判成了100万元,法定主义是否应该反对?有两种可能,一是反对,因为已大大超越了其原来反对过的60万元,二是不反对,因为其仅是反对法院在立法基础上的超越。尽管从形式上看,后者看似更符合法定主义,但是当立法者不断进行积极创设权利,而其仅追求在新法基础上的新的反对,那么也就只能十分被动地调整维护所涉公共利益的具体目标,或许,不能不说只剩下了“形式”。实际上,一个简单的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的新法创设,远比法院从50万元提高到60万元的司法创设对所涉公共利益的影响更为剧烈,极有可能,在法定主义反对司法创设的地方,通过立法创设早已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第四,虽然有学者提出了要防范立法创设,但或许主要还停留在原则宣示的层面,也并未在中国语境下展开该问题。一是总体上看,探讨该问题的文章篇幅,只占法定主义理论表述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例如学者李扬认为,法定主义之所以要对立法者警示、司法者防范,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力度不断强化、公共利益不断遭受威胁,但其所列举的诸项,究竟是出自立法者还是出自司法者的原因多一些,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证。二是在对立法探讨的具体内容上,主要包括应注意哪些平衡技巧,如何处理立法僵化等,基本上是在立法技术的层面展开,并未对我国的30年立法创设、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哪些影响进行事实判断,也并未进而对立法应积极、还是消极创设进行价值判断。换句话说,这些技术性分析,如果用于他国,大致也是可以适用的,因为它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与这些学者在反对司法创设时从我国的典型案例出发,积极进行事实与价值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五,法定主义未能深入解读立法创设影响公共利益的问题,初步来看,可能是因为受制于理论的直接目标以及理论实现策略上的考虑。一是尽管法定主义的理论十分复杂,但其“直接”目标就是要通过阻止法院在法外创设新型知识产权,以实现防范经由司法途径的扩张。因此,在立法问题上并未给予更多关注。二是为实现该目标,现实来看,其必须要能找到足够有力的手段,仅依靠学术批评是不够的。由于法院依法裁决可以说是毋庸置疑,那么依靠立法来反对不当司法创设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虽然追求理论的现实影响力无可厚非,但是理论实现策略的可行性并不一定会与对理论的另一更高要求,即逻辑彻底性,⑦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也能保持和谐。因为,既然是要通过,甚至是只能通过立法者来约束法定主义所认定、所反对的司法不当创设,那么在逻辑上就不方便,甚至也很难去怀疑立法者。如果真要去怀疑,甚至去批判,其所追求的理论实现策略上的可行性就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反向行为在整体上遭到破坏,至少也会出现局部上的减损。通俗来说,这或许有一些投鼠忌器的无奈。虽然这仅是一种初步推测,但是,过于追求理论在策略上的可行,不但如前文所分析的有可能使维护所涉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较难实现,而且还可能会减损理论原本所具有的理论深刻。⑧法定主义的代表学者主要有郑胜利、朱理、李扬、崔国斌等,相关代表作品在文章第一部分基本上都已提及,在此部分,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围绕这些代表作品展开,为节省篇幅,并未一一详加注释,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总体说明。
三、新法定主义的理论构想
如上所述,为了切实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法定主义的代表学者无不明确反对不适当的司法创设,但在是否也应同时防范立法创设的问题上,不但学者们的观点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即使是赞成者,看似也尚未投入足够的学术努力。虽然上文力图指出就其理论目标的实现而言,这种忽略看似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但仍然未能对该问题的形成从理论上进行较透彻的说明,总体上看,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以下,本文试图返回到法定主义的理论起点,⑨在此部分中,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郑胜利先生的《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一文展开。去探寻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进而提出新法定主义的理论构想。
(一)法定主义的理论深刻及其贯彻中的问题
前文对法定主义的提出作过简要总结,主要是,由于一项新型知识产权的创设,会对权利人利益以及相关公共利益都产生影响,因此所涉双方应进行充分的“公共选择”,而立法相对司法更适合作为这样的平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并补充的一个理论“细节”是,对所涉“双方”,郑胜利先生首先是在非法律人格的意义上来谈的,即:现实世界中的知识创新者,以及竞争者和消费者。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情形是,应该由这样的“真实”双方“直接”来谈判一项新型知识产权的社会认可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最理想的情形”呢?有以下两点根本性原因。一是只有真实的当事人,才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理论上,只要有代理人的介入,其真实本意的传达必然会受到影响。二是任何利益的维护都需要利益主体自身努力争取,就像经济学上常说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或如法学上常说的“为权利而斗争”。在谈判是否认可一项新型知识产权时,如果所涉双方都能满足“真实”、“在场”、“充分表达”等条件,才能形成“理想”意义上的道德共识,进而经由立法确认并进入到实施阶段。⑩参见汪丁丁:《在市场里交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页。这样的确认,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双方自愿的选择,因此法律的执行成本将会最低。虽然这种理想型无法成为现实,但其理论制约力却不容忽视,那就是,现实中的某项新型知识产权,某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其它法律,离这样的理想型越远,就越难得到民众的自觉遵守;结果是,执法成本也将相应地提升。并且,对知识产权而言,这样的理论提醒尤显重要,因为知识的公共性,使得侵权的发生“事实”上很难避免,比如买了一本书,作者与购买者远隔千里,前者根本无法控制,甚至也很难知晓后者是否进行了盗版。当然,反过来说,这也说明在知识产权法域,也许比在其它法域,更需要强调公共选择的理想型。这是郑胜利先生反复强调应由“真实双方、直接谈判”的理论深刻所在,但或许郑胜利先生自己并没有将这种深刻贯彻到底。
回到法定主义的理论中,上述的理想型公共选择当然无法直接操作,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也就是说,能否找到一种相对而言更接近这个“理想型”的途径,以使得在认可一项新型知识产权时,所涉双方能够更充分地表达。在郑胜利先生看来,显然立法途径要优于司法等其它途径,这样便有了法定主义的提出,即:知识产权只能由立法层面创设。虽然郑胜利先生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或许还是遗留了一些重要问题。不论是立法者,还是法院,从最深层意义上看,都是因无法实行理想型的公共选择,而被社会确定为所涉双方的民意代表的,其区别仅在于立法者更擅长于“见林”,而司法者更擅长于“见木”,但确立一项新型知识产权,“见林”与“见木”都很重要,并不能、至少是不能过于厚此薄彼。一方面,作为能直接接触民意的法院,并不一定就不能较好地充任这个代表角色,例如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法院,为缓解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际压力,就奉行了宽松式的司法审理。⑪参见张平:《国家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再比如,尽管我国部分法院创制权利扩张居大多数,但实际上也存在着相反的情形⑫参见梁志文:《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判例、法律方法和正当性》,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另一方面,虽然说立法者有“见林”的优势,但也不能假定其就能够更好地充任民意代表的角色,因为说到底,立法也存在其脆弱、多变、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等阴暗面。⑬参见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也就是说,在郑胜利先生提出立法相对于司法更适合作为公共选择的平台时,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如果将之绝对化为“知识产权只能由立法层面创设”,或许在理论上就有些武断。
(二)新法定主义的两个方案
如果对郑胜利先生所提出的法定主义进行高度概括,可以发现,其主要是由五个前后衔接的理论部分或说理论层次所构成,即:知识的公共性→两类利益主体(知识创新者、竞争者和消费者)→公共选择(真实双方、直接谈判)→立法创设(取代其它途径创设)→维护公共利益(尤其是因司法创设所致公共利益损害)。前三项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正好体现出了法定主义的理论深刻,问题主要是出在最后两项,表现为“只有立法者才适合”的假定与主张过于武断,以及忽略了立法创设对相关公共利益会产生更大影响的问题。为弥补后两项的不足,本文尝试提出两个新法定主义的理论方案,即:强式意义上的和弱式意义上的。之所以要提出两个方案,既是因为理论建构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方向探索,因此只有多视角观察而并无所谓定论的问题,⑭尼采曾言:没有“如此这般”的真理,只有从某一角度看的真理。也是因为现实来看任何理论转变都不会轻易发生,因此至少需要同时观照突变与渐变的两种可能。总体上看两个方案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民意代表”的问题上,该术语在前文已经使用过,是指针对新型知识产权的创设,因为理想型的公共选择无法操作,因此必须由某个公共机构作为中介来协调所涉双方利益,具体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或行政执法者等。
方案一,强式意义上的新法定主义。该方案的构成是:知识的公共性→两类利益主体(知识创新者、竞争者和消费者)→公共选择(真实双方、直接谈判)→民意代表(取代了原来的立法创设)→维护公共利益(因任一民意代表行为不当所致公共利益损害)。
与原来的法定主义相比较,前三项保持不变,后两项则进行了实质性的理论更新,其关键在于假定任一民意代表皆有其局限性,实际上,本文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该假定的逻辑展开,因此前文的主要分析都可用作提出该方案的理由。这里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任一民意代表都客观的存在其局限性。针对新型知识产权创设,相对于其它法域,理论上更应强调理想型公共选择的重要性,但由于所涉真实双方直接谈判无法现实进行,必须要借助于民意代表,而原则上,只要是“代表者”,不论其是立法者、司法者,还是其它主体,或许都无法回避所涉双方就某项新型知识产权“对谁有利”问题的追问,因为“一碗水端平”的完美协调事实上很难做到,同时也不能假定立法者就一定会优于司法者或其它主体,这种比较优势虽说可能存在,但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二是切实维护与新型知识产权创设有关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客观来看,尽管某些新型知识产权的创设的确是来自于司法途径,但是相对于立法途径的创设而言,不论在规模上、强度上,还是在对相关公共利益的实际影响上,前者都要远逊于后者,形象说,前者仅是漏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后者才是水面以下庞然大物似的冰山。既然对司法创设所致公共利益的可能损害都要批判,那么对于立法创设所致公共利益的可能损害,更不应该在理论上保持沉默。因此,在此方案中,立法创设已不再被视为理论推崇及依靠的关键,相反,其恰恰是理论反思及进一步发展的逻辑起点,而也只有如此,才有望真正实现“切实”地维护与新型知识产权创设有关的公共利益。
方案二,弱式意义上的新法定主义。该方案的构成是:知识的公共性→两类利益主体(知识创新者、竞争者和消费者)→公共选择(真实双方、直接谈判)→“立法创设”(要对该理论标志重新解读)→维护公共利益(不限于因司法创设所致公共利益损害)。
与原来的法定主义相比较,前三项保持了不变,后两项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更新,其关键在于假定对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者也允许进行怀疑,因此“立法创设”就被加上了引号。实际上,这是对原来的法定主义运用“二分法”所进行的理论重构,即:应提炼出原有理论中的方法论部分,而对具体观点(包括核心观点)则要重新进行解读。上文的主要分析可以用作提出该方案的背景性理论支撑。这里进一步展开为以下两点。一是提炼方法论部分。如前所述,原有理论的前三项构成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恰好体现出了其理论深刻,问题主要是出在第四项,即“只有立法者才适合”过于武断。因此,如果可以用一种“怀疑”的理论姿态来看待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者”,那么法定主义就有望成为一种具有更广泛适用空间的方法论。例如,鉴于可以“怀疑”立法者,那么法定主义不但应该用于分析司法创权,而且也可以用于分析立法创权,不仅是要对国内立法创权进行分析,还应将相关国际立法创权也纳入到分析范围,毕竟,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治实践深受相关国际法的制约。二是重新解读包括核心观点在内的具体理论观点。原有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个著名表述中,即:知识产权只能由立法层面创设。这个核心观点既是其理论标志,同时也是其学术论辩对手的最主要的批判所在,但在此方案的理论框架内,这个标志或许没有再继续坚守的必要,甚至可以考虑要不惜予以放弃,或者即便要坚守,看似也需进行新的理论解读,比如,这个“立法层面的创设”只能被认为具有“象征性”或“相对性”的意义,用此表述不过是要说明,立法层面创设实质上是公共选择过程的代替物,并非是不可怀疑的,也并非是不可置换的,或者只能被认为具有“相对性”的意义,用此表述不过是要说明,强调立法层面创设只是在比较意义上而言的,只是假定了一般情况下立法创设相对于司法创设可能具有某种比较优势,但并未将其绝对化。从理论效果上看,如果这样的方案能够被接受,那么其所能维护的相关公共利益将至少不再局限于因司法不当创设而致损害。
这些新的理论构想的提出,表面上看是对原来的法定主义的一种减损,但实质上是对其所具有的理论启示力的一种高度颂扬,或者是对其可能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深度贯彻。不论是原来的法定主义,还是这两类新法定主义的理论构想,无疑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理论目标,即:追求一个真正的、全面的以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本土理论。
For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Doctrine of Clausus of IPR should be alert to a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d from the judicial channels, but it isn’t clear whether the doctrine should also be against a new one created from the legislative channels. With more detail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by returning to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we can draw a new theory conception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Clausus of IPR, which is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original theory.
Doctrine of Clausus of IPR; public interest; New Doctrine of Clausus of IPR
王宏军,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8201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A820055);天津商业大学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TS09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