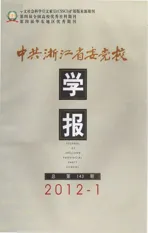政治儒学与王道政治——对蒋庆“政治儒学”思想的几点评析
2012-01-28颜华勇
□ 颜华勇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儒学渐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当今大陆儒学重建中独具特色的一派。在其中,蒋庆先生以其“铁肩担道义”的风骨和独特的言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视为当今中国政治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下简称《政治儒学》)自2003年刊行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蒋在随后的著作中(《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延续了相关的话题,并将政治儒学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构建等方面。
政治儒学所涉的议题极为广泛庞杂,要在一篇文章中对所论问题都予回应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文将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重点评析:第一、政治儒学的提出及意义。第二、王道政治的架构与评析。文章的最后提出,对于“政治儒学”的评判不能流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视阈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对“政治儒学”的本质分析,也才有可能实现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
一、“政治儒学”的提出及意义
《政治儒学》一书是从批判二十世纪新儒学没有为现代中国提供真正的儒家政治哲学开始的。蒋庆认为,这种新儒学是坚持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可以将其称之为“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在起源与发展脉络上,心性儒学“由子思、孟子开其端,宋明儒继其绪,当代新儒学发扬光大。”①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其特征在于:“心性儒学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托付,人格的成德成圣,存在的本质特征,万有的最终依据,所以,心性儒学具有个人化、形上化、内在化、超越化的倾向。”②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总之,几千年来心性儒学在安立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上发挥了莫大的作用,但是当今面对无可抵挡的现代化潮流,心性儒学显然没有做出成功的应对。于此蒋庆在《政治儒学》的开篇便指出了当代新儒学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未能开出新外王。
正是在“未能开出新外王”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政治儒学“超越”心性儒学而诞生。政治儒学源自孔子所著《春秋》,其精神主要传承于《春秋公羊学》,其“开创于孔子,发微于公羊,光大于荀子,完成于两汉(董仲舒、何休),复兴于清末(刘逢禄、康有为)。”③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页。政治儒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认为人性恶,主张用制度来约束人性与政治,标示儒家政治理想能开出新外王。④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页。它与心性儒学安立中国人的精神生命(修身以治心)不同,政治儒学目的在于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建制以治世)。按蒋庆的表述,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关系是离则两美,合则两伤。政治儒学是传统儒学中的外王之学,心性儒学是传统儒学中的内圣之学,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在根本上两者是平等对列的格局。
既然两者是平等对列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提出政治儒学呢?蒋先生论述说:“当代新儒学只有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从而才能完成自己(指传统儒学)的发展。”⑤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页。按此逻辑,只要坚持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传统儒学就可以实现伟大复兴,而未能开出新外王的历史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对其观点进行充分的批判。
第一、蒋庆对心性儒学(包括对当代新儒学)的批判是站得住脚的。蒋先生批评心性儒学未能“自然地”开出新外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现实状况,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评说。在蒋庆看来,之所以未能开出的原因在于心性儒学内部。心性儒学与当代新儒学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但其内在特质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个体生命的成德成圣为依归,以道德主体性的挺立与实践为目标的。然而要开出“外王”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其一、不仅实践主体要存有理性,还要求理性架构的建制。因为制度架构和程序设计是以理性架构为前提的。其二、还必须要求实践主体形成“对列之局”的思维方式。所以,蒋庆认为心性儒学之所以无法开出法治化的道路,实乃心性儒学只是“内圣外王”的体用之道,其本身缺乏理性化的架构、缺乏“对列之局”的思维方式。应该说这一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也直接击中了心性儒学的要害。
第二、政治儒学对儒学的传统及资源进行了新的阐释,对儒学的研究有积极意义。蒋庆主张从制度出发重新解释《六经》,认为政治儒学源自《礼》与《春秋》,最能发挥《礼》与《春秋》精神的是公羊学,从先秦的公羊、荀子,中经汉代的董仲舒、何休,到19世纪的刘蓬禄、康有为,形成了不同于心性儒学的另一支儒学传统。这就使长期受到贬抑的礼学、公羊学、荀学及汉代儒学资源得到了新的诠释与发挥,显示出儒学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第三、充分肯定政治儒学提出的强烈批判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现代化的曲折摸索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从“变器”——“变政”——“变教”——折入社会主义。⑥胡建:《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从上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人对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这两个核心问题,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上,都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还经常会在左右两个“极端方面”(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摇摆。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热烈讨论,今日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激烈论争,都还清晰可见这样的印迹。在这样的维度上,我们看到了政治儒学提出的意义,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在国内学界是被遮蔽的:蒋庆不仅对“心性儒学”加以批判,以有利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更对“全盘西化”进行声讨,加深国人对于现代化道路本身的再判定。这正如刘东超评议说:“难能可贵的是,蒋庆在《政治儒学》中对于某些现代性教条(比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民族等)表现出某种反思精神。”①刘东超:《“奇思妙想”的复古主义,读蒋庆〈政治儒学〉》,《学术评论》,2004年8月,第59页。
对于政治儒学上述意义的肯定,并不代表着对蒋先生具体观点的认同。例如上面肯定了政治儒学阐发中的批判精神,但别忘记了其批判的出发点,或许更多的是蒋先生本人的“价值情怀”而非实际出发点。再比如,在第一章第一节末尾论及政治儒学的时代使命时,蒋庆断言“鉴于此,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②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页。那么,什么是“复古更化”?为什么政治儒学的时代使命是要实现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要对此问题做深一步的分析评判,就必须先考察政治儒学基础上的中国式政治制度了。
二、王道政治的架构与评析
对于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蒋庆论述到:“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③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页。那么“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是什么?在此秩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设计又是怎样的?
蒋庆在其2004年的著作《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中做了系统的阐发。依据儒家经典,蒋庆断言,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必须由三个组成部分,即天道合法性(超越性神圣合法性)、地道合法性(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三个方面的合法性既有层次重要之分野更有结合体系之关联,三者共同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价值”层面的王道政治还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上来,方可结出“新外王”的果实。蒋庆建议,王道政治在“制度”上应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不过这里的议会制与西方的议会制却很不一样。王道政治的三院制包括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而且这三院要相互制衡,每一院都不能独大。“通儒院”代表超越性神圣的合法性,由推举与委派的儒士构成,这些儒士必须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融会贯通。“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孔府衍圣公指定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议会权力,法案须三院或二院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司法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④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4—16页。
蒋先生的“王道政治”论包含了两个层面:理念价值的合法政治秩序和实践层面的政治制度设计。于此,我们对王道政治的评析也将从这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理念上的合法政治秩序的问题。蒋先生之所以把合法秩序的问题作为构建其政治制度的起点,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包括现在)都存在着合法性缺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王绍光教授表达了不同意见:“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缺位’问题”。⑤王绍光:《“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蒋庆“儒家宪政”》,《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尽管学者们对于中国现在是否已出现合法性危机问题见仁见智,但他们关于合法政治秩序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任何政治秩序都需要赢得民众的自愿接受和支持,只建立在暴力基础的政治秩序是难以稳固和持续的。而这正是蒋庆所谓的人道合法性。不过蒋庆所言的三重合法性理论还包括天道合法性、地道合法性。在此,我们看到了蒋庆试图构建出一种既融合、又超越西方民主的政治秩序理论的努力。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肯定努力本身,而是努力本身是否值得肯定。应该说,“王道政治”是儒家先贤们一直憧憬的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原型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按蒋庆的说法,这种理想模型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上中一直未能落实。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果两千多年来这个“理想”都无法实现,它是不是仅一个美妙绚丽的“乌托邦”设想而已。
第二个层面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问题。其一、从政治制度设计的内容来看,以“三重合法性”为基础的中国新政治秩序构想,既汲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圣贤政治、王道政治、民本政治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整合了西方政治思想中合法性政治、现代民主、议会选举、程序公平等众多资源。在前面的分析中,尽管蒋庆对西方自由民主持批判态度,但他并不反对借鉴西方民主传统中的某些积极因素。蒋庆赞赏西方那种通过定期选举来保障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性创新,认为它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他认为,中国有很多需要从西方政治实践中学习的地方,诸如权力分立、司法独立、议会政治和宪政主义。然而必须提醒的是——蒋先生所强调的任何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鉴都只是建立在纯粹实用性考虑之上,他走的还是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老路。至于这条老路能否走通,中国的近代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其二、“王道政治”之本质是精英政治、“圣贤政治”。虽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有所谓的议会三院制,也讲求普选和民主,但蒋庆从根本上否定西方自启蒙以来人人平等和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的原则。他确信,“人在现实的道德层面……差别非常大,有圣贤凡人与君子小人之别,并且这种道德的差别具有政治统治的意义”。①蒋庆:《王官学、政治保守与合法性重建》,《〈南都周刊〉蒋庆专访》2007年8月。这意味着,他完全接受“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这些论断。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很认同王绍光先生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儒教宪政”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构想;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精英主义,而是儒士精英主义,或以儒士为核心的精英主义。”②王绍光:《“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蒋庆“儒家宪政”》,《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其三、对现代民主的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在蒋先生看来,“民主不像科学,并不是天下的公器、人类的共法,现代民主只是西方历史上形成的具有西方特色的一整套观念与制度。”③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6页。“所谓现代民主不过是西方本土的实践经验,并不具备普世的价值,而在儒家传统文化之下,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与在当代西方占据支配位置的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模式。”④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9页。在这样的论述中,一方面要肯定蒋庆对现代民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判定:即民主的确是近代西方本土实践的产物,在民主的操作层面上要立足于本民族之实际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强调。
但另一方面,难道民主真的不具有普世价值吗?在儒家传统文化之上,就真能形成一种与在当代西方占据支配位置的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民主模式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政治学公理》一文中写到:“民主政治在近代西方出生后,很快就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制度,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治选择。”⑤俞可平:《政治学公理》,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61页。因此,民主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成为了俞可平心目中四条“政治学公理”的核心要义所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是任何民族国家所必须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尽管现代化有着浓重的西方“性格”与色彩,但这种由“资本逻辑”发轫而来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公正的现代性精神追求,无可置疑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因此,在对民主的认识上,我们应保有这样的认识:即民主价值是普适性的,但实现方式必然是多元的。
其四、把儒学定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蒋庆在《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中国政治秩序重构和儒学复兴的建议和策略。在国家的层次上,蒋庆提议宪法应该确立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应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并通过以此为基础的考试(被视为一种现代科举制度)。在社会层次,他提议建立中国儒教协会,而儒教协会应该在国家宗教生活中被赋予一定的特殊地位;社会儒学复兴当然还包括促进儿童和学生对儒家典籍的学习等等。总之,所谓重建儒教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儒学定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此,香港大学的陈祖为教授在评论蒋庆的政治思想时指出:“蒋先生的见解似乎违反了现代多元开放社会的理念,即在其中具有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寻求合作,一起生活。尽管韦伯(Weber)的世界祛魅命题原初是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的状况,但似乎正日趋适用于中国,而蒋庆却尝试通过政治上的重构来寻求世界的重魅化。”①范瑞平:《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因此,蒋氏民主非但“不民主”(本质上是圣贤政治)、“不自由”(对现代多元性社会的否定),而且丢失了传统儒学的宽容与和谐,大有滑落“家长式统治”、“暴力政治”的可能。
三、中国现代化历史视阈中的“政治儒学”再评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蒋庆是在对“心性儒学”和“全盘西化论”双重批判基础上提出“政治儒学”的,正是这种起点的双重批判,也奠定了“政治儒学”提出所应有的意义(尽管对于这种意义的评说还是大有出入的)。在蒋先生看来,“王道政治”是“政治儒学”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如果“王道政治”不能在当代中国历史创立的话,那么所谓的“政治儒学”复兴(或者说“儒学的当代复兴”)也只是美好的“乌托邦”罢了。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上面“静观式”的考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阈中来把握和评析“政治儒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政治儒学”有更深入更本质的理解。
一方面从儒学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蒋庆先生提出的“政治儒学”其实是对现代新儒学的“接着说”。中国是被动地开启现代化历史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间,这段现代化历程大体呈现出从“器物——科技——制度——文化”的追求与反思过程。可以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反思批判传统的过程,而这种批判在“五四”时期以最激烈的“打到孔家店”的割断传统的方式体现出来。当然,面对如此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自身也必须主动进行回应,而现代新儒学就是这种回应的产物。“现代新儒学自20世纪20年代发生、发展以来,主要体现为文化儒学与形上儒学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的新儒学,都是现代新儒学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的重建儒学的努力。”②李维武:《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第16页。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是文化儒学的开创和代表之作,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可以说是形上儒学所重建的第一个完整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尽管张君劢、徐复观等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做出过不少的关心和努力,也大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然而,张君劢的政治哲学明显地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而徐复观的政治哲学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家道德精神的结合,而不是“融合”。因此,相比于文化儒学和形而上儒学的重建,政治儒学在现代新儒家的视野中的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庆接过了现代新儒学历史发展的“接力棒”。可以说,蒋庆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政治儒学的理论,尽管这套理论还比较粗糙,也还没有定型,但却已经向人们昭示了政治儒学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一个新形态的出现,并且正在继续展开中。
另一方面,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现实来看,可以说“政治儒学”紧紧抓住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历史大问题,尽管对其“王道政治”的具体道路设计我们不敢苟同。但笔者认为,我们只有把“政治儒学”放置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阈中才能做出较为理性的评析;相反,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站在“保守派”或“西化派”的立场,对“政治儒学”做出道德的褒奖或谴责,无论这样的评析具有怎样的“技术含量”,它都有“从反面滑入主观主义的危险”③胡建:《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吴晓明教授写的)序言第3页。。
即使蒋庆一直都在强调他是在充分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资源的基础上,来创建“政治儒学构想下的中国式政治制度”的。不过,当他提出通过重建儒教来实现中国式的政治制度时,并以此来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我们总是会怀疑很多、质疑更多。对此,笔者认为,蒋先生可能最大的失察还是在于对“儒学自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定位”问题。尽管蒋先生在《政治儒学》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甘阳、林毓生、余英时等学者对于儒学的错误判定,然而笔者认为恰恰是蒋先生自己对“政治儒学”、乃至对于整个儒学的定位出现了重大问题。
当蒋庆批判“心性儒学”最大的弊端在于不能开出“新外王”,而“政治儒学”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中国式的礼法政治制度时,其背后的言说就是——所谓的“儒学复兴”必定是“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复兴。而这是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势截然矛盾的。当代大陆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郭齐勇教授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到:“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有一种自觉,即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政治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今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学之结合有广阔的前景。在经济全球化、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儒学与自由主义有内在的紧张,但三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结盟已是客观之大势。”①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第62页。郭齐勇教授在此已明确表达了儒学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历史的可能未来。不过,他没有点破的是——这样的融合是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融合,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融合。对此,邹诗鹏教授更为明确的表述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②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9页。
总之,儒学要复兴就必须首先承认这样的前提——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多元的发展格局。也只有把儒学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儒学才有可能在守常中有应变,在返本中有开新。因此,无论是现代新儒家还是政治儒学的倡导者怀着怎样悲天悯人的情怀,儒学都已不可能在为中华民族独自承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重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