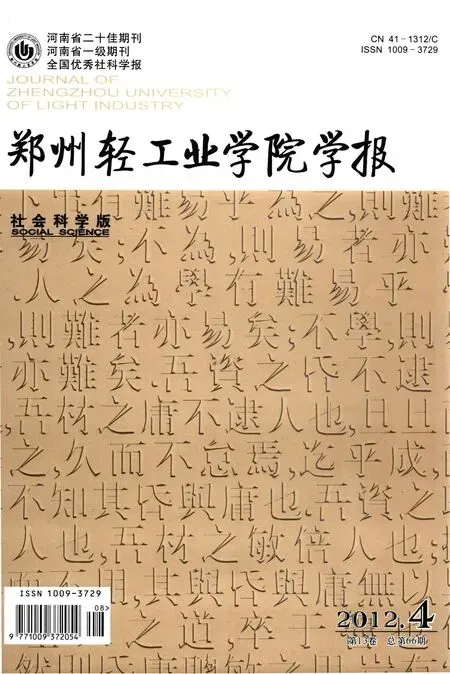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
2012-01-27欧阳敏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012年1月1日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中华书局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何以能够与商务印书馆一道成为民国时期出版界的“双子星座”?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缘于中华书局的高远定位和文化与商务的平衡艺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华书局的成功之道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就笔者已掌握的文献来看,有一些研究涉及到了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从侧面谈到了企业管理制度,缺少对中华书局企业管理制度系统的专题性研究。本文意在综合运用编辑学、出版学和管理学的理论知识,结合相关史料,对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
中华书局初创时是5人集资的合伙制公司,1年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中华书局逐步制定了较为科学化、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发行渠道管理以及危机管理等。
一、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企业进行的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培养使用及组织等各项管理工作的总称。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的规律和方法,正确处理和协调生产经营过程中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协调,实现最优组合,做到人事相宜、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1](P302)实践中,中华书局在人员进用、培训、考核以及激励等方面逐步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保证了其经营目标的顺利达成。
1.书局进人的方式
中华书局进用员工主要有4种方式:一是经熟人介绍进局;二是聘请;三是培训;四是考试录用。前两种方式主要表现在进用编辑方面,是非常态的方式。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近乎托拉斯的大型出版企业,在组织机构方面设有“一处三所”,即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编辑所是书局中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为书局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编辑人员大多是学有所长、术有所专的优秀人才。“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包括局外编辑),其中不乏知名人士,早期有梁启超、范源廉、徐元诰、马君武、戴懋哉、张相、高野侯等人,以后有舒新城、金兆梓、田汉、张闻天、左舜生、陈启天、潘汉年、王宠惠、李登辉、徐志摩、谢无量、马润卿、张士一、朱文叔、章丹枫、周宪文、钱歌川、钱亦石、张梦麟、周伯棣、郑午昌、葛绥成、桂绍盱、武育干、陈伯吹、李平心等人。”[2]他们或是由熟人朋友引荐介绍,或是由书店直接物色聘请,或是经招考择优选拔录用进入中华书局的,担任着选题组稿、编辑加工乃至著述编译等重要工作[3]。此外,进人的非常态化方式在1932年以前的各分局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分局经理们在人事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存在着引用同乡戚族的现象,容易产生财务监督管理上的弊端。为了防止此类弊端,1932年10月,陆费逵提请董事会通过了分局用人标准的规定,“分局用人,经理同乡介绍者,考试录取额不得超过四分之一,须凭考卷照片经过总局核准。经理绝对不得任用戚族。前用同乡超过四分之一者,应该酌量辞退”。[4](P335)
培训也是中华书局的一种非常态进人方式,包括委托代培和自办培训。委托代培方面,1922年9月,中华书局曾经委托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开办国语商业夜校,招收学员60名,设有国语、商业及书业常识(编辑、出版、印刷)等课程,陆费逵亲自讲课,题为“书业商之修养”。学生毕业以后量才录用。自办培训方面,1935年9月,中华书局自设职业训练所,由舒新城、王酌清、薛季安、武佛航等组成委员会,日常理事由武佛航教授负责。招收学员30人,学习期1年,前半年全日上课,后半年白天派往各部实习,晚间上课,供膳宿,不收学费,视月考成绩给予奖金4~12元,或令退学。录用后月薪为25~45元。同年12月,又招一期,至1936年10月结束。[4](P333)书局自招学员并加以培训有两个好处:一是中华书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锻造所需要的员工,使员工的素养与书局的要求高度统一起来;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书局具有很高的忠诚度,能够保证书局人员的稳定,有利于书局的长远发展。
考试是中华书局进人的常态化方式。早在1913年5月,董事局就制定了《任用职员规程》,规定进用职员,除特别延聘外,一律要经过考试、试用,合格后正式录用;以考试为原则,以举荐为例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6年的25年间,在《申报》上刊登招聘及招考广告,共有20多次,招聘和招考的人员,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学习员、学生等。[4](P332)针对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考试方式:对于应聘中高级岗位者,先报名再函约面试;对于应聘初级岗位者,实行集体考试。集体考试报考人数超过1 000人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36年5月的一次考试,报名者有1 700多名,最后录取42人;第二次是1940年6月的一次,报考者有1 300多名,最后录取60名。对于1940年的这次考试,当时还有面试者写了一篇“应试记”[5]发表在《申报》上,摘录如下。
这次投考的资格,规定:(1)初中毕业执有文凭者;(2)本届暑期毕业之初中生;(3)高中肄业曾在其他商业机关服务者;并需精通写算,略懂一些薄记。手续很简单,只要你写一封自荐信,寄至哈同路中华书局驻沪办事处,并附半身照片一张就行了……这次公开考试,报名的人数差不多有1 300余人。
经过严格的选剔后,准予应试的记240余人,考期是上星期日上午,地点假南阳路滨海中学。
……主考者为该局账务部主任武育干先生等……
考试的科目分国文,英文,常识,算数与薄记等四种。国文题目很是简便的,做作文一篇,题目是“求学与求业”。
英文试题计分两类,(1)名词译英,共生字六个,信纸,信封,自来水笔,折扣,发票,收购,大都关于商业方面。(2)词句译汉,包括词句十一题:关于商业方面的,如Draft,bill,Here is a bottle of bright quality等。关于常识方面的,如Season,ticket,elevator,telephone等。
常识试题凡九个,内容无所不有,例如:(1)现在往重庆有几条路可走?其经过重要地方试列举之。(2)你所喜欢读的书籍和杂志有些什么,列举出来并分别说明其优点何在?……(4)“投机”与“投资”有何不同?
……
听说这次名额内定六十名,考取者分派该局账务部,编辑所,发行所等处服务。在服务期间,除支取正薪外,尚有基本津贴,生活津贴等等。将来习业期满还可升为正式职员。
揭晓约须在一月之后,因为录取名单定夺后,照例须转香港总局请核。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书局考试制度之规范。严格的考试选拔使那些具有真才实学、自身素质符合书局要求的人员能够“得其所”,进而在工作中“尽其才”。
2.员工的培养方式
中华书局是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的出版企业,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企业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实现,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文化水平,使员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
由于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不同部门的员工在文化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应充分考虑到他们对文化知识的不同需求。总的说来,中华书局员工的培养方式主要有设立中华书局图书馆、支持员工结社、资助员工出国深造、鼓励员工业余进修等。这些多样化、分层次的培养方式,使中华书局的大部分职工都从中受益。
3.员工的激励方式
中华书局对员工的激励方式主要有工资激励、奖励金激励、福利待遇激励以及附股激励等。
首先,中华书局的员工工资待遇在业界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与其他同行相比居于中上水平,而高级编辑的待遇则较商务印书馆为优。当时的很多年轻人都以能到中华书局做事感到光荣,原因之一就是相对丰厚的工资待遇。其次,在奖励金方面,中华书局对有重大功绩员工的奖励是非常慷慨的,舒新城在1936年4月5日的日记中有记述:“去年公司因印刷营业特好,而瑾士对于印刷研究与发明之功至大。伯鸿去年赠以五千元特别酬劳,我尚嫌少。”当时总经理陆费逵的月薪为400元,5 000元的奖励金分量是相当重的。再次,在福利待遇上中华书局充分做到了以人为本,1920年根据《同人储蓄寿险章程》设立了寿险部,开办同人储蓄寿险,便利同人福利,共谋幸福。逢有员工去世,书局还会送治丧费与抚恤金,并担负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费用,这些措施可以让员工们无后顾之忧,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对书局的向心力。最后,在员工附股方面,中华书局对工作绩效突出的员工通过允许其认购公司股份的方式来作为回馈,如总店店长李默飞为中华书局编教科书出力甚多,书局便允其以编辑费1 300元附股。以附股作为激励的方式既可以留住人才,同时也可以增加书局的发展资金,对书局扩大生产规模和开展多种经营是有好处的。
二、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指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资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管理的总称。[1](P287)中华书局的财务管理在1917年以前较为混乱,1917年以后逐步建立起完整严密的财务管理体系。
中华书局初期的领导班子由6个人组成: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沈继方和沈知方。陆费逵和沈知方都是出版业难得的多面手,精通出版与发行,戴克敦、陈寅、沈颐以前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沈继方在商务从事保管等事务,对出版业务不太精通,他原先能拆借资金的本领因自己破产之后也难以施展”[6],因此在6人中除了沈继方,其他人对财务管理均不在行,沈继方由是于1913—1916年任中华书局监察之职,1916年病逝于任上,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沈继方在中华书局的财务监管上并未有大的作为。
1917年,中华书局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称为“民六危机”,中华书局财务管理上的混乱在这次危机中彻底暴露出来。在“民六危机”中,武进士绅吴镜渊以垫款人身份进入中华书局,继由股东查账代表当选为监察、驻局监察、驻局董事和常务理事,负责对企业进行改革,对分局进行整顿。“吴氏深知经济是企业的命脉,首先要堵塞漏洞,掌握稽核这一关,于是董事会议决:‘公司逐日账目,应由监察检阅,月终将支款凭证交监察审核无误,应于总结处盖印,年终于总清各款总结处盖印。’又为健全账务制度,全权委托吴镜渊办理。后来又于监察之下设稽核处,由吴镜渊任主任,其下分设核算员、稽核员,对于总店和各分局严加稽核各部账目”[7](P213),吴镜渊善于理财,在汉冶萍查账案中颇有名声,他对待工作又极认真极负责,“吴老先生到中华后,办事严明细致,确实使人敬佩。大事不用说,就是连一只痰盂都要编号入册,有专人负责管理”[7](P214)。
经过吴镜渊的一番努力,中华书局得以建立起较为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由常务理事吴镜渊代表董事会对企业进行财务监管和审查,后来这也成为中华书局的定例。此后的中华书局虽然也遭受过一些波折,但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始终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得益于吴镜渊对中华书局的财务管理系统的改革与完善。
三、精品化与多元化的生产管理
中华书局在生产管理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产品生产的精品化,二是生产经营的多元化。
1.产品生产的精品化管理
中华书局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高品质的学术出版机构,这与中华书局所坚持实行的精品化生产管理是分不开的。中华书局的精品化管理贯穿于图书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图书的文字出错率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在图书版式设计、装帧、用纸等方面也达到了业界的领先水平。
当时中华书局为了在图书的印刷质量上取胜,花重金从美、德等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白度较高、强度较好的道林纸,使图书在形式上得以取胜。形式上的精品化还需要图书内容的精品化相呼应,这从《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大部头图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可以窥见一斑。这些大部头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参与的人员多、持续的时间长、耗费的资金大,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在这样大型的编辑出版活动中,要将精品化管理贯彻始终,客观上来讲是一个管理难题,但是中华书局用主观上的努力化解了这一客观上的难题。总的来说,这些大部头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的精品化管理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工作的计划性强。以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为例,“影印这样一部大书,其工作量相当巨大而又艰巨,必须配合出书时间组织各个环节协调进行,在编辑出版部门挖潜力,并指派业余加班,相互合作,分工负责,共同努力完成出书任务。属于编辑部门的工作,由舒新城所长负责……属于出版部门的工作由路费叔辰部长领导”[8]。又如《辞海》,由于已经有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专美在前”,所以中华书局的《辞海》要想后来居上就必须在内容上有所创新。中华书局为了全力打造《辞海》不同于《辞源》的独到之处,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直到1928年才由舒新城开始正式主持《辞海》的编辑工作,但由于工作计划抓得不紧,计划性不强,进展并不理想,于是陆费逵又于1930年延聘当时在北京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沈朵山来主事。沈到任后锐意革新,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重新调用人员,终于在1936年上半年出版了《辞海》的上册。中华书局的几部大部头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时间跨度大,要是没有周密的计划,完成这样浩大的精品图书出版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严格的全程质量把关。中华书局的图书注重精编精校,编校质量之高获得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认可。《四部备要》的编辑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四部备要》之前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注重实用而非版本,因而《四部备要》选用的版本是经过清代学者校勘、考证过的印本。《四部备要》在编印之初就请宿儒悉心校对多至10余次,对原书中的讹误之处进行处理,出版后又多次勘误。到1934年重印时,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称如果能在《四部备要》中发现一个错字就能获得10银元的酬金,这件事被传为业界美谈。全程质量把关是中华书局实行精品管理、打造精品图书的要诀。
2.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管理
中华书局的主营业务是图书出版,在主营业务之外又兼做其他经营,主要有大力发展印刷业务、发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培训机构等。这些副业不仅为中华书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中华书局的多元化经营势必要求生产管理上的多元化,中华书局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管理基于这样的经营理念:书业为主,印刷为辅,多业为补。
中华书局首先是一家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的文化企业,这也是其文化使命之所在。因此,书业是书局产品生产经营的重心。中华书局长期稳居民国出版业第二的位置,在图书出版的品种和质量上也无愧于这个位置。1912—1949年的38年中,中华书局共计出版图书5 908种,约占民国出版物总数的14%。
印刷业是中华书局一大经济支柱。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营业额在总营业额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1936年以前所占的比例大概在20%~30%之间,“1936年5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6年间,共计承印钞券21批,营业额累积达2 800余万元,平均每年营业额达470余万元,约占中华书局营业额的45%”[9],这一比例远高于同时期商务印书馆的9.37%。印刷业虽然是中华书局的经济支柱,但其定位仍然是辅业,原因就在于中华书局是提供内容的文化企业。
发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机构等是作为中华书局的补充业务而存在的,这些副业不仅带来了经济利润,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华书局在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实现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增值。
四、发行渠道管理
今天的出版界有“渠道为王”的说法。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出版界对此体会得就较为深刻,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路子。中华书局的主要创办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中脱离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在业界做得很成功,主要包括创办分支馆、组建现批处、设立特约经销处和经销店。中华书局在发行渠道管理上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做法,同时又根据自身情况有所改进。
1.创办分支局
中华书局趁商务印书馆误判形势之机,靠着《中华教科书》系列迅速夺走了原本属于商务印书馆的部分教科书市场份额,从而站稳了脚跟,开始与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中华书局能够迅速打开市场与广设分支局是分不开的,当时在北京、天津、奉天、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温州设立了9处分支局。限于人力和财力,又为了快速打开局面,在设立分支局时曾广泛采取与当地士绅合资开办分支局的方式,如初期的9处分支局中南京、奉天、北京、天津、杭州5处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办的。后来中华书局实力壮大了,合办书局也就陆续收回自办了。到解放前,中华书局在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分支局已达40余处,其中只有济南教育图书社和青岛分局仍是合资设立的。
中华书局对分局的监督管理颇为严格,印有两本《办事通则》,为管理分局的规章制度;将全国的分局分为若干区,每个区设一名监理人,以便就近监督分局;将对分局的视察作为一项常规工作,1936年6月专门制定了《视察分局简章》14条并通告施行。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推销本局出版图书,推销的手段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依靠当地旧书店代为推销,这需要给回扣;二是依靠当地中小学校长,校长手中握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对教材的选用有决定权;三是依靠当地乡绅,请他们向中小学施加影响。
中华书局选择分局经理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一)品德较优,(二)文化水平较高,(三)是本业的同行,(四)要懂一点经济”[10]。总店、分局、印刷所是中华书局利润的三大来源,其中尤以分局为大,1921—1935年间,分支局对利润的平均贡献率为35.61%。分局的重要性对中华书局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分局经理的选择上也就慎之又慎。
2.设立特约经销处
中华书局创立后的头几年,业务呈井喷式发展,为了铺设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除了建立分支局外,设立特约经销处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全国有不少城市都设立了特约经销处,经销处有的是独立招牌,有的则挂“中华书局x记”,称“挂牌分局”,如扬州的“中华书局峻记”。这些特约经销处由于地处中小城市,市场份额有限,所以既做零售也做批发,有效填补了分布于大城市的分支局发行网络的遗漏之处。
3.添设通信贩卖部
通信贩卖部是通过邮政系统来满足顾客对图书、文具、仪器等需求的零售发行机构。1917年,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相关广告[11]:
本局现为方便内地顾客起见,特设通信贩卖部于上海总店,不独本局出版之件可以函购,即上海各种物品亦可代买,办法如下:
贩卖品:(甲)本局出版书籍、仪器、文具、笔墨、信笺、信封、名人对联、画屏、折扇及欧美原版书籍……(乙)上海书肆出版图书;(丙)各药房药品及一切饮食衣着品……
通信贩卖部做的是零售,既销售本版图书也销售非本版图书,同时还兼售其他学习或生活用品。这种零售形式的发行渠道是对书局批发渠道的一种有益补充。今天的出版企业除了批发业务之外,也通过邮局做零售服务,零售并非出版企业的主要发行方式,但仍然要做,原因就在于零售服务能够满足顾客的个体消费需求,体现出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对出版企业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有积极作用。
五、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指组织机构在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针对可能面临或正在面临的危机,为了预防和消除系统内的不平衡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乃至变危险为机会。[12]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1960年代,但是有关危机管理的实践要远远早于其理论。中华书局浮沉民国书海38年,经历了许多波折,主要有:1917年“民六危机”;1916年与商务印书馆争夺《饮冰室合集》版权;1919年商务印书馆控告中华书局“毁誉”案;1927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1934年《闲话扬州人》被控案。中华书局最终都妥善处理了这些危机,化险为夷,其危机管理实践对今天的出版界是有参考价值的,主要经验有以下3点。
1.重视与媒体的合作
以上所列举的危机在《申报》上都可以见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记者主动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华书局主动与媒体合作,在媒体上刊登启事或声明。《申报》是中华书局选择合作的首要媒体,除了《申报》外,《大公报》《晨报》等当时的主流媒体也是中华书局进行媒体公关的舞台。在“民六危机”中,中华书局就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告示,主要是针对顾客和股东。在1917年8月8日的《申报》上,中华书局就刊登了敬告各埠同行的启事,声明秋季应用各书正在日夜赶印,已陆续发出,绝不误期,可就近向各分局配货,万勿为造谣者所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华书局又陆续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向社会告知书局的最新情况,向股东谋求偿还债务的办法,有效缓解了股东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谣言止于智者”,今天的出版业在面对危机时更要有勇气直面媒体,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
2.积极谋求行业协会的支持
民国时期上海有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属于上海商会的一个分支,是出版印刷业的行业协会。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对规范同业的经营行为、协调同业之间的关系、协助同业应对危机等方面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曾长期担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有一定的威望。关于书业同业公会的职责所在,陆费逵曾在1932年就北新书局所出书籍侮辱回教一案中表达过他的观点[13]:
北新侮辱回教之文字确实不堪寓目,不特回教同人痛恨,即书业中人亦多认此类刊物足贻出版界之羞。迩来屡有人函至书业同业公会,责问及此,但同业公会实无权取缔之……今因以行政处分、变更法律,其影响之巨不堪设想,至此不能再事旁观,始登启示,冀与回教代表协商补救办法,此举固为出版界全体利益计,亦为全国人民法律保障计……总之,北新案如依法办理,无论其结果如何不利于北新,书业公会绝无异议,但不经法律手续而废封,想不以为然者,不独书业同人而已也……
陆费逵的这一表态是很明确的,即书业同业公会对同业触犯法律的经营行为绝不护短包庇,但如果不公正的法律威胁到书业同业的利益,公会也绝不会作壁上观,书业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同业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当利益。因此,在“民六危机”、工潮事件以及《闲话扬州人》案中,书业同业公会都曾出面协助中华书局度过难关。
3.主要领导勇担责任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发起创办,其后他一直担任书局的领导职务,前后长达30年,任职之专且久在业界也是罕见的。在1941年以前中华书局所遇到的每次危机中陆费逵都能够直面危机,冷静、理智地进行处理。尤其是在“民六危机”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他的好友汪汉溪请他去做《新闻报》的主笔,范源廉请他去教育部任职,他都拒绝了,选择留在书局和同人一道为书局摆脱困境殚精竭虑。在1927年的工潮中,陆费逵直接与工人代表沟通,并发表了一篇真挚的谈话,对危机的解决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危机面前,逃避没有出路,直面危机、勇担责任是企业家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六、中华书局企业管理制度对当今出版业的启示
中华书局比较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支撑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企业典范的原因之一,但是其企业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譬如,“人治色彩”较浓(主要是相对商务印书馆而言),陆费逵的个人权威对企业的“法治”造成了客观上的威胁,尽管陆费逵主观上是严格按照企业的规程来行事;发行上,与同行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不规范行为;印刷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值过大,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企业的文化色彩等。对于历史,我们不能苛求,瑕不掩瑜,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当时是走在行业前列的,成功地做到了文化与“商务”的巧妙平衡,也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这对今天的出版业是有启示意义的。
首先,找准自身定位,关注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在当今出版业中有被淡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当前,一些出版社对自身没有准确的定位,在出版活动中过于功利化,“只出赚钱的书,不出亏本的书”。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社对于赚钱的书要大量出,明知会亏本的社会效益型书也要适当出。很多时候,“亏本书”虽然会给出版社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却能带来社会效益,这是出版社宝贵的无形资产。出版的本质是文化传承,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价值还在于文化上的创造和贡献,出版社应该始终把对文化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因此,出版社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出版活动中注重社会效益,对过去和当今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行挖掘、整理、加工,运用现代化手段以符合公众认知模式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定位,商务印书馆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中华书局的“关注国民教育”给我们今天的出版行业树立了榜样,对社会效益的注重是出版行业的优秀传统和使命所在。
其次,创新出版理念,拓展经济效益。出版行业自身盈利能力不足,经济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当今出版业发展的又一困境。出版行业的三大板块分别是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产品主要是教辅教材,教辅教材出版是很多出版社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随着教改方案的实施和学龄人数的减少,教辅教材带来的利润锐减。而在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对阅读人群的分流导致利润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总体上,就出版行业自身来说,其盈利能力是在衰减的。因此,出版行业需要转变思维,利用新技术开创新的盈利模式。具体来讲,出版业要树立“大出版”理念,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何为“大出版”?笔者以为出版业的“大出版”就是指出版业要在以图书出版为基础的前提下,涉足酒店、房地产、金融、物流、信息咨询等多领域的经营。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书业为主、印刷为辅、多业为补”的经营方针或许能带来一点启示。除了图书出版以及印刷业外,中华书局还办过文具仪器厂和学校,利用厂基地建住宅楼对外出售,投资设立中华大药房等,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对“大出版”或是一种诠释。传统出版正在逐步衰落,数字出版正在强势崛起。出版业转向数字出版是必然的选择。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业、酒店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等行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整合到一起,出版业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涉足其他领域的经营,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效益,对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和梳理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笔者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史海钩沉,磨洗之后,或许于解决今日出版业管理制度之疑难与困惑有些许助益。
[1] 李启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M].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C]//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81.
[3] 吴永贵,曹琳娜.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管理[J].中国编辑,2006(2):88.
[4] 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C]//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三原.中华书局练习生、学习员应试记[N].申报,1940-06-24(12).
[6] 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史料杂录(之二)[J].出版发行研究,1994(4):45.
[7] 吴中.我所知道的“维华银团”[C]//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孙荦人.《古今图书集成》影印经过见[C]//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169.
[9] 余筱尧.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C]//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232.
[10] 陈世觉.我的回忆[C]//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178.
[11] 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添设通讯贩卖部[N].申报,1917-02-16(2).
[12] 董传仪.危机管理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7.
[13] 《申报》记者.陆费伯鸿谈北新书局案[N].申报,1932-03-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