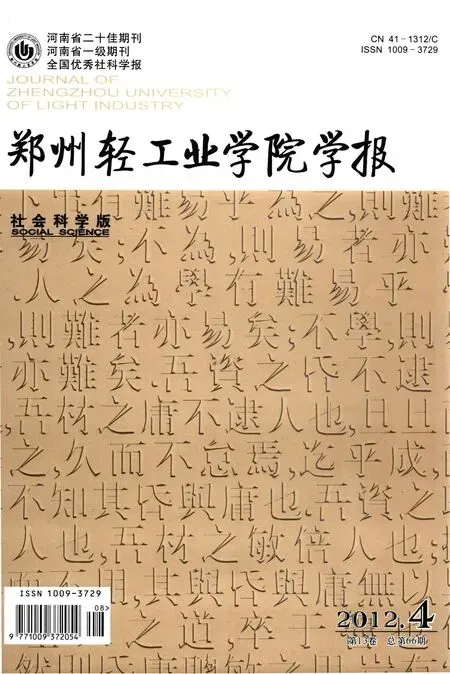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及其伦理简析
2012-01-27张斌
张斌
(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河南郑州450008)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等弊病。首先,科学技术运用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观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自然仅仅被看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因此科技工具化必然会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其次,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为了逃避劳动异化,人们试图通过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来获得自由和体验幸福,而实质上这种商品消费并不是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徒具替代意义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本身也不可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以利己与逐利为特征,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绝对化,即对资本增殖的无穷需要和无限追逐。这就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无限开发和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从而使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无法避免,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绝对化的矛盾由此产生。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全球范围扩展,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造成了国际环境的不正义,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
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1](P29)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及相应的资源开发,当其国内的原材料和资源无法维系其经济规模时,就把资源消耗的触角同经济殖民主义一起伸向全球,通过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将不发达国家变为他们的原料掠夺地、废弃物接收地和污染工业转移地,在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危机。正如福斯特所说,生态危机的根源“还是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逻辑中寻找答案”[1](P1)。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正在不断将环保目标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但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扩张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范围、变换了资本增殖的方式罢了,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
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生态系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既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公平,又造成了国际环境的非正义;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的追逐造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人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与生态问题相关的人类生存危机。这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并用生态殖民主义揭示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扩张和生态危机转嫁的行径。然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非正义性,更在于如何变革反生态、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正义的社会制度。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揭示出资本主义“以漠视环境需求所换来的利益仅使少数人暴富”,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必然导致为争取环境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因此“为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也正在前所未有地与为保护地球而进行的斗争汇合在一起”。[1](P34-35)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一个适应生态要求的没有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2](P439-440)。
生态社会主义实行分散化、生产性正义、适度增长、建立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主要用投入与产出来衡量经济发展而置环境、社会成本于不顾的外部性发展模式,它只会加剧生态危机。资本主义还通过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来操纵消费者,其结果使人们把获得自由和体验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造成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代之以分散化、生产性正义为特征的“稳态经济”生产模式。“分散化”指的是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产品,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绝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2](P538)。这种“稳态经济”是适度的、“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1](P42)的增长,人们把需要的满足建立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消费过程中,劳动成为创造性劳动和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经济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3](P129)。“稳态经济”能够满足人们的真实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环境,人们同自然保持和谐,又彼此平等相处。[4]
生态社会主义下的政治制度实行以“非官僚化”为特征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规模化经济、科层制政治、消费主义文化而高度操纵着整个社会,其结果必然导致官僚化。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基层民主,反对官僚化,认为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严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在政治上把权力释放到基层,真正贯彻权力“非官僚化”的民主政治原则。“非官僚化”是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高度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人们直接参与事务决策和管理的体制,让人们真正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本身的快乐,彻底消除异化劳动,实现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真正体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变革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地与“控制自然”的世界观紧密相联,而消费异化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走向紧张。“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1](P1)价值观的变革就是这种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内容。那么,如何实现价值观的变革呢?首先,应以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代替“控制自然”的价值观。这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5](P354),但它又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5](P340)。其次,应树立基于人的本质的正确的劳动观、消费观、需要观和幸福观。人的本质需要最终在于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只有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处理好劳动、消费、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创造过程中体验幸福和获得自由,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决定了必须树立环境正义的价值观,才能使环境运动走向全球一致的生态政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执着于经济理性并全然违反生态理性,而且还利用资本的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生态环境问题,最终破坏了全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生态根基,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6]“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3](P43)
三、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变革的伦理简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大致包括上述批判和建构两方面的内容,批判是为了建构并为建构提出问题,建构以批判为前提并化解批判揭示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当今全球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揭示了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正义问题。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导致的新问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对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围绕生态问题所提出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方案,在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是否就是一种有效的通向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方式还有待考量。毕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是基于当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经验和矛盾现实而提出来的,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西方话语系统。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制度变革方案缺少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存在状况和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例如,如果实行“稳态经济”模式,虽然可能解决局部生态问题,但是不是有维持不平等现状之嫌?这种经济正义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还未得到根本保障的情况下,如何遵循“理性适度”原则?这些问题并未进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如果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剥夺后发展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种环境正义只能是实质上的非正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还是应从人类的利益出发,依靠实践理性去纠正我们的环境价值观念,规范我们的环境开发行为,既要强调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以保护环境,又要看到人类社会内部利益协调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条件。我们对正义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外部的某种秩序和规则的基本认同与践行上,更应深入到秩序和规则背后,探究其是否蕴含着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的自由自觉本质的价值承诺。[4]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变革的方案具有主观改良的成分,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小规模技术和生产来避免由大规模技术和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但取消和否定大规模技术和生产就等同于取消和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果——虽然小规模生产技术和生产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坚持生态的、基层民主的和非暴力的原则,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变革的依靠力量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生态意识、认识到理想社会的美好性并自觉为之奋斗的中下层人身上,并力图得到其他政党代表、公司经理们的同情与支持以及政府的“资助”。显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幻想,具有典型的改良色彩。
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逻辑关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克服生态危机、建构正义制度上缺乏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存在状况和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带有乌托邦色彩,很难真正解决环境危机和社会正义的双重难题,但它把生态危机与正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模式为环境正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对“稳态经济”、生产性正义、生态政治等内容的论述为环境正义实践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借鉴其关于制度伦理的理论资源,从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为构建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价值支持。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生态危机的真正克服,一方面在于人的全面提升,即由个体人向类主体的发展,由人的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向人的丰富性创造性发展转变;另一方面,由于造成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非正义性,是社会关系结构的不合理或非正义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造了“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关键还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权力结构的变革重建通向正义制度之路,以达致自然、人、社会之间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王桂艳.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观刍议[J].思想战线,2008(3):55.
[5]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 王雨辰.生态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J].哲学研究,2007(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