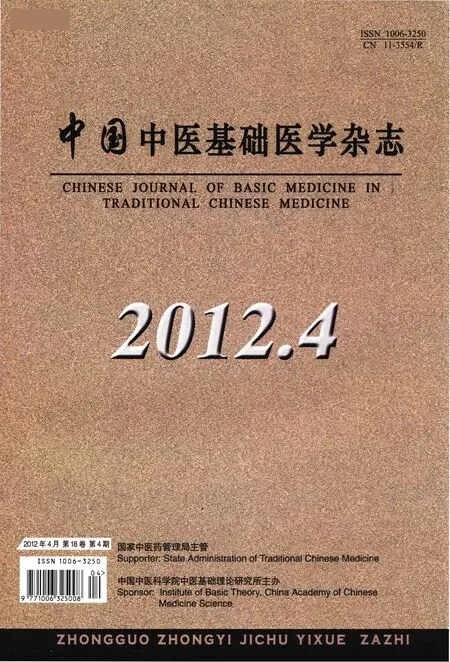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及其临床价值*
2012-01-25董正平严哲琳肖相如
董正平,严哲琳,肖相如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3.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导师肖相如教授3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外感病初期辨治方法的思考和研究,并于近年发表了多篇与中医表证理论相关的论文,其研究成果条理清晰、自成体系。笔者将其相关论述加以归纳总结,并命名为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笔者体会,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虽属一家之言,却对临床辨治外感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不揣孤陋,将点滴学习心得汇报如下。
1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的思想渊源
肖相如教授通过30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中医界在外感病的辨治过程中,存在着“多温少寒”的流行观念。在这种流行观念的影响下,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法则正在淡化,这就导致很多中医师在治疗外感病初期时,不再认真辨证,而是以“辛凉解表”通治。早年,肖师曾治1例感冒迁延不愈的小儿,患儿症见“鼻塞声重,发热恶寒,无汗”,是明显的风寒感冒,而此前所服某名老中医的药全是辛凉解表类。肖师改用辛温解表法,一两剂而病愈[1]。肖师由此而进一步思考“风寒感冒”之所以会被误诊为“风热感冒”,这一方面是受“多温少寒”流行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医院校教材中有关“风寒表证”和“风热表证”的相关表述以及鉴别方法也多有商榷之处。经过深入研究,肖师认为“风热表证”不应该与“风寒表证”并列,它的病机实质是肺热兼有表寒证,并由此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述,以期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医表证辨治思路”。
此外,早在1981年肖师在家乡湖北沔阳工作期间,正值出血热大流行,病人在发病之初多有明显的恶寒,肖师开始根据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的原则,见有恶寒就用解表,结果患者病情加重,很快进入低血压休克期和急性肾衰少尿期。困顿之际,他深入思考后认为,出血热即使有表证也是热入血分兼有表证,此时的表证是不需要治疗的,也是不能治疗的,应根据《伤寒论》中“表里先后缓急”治则,里证急重者先治其里,直接凉血散血为主,方用犀角地黄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转变思路后,疗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由此他认为,《伤寒论》“表里先后缓急”治则,在处理表证兼夹证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
2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
2.1 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表证基本等同于外感病的初期阶段。《伤寒论》太阳病的提纲条文“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中“恶寒”是表证的特征性表现。所以判断是否表证的关键是“恶寒”的有无,即“有一分恶寒,必有一分表证”。这一认识得到了历代医家的普遍认同。
温病学派兴起之后,一些医家认为温病初起也是表证,既然是表证也应该有“恶寒”(至少也该“微恶风寒”),因而将“恶寒”纳入温病初起的症状范畴。由此,中医表证理论及解表法走向混乱,强分风寒表证和风热表证,将银翘散、桑菊饮划分在解表剂之列,使学术界无所适从[3]。
2.2 解决的办法
肖相如教授认为,“恶寒”是表证的特征性表现,“恶寒”的形成机理是寒邪束表,卫气被遏,卫气不能发挥温分肉的功能所致。因为寒性收引、凝滞,所以只有寒邪侵袭肌表,才能束缚卫气,才能导致恶寒,才能形成表证。“恶寒”不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引起,特别是热邪不可能束缚卫气,不可能导致“恶寒”。因此,临床上是不可能有所谓的“风热表证”的[4]。事实上,温病初期并不是表证,实为“肺热证”[5]。
基于以上认识,肖相如教授将表证定义为:表证,是寒邪侵袭肌表、束缚卫气所导致的临床证候。“恶寒”是表证的特征性表现;表证的“八纲辨证”属性是属表、属寒、属实;表证可分为太阳中风和太阳伤寒两大类;表证常常有兼夹证,太阳中风的兼证有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等,太阳伤寒的兼证有葛根汤证、大小青龙汤证等;表证的治法是发汗解表;太阳中风用桂枝汤类方,太阳伤寒用麻黄汤类方。
所谓的“风热表证”、“湿温表证”、“秋燥表证”等,其实都是表证的兼夹证:“风热表证”是“热邪犯肺兼表证”,“湿温表证”是“湿热内蕴兼表证”,“秋燥表证”是“肺燥津伤兼表证”等,其治法应遵循《伤寒论》中“表里先后缓急”的原则。一般而言,表里同病以表证为主,里证不急、不重者,应先解表,或以解表为主;里证急重者,应先治里,或以治里为主。
3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的临床价值
3.1 将有效遏止“外感病滥用寒凉”的时弊
当前,中医界“外感病滥用寒凉”的问题非常严峻。宋华[6]通过临床调查发现,在北京地区,感冒初期误用“清热解毒药”和“苦寒药”的情况非常普遍,所用药物有清开灵注射液、清开灵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蓝芩口服液、板蓝根颗粒等。甚至有学者认为[7],目前临床上滥用抗病毒清热解毒药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滥用抗生素,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对整个医疗事业带来危害”。
寒凉药在外感病治疗过程中的滥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温少寒”甚至“有温无寒”的流行观念,而造成这一流行观念的核心原因则是后世温病学家将“恶寒”纳入温病初起的症状范畴。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将“恶寒”一症局限于外感寒邪的病因,是遵从中医“审症求因”的原创思维,这一认识将强有力地提示医者:只要病人有“恶寒”见症,就先要肯定其“外有寒邪束表”的病机。虽然其具体治疗还应进一步参考“里证”的情况而确立治法和用药,但至少可以警示医者,“外有寒邪束表”,寒凉药的应用就必须慎重,一旦误用就会有“寒而冷之”的危害。
3.2 将有效避免“辛温解表”在“重症温病”中的误用
这里所说的“重症温病”是指流行性出血热、肠伤寒、重症肺炎、重症肝炎、乙脑等而言。这些“重症温病”大多以里热证为主要表现,往往伴有“恶寒体痛”等见症,因此容易误用“辛温解表”治疗。数百年来,温病学家们一再强调“不可以伤寒法治温病”,正是指此而言。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认为,“重症温病”伴有“恶寒体痛”等见症,其病机是里热证兼有表寒证。此时,以里热证(甚至是营、血分证)为急、为重,以表寒证为缓、为轻,所以应该直接清里,而不能解表,特别是不能用辛温之性较强的解表药。里热得到有效清除之后,病情可能有两种转归:一是里热得清,正气得复,表邪自解;二是里热得清,表邪尚在,此时可以结合具体病情考虑用解表法。
3.3 将更加有效地指导“辛凉解表”类方剂的临床应用
关于“辛凉解表”的提法一直都有争议。“辛凉解表”实际是在“解表”的基础上加入了“清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解表”了。当代温病学家赵绍琴先生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用“辛凉清解”[8]来代替“辛凉解表”的用语,但“辛凉清解”的内涵仍然显得晦涩难明。
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则明确提出,所谓的“风热表证”其病机应为“肺热兼有表寒证”。这一观点从中医“表里”辩证的角度分析“风热表证”,对其病机实质的表达更加清晰。用这一观点来分析《方剂学》中的“辛凉解表剂”,也将更加有效地指导该类方剂的临床应用。
以银翘散为例,肖氏“中医表证辨治思路”认为,银翘散证以“口渴,咳嗽咽痛,舌尖红”等肺热证为主证,兼有“微恶风寒,无汗或有汗不畅”等表寒证。因此,其治法以银花、连翘、芦根等清肺解毒为主,兼以荆芥穗、豆豉等解表散寒为辅。如果是“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则不兼“表寒”,此时应减去荆芥穗、豆豉等解表散寒药,如吴鞠通治汤某“风温自汗”[9],用银翘散减去荆芥穗为主方;相反,如果“恶寒”较重,而“口渴,咳嗽咽痛”等症较轻,则应加重荆芥穗、豆豉等解表散寒药,减少银花、连翘、芦根等清肺解毒药。如吴鞠通治疗赵某“喉痛”[9],兼见“头痛身痛恶寒甚”,以银翘散化裁,此时,荆芥穗用五钱、豆豉用三钱、薄荷用五钱,而银花、连翘、芦根则各用三钱。
[1]肖相如.克服流弊,注重辨证[J].中医杂志,1996,37(6):377.
[2]肖相如.区别太阳阳明与正阳阳明的临床意义[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1):22.
[3]肖相如.表证并非六淫都有[J].河南中医,2009,29(8):729.
[4]肖相如.《伤寒论》表证的相关理论及其临床意义[J].河南中医,2007,27(6):3.
[5]肖相如.太阳温病提纲“不恶寒”的意义——温病初期不是表证[J].辽宁中医杂志,2004,31(8):644.
[6]宋华.对北京地区感冒误用中成药现象举例分析[J].北京中医,2007,26(9):609.
[7]赵鸣方.病毒性外感疾病从“寒”论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12):1943.
[8]赵绍琴,胡定邦,刘景源.温病纵横[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38.
[9]清·吴瑭.吴鞠通医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