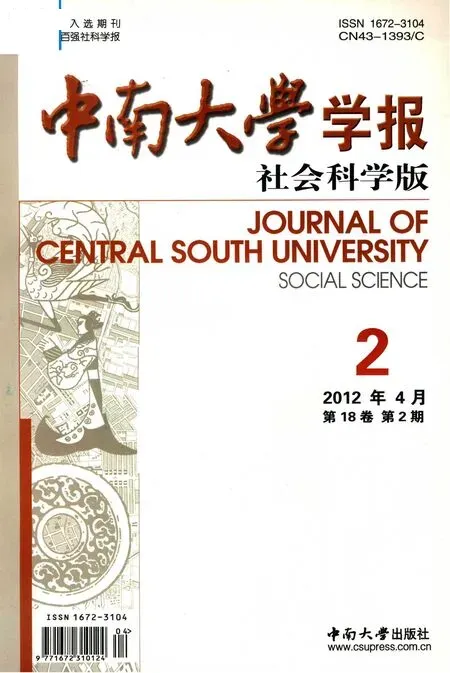论性正义
2012-01-22颜峰
颜峰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强调,我党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性正义的建立。
一、性正义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学深刻揭示了人的自然、社会与超越三重属性。从自然属性来说,“食色性也”,性欲是人类所有自然欲望中最强烈的“生存意志”,源于人的生殖冲动本能,只有性才有生命的延续,才有个体的“不朽”与人类的生生不息。性不仅生殖和繁衍了生命,也生殖和繁衍了人类精神,人类的终极精神是对生存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战胜,生命不朽的前提是精神的不朽。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终极动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性自由到性压抑再到性正义的过程,大凡性相对正义的时代,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相对较快的时代。
性正义就是恢复性的本来面貌,祛除加诸其上的过多意识形态内容,强调性的本能与天然,是相对于性压抑与性放纵而言的。性压抑的实质是与自然或造化对着干,强调性的强制、操控性。性纵欲的本质是人的动物化。由于动物依靠本能生存,其予成性决定它能“放纵”的范围极其有限,当人放纵性欲,追求性享乐,人就失去意志自由,沦为性欲奴隶,彻底偏离人性与生存轨道。自然界种类繁多的雄性动物穷尽毕生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个雌性配偶,一肆交配完毕完成生殖使命,生命就会终结。例如螳螂、深海中的琵琶鱼、生存于火山口上的火蜥蜴等,它们只能完成延续物种的使命,不能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无论是桎梏天性的性压抑,还是放任动物性的性纵欲都与人性本质格格不入。人性是动物性与超越性的综合。从动物性讲人具有局限性和必死性,从超越性上讲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人的本质就是用无限的创造性超越动物的有限性和必死性,实现不朽。而这种本质的源头是男人和女人性的极端不均衡、不匹配。女人是自然之性,创造之源,天生具有无限的性能量和远在男人之上的生命力,这从男女寿命的平均差上得到深刻反应。男人不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性能力有限,生命力相对弱于女性,必须进行后天的弥补。保障有限在无限面前发挥最大效用,这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一般来说文明起源于男人的暴力和女人的桎梏:一方面是男人凭借自己的体力优势,以暴力手段压抑和限制女性,确保自我基因得到复制与延续;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女性都是正在和潜在的母亲,在生育期间她们无法获得维持自身及后代生存的资源,因此,她们需要得到男性的帮助,于是进化出一套合作(谄媚、投其所好)与宽容(自我贬抑与同情)策略,以确保自我生命延续和基因复制,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性压抑与性纵欲不断搏弈的历史。无论是性压抑还是性纵欲都有害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为压抑一方的结果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抑制,而纵欲的前提是人的动物有限性,超越这个边界就会导致精神萎靡和崩溃,最终滑向性压抑。因此性压抑和性纵欲的本质是一致的,性正义就是祛除性压抑与性纵欲,实现性的自然状态。
二、性正义缺失及其原因
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清楚知道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因此千方百计进行弥补。但身体生命的缺失决定了精神生命的缺失,人有限的理性往往把人带入歧途,导致性正义运动不是偏离目标,就是倒置目标与方法手段,使自身异化为性欲这种动物性需求的奴隶和工具。
首先,性本质的异化。性的本质是生殖,但因为生殖使出生的婴儿遭受客观世界的威胁与侵害。“于是,因为出生,我们踏出了绝对自足的自恋状态,而察觉到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并开始发现对象。相应而生的事实是,我们无法忍受这种新的状态,所以也不时从中退缩,在睡梦中回复到无刺激、无对象的早期状态。”[1](268)婴幼儿相对其他动物而言,有一个特别漫长的无助期。他们在面对生死存亡等极端重要的事物时极度脆弱、无力,必须依靠他人照料,由他人为其提供他们无法自行获得的生存资源。因此,在婴幼儿混沌的初始意识中,为他们提供舒适、营养和安全保护的人极端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使其回归快乐无忧、不受干扰的自足状态。婴幼儿对他们怀有极度热烈的渴望,渴望回归他们,与他们融为一体。这种渴望始终伴随人的成长,并能够把在婴幼儿时期就学到的关怀和照顾回馈给那些他能为之奉献的人。这种伴随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拒斥,希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奉献就是爱。换句话说,爱起源于性的生殖冲动,但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对性的超越与升华。人自身的局限性和必死性决定了人对爱的需求是终其一生的永恒需要,相反一俟生殖功能实现,性的根本使命就完结,转向愉悦功能,以维持和增进爱欲。但现代人不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是忽视爱的极端重要性。前者造就禁欲主义“牢笼”,形成普通民众阶层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和性压抑。后者把性等同于生命力,将其重要性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形成人们对性的膜拜和上流社会的性放纵,人因此异化为自己性欲的奴隶,周而复始地在动物性生殖原点上转圈,却忽略基于精神生殖的爱欲,因此消解了爱欲内涵的超越性与创造性,使人沦为动物。千百年来人们对性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都给人类的性欲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附加了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
其次,性目标的偏离。性的终极目标是生殖后代、创造生命,不仅是肉体生命的生殖与创造,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的繁衍与再造——一种无论是自我还是人类共享一种更好生活的想象与行动。性欲目标一旦突破自我复制的局限,定位于家庭、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性欲就已经超越了动物性的生殖本能,而具有了人类精神的崇高禀性——囊括了分享、共情、奉献和创造等情感与能力在内的爱欲。但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人们常常偏离目标:一是用性活动来取代神圣的性目标,用动物式的、被本能所牵引的性欲取代人性的、超越的爱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劳动异化导致包括性异化在内的人异化:一方面,生物性竞争的本质和人的自尊要求促使人们争取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声望地位,这种地位和优势的获得在资本统治的时代是通过消费商品和服务实现的,商品成为证明自我支付能力和歧视性对比的象征和符号。换言之,商品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可以被人使用,而是借由它来证明商品占有者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个人处于优势地位。为了在这种歧视性对比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商品占有者必须摈弃并贬抑体力劳动,因为参加劳动不能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是有损体面的。更重要的是进行炫耀性消费,只有这样才能炫耀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显示轰动性优势和与众不同。最轰动的炫耀性消费是“代理消费”,于是“包二奶、三奶”“包二爷、三爷”应运而生。由此,人们对物的崇拜转化为对性欲崇拜,性放纵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其中的奥妙在于,商品的符号化和象征性使其与生活的真实联系被斩断和剥离,消费“从不消费物本身”,而是把人和人的关系转变成人和物的关系,而这种消费的最终和最“高级”形式是消费人,由此我用财富购买性,你用性购买财富,结果是整体人格分裂,人不再是由爱欲推动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仅仅异化为“性机器”,人与物的关系这时转变成物与物的消费关系。人仅剩下动物式的性冲动和消费这种冲动的冲动。既然性是可以拿来交换的商品,那么这件“性商品”的性能好坏至关重要,通常反应其性能的指标是性交时间的长短、性技巧的高低和性器官的大小。因此这些反映商品性能的指标一跃成为人追求的目标,受到人们的无限膜拜,并控制人的所有追求。现代传媒铺天盖地的病态情色广告和色情影视作品,更把性技巧对生活幸福的作用,性交时间和性器官的形制对性生活的功能推向极致。事实是,幸福感、性交时间、性行为技巧和性器官大小等“标准”都是主观、因人而异,因而是相对、非确定性的。用促销广告的夸大标准来衡量千姿百态的个体生活,必然导致人的普遍焦虑。
第三,性主体缺位。当代中国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语境下,性主体在这种混沌不清的状态下极端缺位。一方面性压抑的前现代语境导致主体性扭曲。传统社会的性行为以生育男性后代,实现男性基因的延续和扩散为目的,因此生殖主体不是个体,更不是个体中的女人,而是以男性家长为首的家族。生殖主体决定性主体,生殖偏好以男性家长的性别偏好为准则,因此性行为通常恪守男性家长制定的规范,以男性的性行为偏好为准则,无须考虑女性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感受,女性仅仅是男性性行为的客体,是否过性生活,怎样过性生活都由男性决定。因此女性并不具有主体性。而性行为本身是男女两性的共同行为,是在主体间互动基础上建构的,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缺位,事实上解构了男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男女两性都成为家族的生育工具。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爱情诗总是诗人与妓女情感生活的记录,而写给妻子的只有悼亡诗的原因。因为封建社会,只有妓女才能在一段感情中获得精神独立和人格自由,因此才能成为诗人眼中的审美对象,才能在同样脱离家族规约成为主体性人的诗人那里产生精神上的自由联想和情感上的审美感受。而妻子仅仅是诗人家庭的特殊“财产”,只有当这个特殊占有物消失不被掌控和占有时,才会在诗人眼里形成虚幻的独立性,从而被诗人歌颂。
另一方面性放纵的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导演了一幕幕主体性萎缩的悲剧。公民社会建设并不能自动确认男女两性的主体际性。原因之一是,传统男性意识的建构基础是男性作为唯一家庭经济支柱的事实,男性自尊是建立在职业氛围和职业性人际交往中的。现代社会同等的教育以及相对平等的男女两性权利,一方面使女性的自主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男性丧失传统的职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其自尊严重受挫,导致性自主性大大降低。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男性气质丧失。原因之二是,控制性生育行为导致控制性性行为,再加上爱滋病等疾病流行,人们通常不愿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进行性行为,而医疗设备及药物的介入给男女两性带来的心理影响是显著的:把一种自然的行为演变成一种机械的程式化运作,使行动的双方都能切切实实感到外在机械性力量的控制,使性行为本然的自然自由的主体性感受大打折扣。原因之三是,一方面女人虽然获得社会生产劳动参与权,但却并没有因此获得与男人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权利,家务劳动依然被认为是低贱、没有价值的。而由性生活而来的生育行为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如“生”(生育孩子)还是“升”(职业升迁)的矛盾,身体遭受疼痛、心灵遭受痛苦还是让身体和心灵都获得安宁的冲突等,使女性,尤其是高素质女性往往选择逃避婚姻、逃避性,使本来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中国社会“剩女”(A女)和“剩男”(D男)现象都异乎寻常地严重,不仅有“一女嫁三兄弟”的怪事,还有大量涌入的外籍新娘,加剧人口负担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竞争压力的加剧使男性的性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男性在义务感和传统性文化的钳制下,被动性与受控制感前所未有地增强,性活动自主性的丧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更加严重。
第四,性情感缺失。情感是基因发出的声音,与人的生存状态有直接、密切的联系。情感有积极的情感和消极的情感,积极情感如快乐,能促进人的行动;消极情感如恐惧、愤怒、悲哀,能使人迅速避开或抵抗危险,因此,无论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极大价值,其中积极情感更关注人的超越价值,消极情感更关注人的生存价值。与性活动联系密切的主要是快乐感——需要得到满足后的情感体验,恐惧感——面对危机状况企图逃避而又感到无能为力的状况。人趋乐避苦的本性使人们在性活动中追求快感,逃避疼痛感,而现代生殖技术和医疗器械及药物的大面积推广使用极大满足了人们这一需求,再加上由医生、医院、制造商、销售商和广告商所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和资本链的介入,一是使生殖过程的剖腹产率大大上升,在我国已超过50%的比例,二是“无痛人流”遍地开花,三是孩子的父亲成为生殖这一性活动后果的局外人。上述方面共同导致性情感缺位:首先剖腹产一方面造成母性这一最重要的性情感缺失,另一方面造成婴儿性意识错位,因为自然分娩的过程不仅是母子共同为新生命的诞生奋斗挣扎,由此建立婴儿最初生命意识,增进母亲意识的过程,还是重要的性情感建立的过程,伴随生产的一个重要生物因素是不同量的性激素分泌,有实验显示,生产过程中人为干预注射更大剂量的雄性激素,结果导致生产下来的女婴表现为男性情感。此外研究显示,剖腹产造成的新生儿发生感统系统失调、多动症的可能性远高于自然分娩的婴儿,而感情系统就是人情感形成的生物基础。此外父亲角色的边缘化,不仅是使男人与孩子的亲情联系降低,还使男人很难与安全保护与怜悯同情这类与男性气质关系更密切的情感建立联系,这很可能是现代男性缺少血性麻木不仁的重要原因。其次,所有的手术都对人的整体性产生破坏,生殖手术也不例外,除了手术造成大面积创伤和高风险外,女性恢复慢、高并发抑郁症、难以迅速建立亲子关系,这既不利于母性情感的建立,也不利于孩子包括性情感在内的人类情感的建立,因为突然被“拿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婴儿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她)的不适是可想而知的。器械化、规格化的医院育儿模式和后天教育模式很可能是导致现代人情感淡漠疏离,缺乏激情和个性的始作俑之一。“无痛人流”手术在“无痛”意象下隐喻的性放纵,造成性情感的特殊障碍:女人因为“无痛”放任性欲泛滥,男人因为“无痛”而“去罪化”,丧失责任意识。整个医疗系统联姻生产与销售企业为共同的赢利目的大肆宣扬这种使人沦陷为自身性欲奴隶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消解人类基于自主的性情感。
第五,性意志力衰减。意志是认识、情感与行动的综合系统,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个体的人只能作为男人或女人存在,男人和女人在各自的性别框架下从事生产实践和生殖实践。男女两性的结合生育出新个体,实现人的延续,男女两性的共同生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是基于生理性别不断进步的历史,是男性意识与女性精神不断共同发育的结果,任何一种不平衡发展都会导致人类精神的沦陷。男性精神主要是一种冒险、占有的精神,他的缺失导致社会停滞、缺乏活力;女性精神主要是一种包容、奉献的精神,她的缺失导致社会冲突、缺乏和谐。
男性精神片面发展是性意志力衰减的主观原因。以冒险和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男性精神结合资本的膨胀性本质生出“当下性”和感觉主义怪胎。“当下性”使人不考虑长远和根本,只考虑眼前和即时,其结果是导致人的漂泊感和不确定性,人仅仅是被命运偶然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子”,无依无靠孤独荒谬,只能在自我的寻找和确定中构建自己的命运,人生就是在这种偶然性中自己去制造戏剧性高潮,而唯一能创造这种高潮,带来激情体验的活动是由性行为带来的,因此纵欲不仅具有我还活着的象征意义,还上升为生命存在的本体意义。问题是当人们沉溺在占有、消费肉体的性放纵中时,人本质具有的创造性和奉献精神荡然无存,人愈益在自己制造的虚假的戏剧性高潮中神情黯淡,精神萎靡,情感畏惧,行为退缩,在“性自由”的表象下掩盖着深深地性无能与性压抑。
科学技术发展,高度发达的人类物质文明是性意志力衰减的客观原因。科学技术发展一是模糊了人的性别界限。性别身份是个体形成相应责任意识和正义行为的前提。以信息生产、流动和运用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技术消解了基于生理性别的劳动分工界限,使传统男性主导的领域活跃着大量女性,而传统女性主导的领域不乏男性身影,这种劳动分工的模糊性某种程度上导致性别角色模糊,造成一定程度的性行为动机降低。二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字的阅读人能控制阅读速度,边读、边想,是一种深度、整体阅读方式,这种深思熟虑的阅读方式,训练并培养了人的思维力和专注能力。电视图像的迅速转换性,网络的链接性把人控制在片段的、割裂的和肤浅的世界,人既失去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的耐心,也丧失对特定对象持续关注的能力,变得浮躁易变,这既是现代人越来越不信任持久专一的两性生活的深层原因,也是人们无法专注进入性爱情境,导致性爱不成功的深层原因。三是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多样性、强刺激性,不仅使新奇变化取代了性行为千篇一律给人带来的厌倦感,而且那种无拘无束的彻底放松也解除了在进行性活动中感受的意识形态压力。今天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沉溺在由科学技术营造的娱乐世界,日复一日地疏离伴侣,冷落亲人,放逐自我。
三、性正义的实现路径
性正义的根本目标是回归人性本质,促进人的自然性与创造性的高度统一,给包括性关系在内由人创造的一切可能生存样式以应有的尊重。
首先,女性解放是性正义的前提。只有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对社会劳动的参与,才能造就她们人格的自由。只有自由人格才能为生活提供无数可能,而基于人格自由的性正义才能为性关系奠定多样性基础,使性关系不再依附于各种社会关系,愈益脱离手段性趋近目的性,性不仅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手段,甚至不是生育的唯一手段(试管婴儿、代孕母亲)。使两性关系的建立不再以物质和人身的双重占有为基础,实现男女两性的主体际性,真正实现以审美为依归,以爱欲为联结纽带的性正义、人的解放。
女性解放的关键是建设男女平等的制度环境。以往一切性别图式不是建立在对立观念上的,就是建立在等同观念上。前者导致男女两性的敌视、对立和冲突,最直接的后果是男性在长达几千年历史中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也导致男性的压抑和扭曲;后者抹杀两性基于生理不同的差异,因而在包括家庭制度设计上以男性需求为样本,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从突破传统性别图式的角度入手,形成普遍的社会性别回归意识,消除性别等同观和对立观,建立以男女两性生理差别为基础的平等体制,追求男女根据自身特点及先天禀赋而获得平等机会以及和谐发展的爱欲护疗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在当前最重要的是创造机会平等,使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经济地位。例如家庭共有财产的制度保障,以及建立在差异原则上的机会平等。实现人的自主独立性,才能实现男女两性的主体际性。
其次,加强男女两性沟通与理解是性正义的基础。解构父权、夫权专制话语,建构两性和谐的现代性别语境,其关键是改造以占有和控制为特征的传统夫妻、父母子女关系,通过具有社会实践本体论意识的唤起,造就有见识、有抉择能力和有勇气摆脱各种物化趋势的独立个体,使个体体认到只有两性共同发展和谐相处,才能使自身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从营造两性间的民主关系入手,倡导互相尊重、强化沟通、开放包容的民主精神。因为只有当男人、女人不再把女人、男人视为占有物,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个体才有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具体路径是,消除操纵:一是致力消除消费文化对性文化的操纵,倡导“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活,在消费上保持对消费品广告的高度警醒,化解其针对人的意识和无意识所实施的操纵与调节。消除以“厌女情节”和“仇男心理”为核心的男女两性对立观,为男女两性的有效沟通奠定基础。二是致力于消除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产品对人的精神控制,尽力消除医疗器械对人的精神影响,加强亲子、两性的交流与沟通,提倡面对面直接交流优先于电话、网络交流,体育活动优先于人-机游戏活动,文字媒介优先于图像媒介,网络媒介优先于电视媒介,尽可能提高自然生产率、降低医疗器械使用率,其目的是强化意志力培养,唤醒人的主体性意识,追求人性自由本质,即升华的性欲——爱欲活动的自由自觉。三是致力于消除夫权和父权话语机制下的家庭成员间的操纵,形成平等协商、他人建议、自我决策的行动机制,实现男女两性共同成长。
第三,加强以爱欲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性正义的核心。相对于占有,爱欲强调互相融合;相对于索取,爱欲强调奉献,相对于消费,爱欲强调创造;相对于及时行乐,爱欲强调持久的和谐幸福。因此树立爱欲的人本质观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前提,正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人的解放,爱欲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
具体路径一是大力宣传谁也离不开谁的观念。爱欲是一个分享——需要——创造的开放系统。爱欲中的男女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奉献身体、时间和理想,分享信念、激情和想象,追求共同价值需求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失业居家,从事家务劳动,帮助妻子或女伴实现他们共同理想追求的男人也一样是被需要,有价值和受人尊敬的。因为家务劳动同样具有劳动本质上的神圣性。
二是大力开展科学的性健康观教育。以往性健康教育的实质是母婴保健教育,其立足点是为生育一个健康婴儿展开的生殖教育,忽视男性、女性健康教育,欠缺男童、女童,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教育。忽视性健康教育的结果是“迷信”主宰人们的性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需要受到保护和奉养的弱势性别,男性是必须为女性提供保护和奉养的强势性别。而大量科学研究成果证明,男性除了在爆发力方面较女性占优势外,在感受性(避免危险)、耐受性(持久力)和判断力(做出正确选择并展开行动)等方面不如女性,换句话说,从生命力角度看男性不如女性,因此在关注女性健康的同时,应更多关注男性健康。男童、女童和老年男性、女性教育缺失的结果是谬误统治人的精神。教育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也是社会控制的途径与手段。男权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因此男权性健康话语的典型特征是赋予男性丰富绝对的性话语权。为此一方面是保持男性对性知识的占有,另一方面是保证女性对性知识的无知,依照男性制定的标准“好女人”=“纯洁的女人”=无知的女人模塑自我人格,直至全社会都在高喊男女平等的今日,女性虽然获得了性权利平等的意识,但依然把与性相关的话题作为禁忌。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导致现代社会的普遍失控,因为利益实现以赋权为基础,权力获得以责任担当为前提,责、权、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担当责任的内核是具有责任能力。因此,男性获得绝对性话语权的同时,要独自承担性责任、履行性义务,显然不具有这种独自担当的能力,结果造成两性间的对立和冲突加剧,人们普遍感到生活无意义、生命无价值,生存意志沦陷。科学的性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强调女性具有和男性同等的性权利,更强调女性要同男性共同担当性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仅片面强调女性权利,而不谈女性应履行的责任、义务,个人内心的和谐,男女两性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只能是空话。
[1]玛莎•纳思邦.逃避人性[M].台湾: 商周出版社, 2007.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