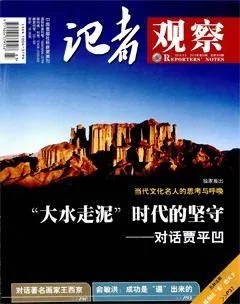“大水走泥”时代的坚守
2012-01-01吉冬文
记者观察 2012年3期
贾平凹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被誉为“鬼才”。他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具有叛逆性、富有创造精神、有着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前不久,贾平凹历时4年创作的60万字新作《古炉》正式出版。面对世事浮华,他始终坚守写作,他所思所写的,仍是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人”。
近年来,他以每三至四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陆续完成了《怀念狼》《秦腔》《高兴》等作品,不但每部作品都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秦腔》还于2008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正是这部作品把贾平凹推上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在《秦腔》的授奖辞中这样写道一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面对纷至沓来的祝福,贾平凹的获奖感言既独特又发自肺腑一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能授予我,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我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也是我最费心血的一部书。当年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立一块纪念的碑子。现在,《秦腔》受到肯定,我为我欣慰,也为故乡欣慰。感谢文学之神的光顾!感谢评委会的厚爱!
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遇到了桥,是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
记者:文学创作要有精品意识,这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您每隔三四年就有一部作品问世,并在不断求变、求新、求精品。请谈—下您如何看待作家的精品意识。
贾平凹:作家的精品意识,说到底还是要出好作品。强调要有精品,有精品就代表了一切。这就像我们现在说中国就想起长城,说古时候的小说就想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
文艺精品创作要有占领制高点的观念,起码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普及,二是抓重点作品。比如支持文艺创作的资金,只能用来做普及工作。精品不能事先来确定,谁也不知道创作的一定会是精品,只能有成果以后形成一种效应,因此,创作精品不能急功近利。
现在,我们需要写伦理,写出人情之美;需要关注国家、民族、人生、命运。这方面我们的作家还写得不够好,不够丰满。但是,我们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或许—时完不成,但要时刻心向往之,将眼光放大到宇宙,追问人性的、精神的东西。
我认为,大家大作可以起到引导和提供国家综合文化素质的作用,益于培养公众道德情操、净化人格修养、提高文化知识、提升阅读水准,这些就是作家的时代使命。
记者:您前面谈到,写作要有精品意识,怎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最关键的是抓人,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大时代决定的,要产生大的作品,就一定要关注社会和现实。现在文坛上一直关注现实、研究现实的作品还不太多。没有大作品就是因为理想不足、境界不足。我认为,史诗是一个时代的境遇,也是作家本人的境遇,作家深入生活后,在生活中有体味,这体味又建立在崇高的向往中,个体生活的感受应该和社会大的境遇一致。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精神是丰富甚至混沌的,这需要我们的目光必须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写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坚硬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心在地狱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更需要活在精神中。精神永远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照耀着我们,人类才生生不息。
所以,作家要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人的理想要大,成功的作家的思想要想大问题,要有伟大的胸襟。此外,还要在专业上丰富自己,要丰富自己的笔墨。这是作家修养问题。这两点正是目前我们的作家缺乏的东西,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好的作品就可能问世。
记者:在现今中国文坛,许多和您同时代的作家,在达到一定创作高度后都不再专注于写作。但您却是一个例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并不断寻求突破,这种现象非常难能可贵,您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贾平凹: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水走泥”的年代,这个时代是剧变的,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破坏。这样的年代,混沌而伟大,它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
我认为,作家是社会的观察者,永远要观察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和身影,永远要叙述这个社会的伦理和生活,更要真实地面对现实和自己的内心,尽一个从事作家职业的中国人在这个大时代里的责任和活着的意义。我是一个普通作家,越发要努力写作,不敢懈怠和虚妄。
更何况,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耐性强,适合马拉松;有的擅长冲刺,适合百米。作家一定要有冲动的劲头,保持自己的写作状态,有鲜活的生活积累,在艺术上一直有突破,同时保持好奇心和不服输的劲头,强迫自己时常有变化。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他说自己发现了长寿的秘诀,就是永远觉得有干不完的事情。这个农民从60岁开始每年订计划,订到了120岁,连120岁那年1月、2月干什么都有详细计划。写作也一样,只要有宏大的目标放在那儿,人的写作寿命就会延长。
记者:您的作品一部一部接连问世,普遍得到社会认可。您心目中的好作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个大致的标准?
贾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样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出来,不会写小说的人读了产生出他也能写的念头,而会写小说的人读了,又产生这样的小说他写不了的念头,那么这个作品就好了。
记者:您把自己的创作分为几个阶段?您觉得从哪部作品开始,对自己的写作风格比较自信了?
贾平凹:我在创作中一直追求变化。从30岁写完《浮躁》之后,便开始不满意那种写作方法,觉得那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常用的写作方法。后来写《废都》,也总想着变化,但这些变化都不是剧变,而是慢慢地变。当时经常觉得有一些想法想去实施,但各方面的能力还达不到,于是一直在尝试。基本上是从《废都》开始,一直在做这种实验,到了《秦腔》,再到《古炉》。但还是任何东西写完以后都觉得应该写得更好。
记者:您的《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秦腔》等作品,无一不是深入农村后完成的。《秦腔》获茅盾文学奖,是对您深入生活拒绝浮躁的肯定,请谈谈《秦腔》的写作。
贾平凹:茅盾文学奖增加了我写作的自信和力量,但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获奖,文学的路还长着呢。我写《秦腔》时,父亲去世了,母亲还在世。我母亲没文化,但她给我讲了很多家族和村子里的事情,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的素材。
我对自己的家乡和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30多年,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农民。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所以要用忧郁的目光观察农村,体味农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碑。
我的《秦腔》中有家乡生活的点点滴滴,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家族印迹。这部书写的是我的老家,我家族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和生命有关的写作。
近年我写了不少农村题材的作品,《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这些作品中有我对陕南商州家乡的真挚情感。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一个碑,写作是我生命的另—种形态。在《秦腔》之前,我的《浮躁》《高老庄》《怀念狼》都入围过茅盾文学奖但没有评上。《秦腔》获奖对于我当然是好事,但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奖,创作之路遥远,它只是走渴了,遇到了一眼山泉,过河时遇到了桥,你还得继续往前走。
《秦腔》我写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四易其稿,除了第四次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修改,其余三次都是重新展开写的。我一直用笔写作,光是抄写这三遍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就是一件体力活。
记者:谈到您和您的作品,不能不提到《废都》。在沉寂了17年后,您的《废都》与《浮躁》《秦腔》一起打包为“贾平凹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能谈谈《废都》吗?
贾平凹:《废都》基本是上世纪末的那个时候,写知识分子一些心境的,写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当时写出来,一般人不愿意承认那个东西,谁也不承认,就包括知识分子,他也不承认,是我我也不承认,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不愿意承认那些东西。实际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冷静下来,就是那么回事情。大家当时都对性的描写有争议,关注那方面的事情,引起了争论。当时写的还是有些早了,但是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感知,对人生的感知,我觉得一定是要具有预见性、前瞻性的那些东西。
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很爱写作,那时见到什么都有感觉,见到什么都想写。现在50多岁,回过头来一看,再遇到年轻时遇到的那些事情,也许还有冲动,但一想也没什么意思,就不写了。我一生一直在受争议,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受批评。特别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是最没有顾忌的,关键是有时写作我就不管那些东西了,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废都》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
《废都》现在能再版,首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文坛关系的回暖。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经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学本身。
记者:前不久,您的又一部长篇《古炉》出版,能谈一谈这部小说的写作吗?
贾平凹:写长篇是慢活,既要保持写作状态又要把握住节奏。我杂事很多,而在写《古炉》过程中除过一些必须参与的会议、活动和家事外,我尽量拒绝一些可去可不去的场合,拒绝一些可干可不干的事。这些年里,六七次出国机会我都谢绝了,一些必须去的大活动和会议都带着稿子,晚上书写。在西安的日子,每早8点前必须到书房里,写到中午11点,11点到12点接待来访人,中午睡一觉,起来写到下午5点,5点到6点又待客,基本生活规律就是这样。有时写顺了就特别愉快。写不顺有各种原因,有时就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有时故事不知道怎么延续。写的时候要没有感觉,作品肯定就没意思。要是哪天写得特别有味道,就特来劲。灵感来了嘛,就很愉快,一般一天能改好5000字,特别顺当就能写到8000字。有时就两三千字,太忙就放下。3年左右短的文章都没有写。
每个人创作的习惯不—样,年轻时写散文、写中篇,我一般写一遍再抄写一遍就完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然后会在—个笔记本上打草稿,然后再改一遍,然后再生稿子背面写一遍,然后再定稿,《古炉》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写出来的,前后加起来写了两百多万字。这部书用去了三百多支签名笔。但写完《古炉》,并没有被掏空的感觉,还有别的东西等着写呀,作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记者:《古炉》的写作,似乎延续了《秦腔》的写法,重整体,重细节,以实写虚,混沌而来,苍茫而去,在当今文坛上风格别树一帜,这种写法是怎么形成的?
贾平凹:这种写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吧。我一直写的是当代生活,行文上又想尽力有中国气派,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其实很难,如国画很难表现现代生活一样。这需要作者必须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细节,讲究节奏,把味道写足。
散文可以这样写,但六七十万字的长篇写下来气息绵长就不容易做到。这套写法从《废都》之后就开始了,但那时仅是试验,过渡到《高老庄》,再过渡到《秦腔》《高兴》,直到《古炉》。
人常说“文如其人”,其实只有写到一定程度了才可能文如其人,又常说“得心应手”,即便心里想到的未必能应了手。《古炉》在构思时是艰难的,写作时常有一种快感。年轻时写东西,有激情,锐力外向一些,年龄大了,就可能沉淀了些,想写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了个人生命体会的东西,就不讲究技法、起承转合,只想着家常话,只想着朴素了。古人讲的几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琢磨琢磨,真是这样,可这样也真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