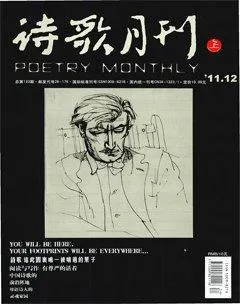当我失去听
2011-12-31明迪
诗歌月刊 2011年12期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不需要翻译,阅读的时候,汉语一下子冲出来,在英文的字里行间跳动。但当我旅行归来后记录下这些汉语碎片时,突然发现它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流失了原有的色泽和节奏。我试图找回最初的感觉,无奈所剩不多。我怀疑那些乐感都流失在火车轮子的滚动和飞机翅膀的滑翔中了,抑或是一开始那种感觉就伴着旅行节奏而来,如今坐在平稳的家中已无法再体验。只有重读。重读时有一种东西扑面而来,只是我已无法转换在我的母语中与同胞分享,虽然我自己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面对伊利亚,你会不相信他有33岁,一张娃娃睑天真的眼睛。我忍不住问道:
“你是做什么的?”他以非常东方的方式回答:“瞎混。”“在哪里混?”“圣地亚哥。”“那你认识陈美玲?”“我和她一起教书。”
“哦,你教写作啊!”
这是在南欧一个诗歌节的电脑室里。突然他在我刚打印出来的《瓷月亮China Moon》背面写了一句话:
“你先用中文写还是先用英文写的?”他低头写字时我看见他耳中的助听器,一阵心痛。我不知道他耳聋!这大概是他过去常用的方式——书面交谈。我不想谈自己,我对他有很多问题,比如敖德萨是什么样子?他的童年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写诗?对“难民”身份有什么感受?怎样理解“流亡”?对生活本身有什么感受?但这些问题需要问吗,读他的诗就够了,我们了解一个诗人不就是通过阅读吗,比这更多的问题都能在诗中找到答案。
然而我找到的不是答案(我不需要答案),而是一种欣喜,愉悦,感动。
一个多月前,我突然得了“厌食症”,读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厌倦了悲痛的诗,极想看到新鲜的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德国诗人杨-瓦格纳、乌克兰美籍诗人卡明斯基等人,他们的诗正是我渴望读到的那一类。我不由自主地翻译,在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这已成了一种习惯,见到喜欢的诗就想“分享”。他们不是国际大牌诗人,从未被译成汉语,但他们在我饥渴的时候带来雨露,这就足够了。
伊利亚‘卡明斯基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雨露,还有泪水。但不是悲痛的泪水。我说过我已厌倦了悲哀的诗。我盼望读到的正是这样悲而不哀、浓而不重的轻盈线条,如雨后的燕子在树间穿行。
斯特鲁加大桥上,我们坐成一长排,面对河水,小船,风,热情的读者。这是马其顿诗歌节标志性的朗诵地点,我和瓦格纳若无其事地聊天,无视这种时刻的严肃性。而当卡明斯基朗诵时,我突然震惊,那是一种嘶喊,第一声就喊出我的眼泪。一个无法正常听到声音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只有喊叫,否则别人会同他自己一样听不见。我被他的喊叫震撼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伊利亚4岁时因医生误诊而失聪。在他的诗中,“医生”同“审判者”一起出现,但没有怨恨的字眼,他甚至可以爱上医生的孙女,他接受命运如同我们每天接受阳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他第一次看见关于他母亲在集中营的照片和记录,有些震惊,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仇恨”。我知道在后屠杀年代很多犹太青年都不谈大屠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连自己母亲的身世都不知道,于是忍不住又问,他说他父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他四岁后就再也听不见了。他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戴过助听器,但他的童年是快乐的,他读童话故事,读巴别尔的小说,读布罗茨基的诗,他父亲认识很多诗人,包括布罗茨基,虽然他自己从未见过布罗茨基。来美国时他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罗切斯特公立学校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补习班人数已满,于是他上正常班,学的第一首诗是史蒂文森的“十三种看黑鸟的方式”,他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他继续用俄语写诗。第二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无法用母语表达内心的感受,因为写诗对于他一直是一件隐私,他不想让家人和周围的人知道他写些什么,于是用英语写诗,一写就停不下来,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新罕普西尔州著名的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馆作家。他刚出道时很多人称他为神童、小布罗茨基,他说俄罗斯人对年龄有不同标准,他的中学同学16岁就可以结婚生孩子,某某诗人死于22岁,某某诗人死于26岁。《费城问询者报》称他的英语诗歌使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感到羞愧。他仍然用俄语写诗,但他不写“双语诗”,而是分开写。他也翻译,翻译经典俄语名诗或者同时代俄语诗人的作品。
我也有个秘密:失忆症。那天晚上在电脑室我和瓦格纳等人一起读卡明斯基送的诗集,翻开第一页我就发现眼熟,“我读过他的诗”,我非常肯定地说。但后来我搜遍记忆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读过的。我认识的人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提醒我以前什么时候读过他的诗,后来我确定以前没有读过,但一拿起书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在欧洲闲荡一个月的时候,从奥斯威辛到贝多芬故居,我没有联想到他。回到加州突然想起,于是一天之内一口气翻译了12首,“没有版权麻烦吧?”我问他。“没有,想译多少都可以!”我真的想一口气把这本诗集垒部翻译出来。选出的12首诗是最简单的,最精彩的还没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纳塔丽娅。他的下一部诗集是《聋子共和国》,童话诗,嘿,“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聋子”。
我写诗是为了抵抗失忆症,有时候写过几天后就不记得了。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我爱的人面前而想不起他的名字。
卡明斯基为什么写诗呢?“因为停不下来。”他想不起来为什么或者怎样开始写诗的,只知道现在停不下来。用英语写作是个偶然,“是一种无理性的美丽的自由”。
我被他的诗所吸引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写一些回忆故乡和童年的诗,但我发现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母亲大串联从新疆带回的葡萄干,红卫兵占领了大礼堂,窗口里伸出的枪支,教学楼全部变为城堡,下放,回城,少年文化宫的演出,小提琴,芭蕾舞鞋,英语词典,母亲从江汉路外文书店买回的乔木斯基转换生成语法。
敖德萨是一个海港城市,有鸽子和乌鸦,有剧院和音乐厅,
每一个人都喜欢跳舞,有西红柿和烤鱼。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父亲维克特有一段童年传奇。他父亲(伊利亚的爷爷)被斯大林镇压枪毙了,他母亲(伊利亚的奶奶)被判刑2睥,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菅(古拉格)挤牛奶,维克特被送到孤儿院,维克特的奶奶从一列一列火车顶上跳过,穿过大半个俄国,把一岁的维克特从孤儿院里“偷”了出来。维克特后来成为成功的商人,很富有,乌克兰经济萧条后却破产,又遇到“排犹”,于是把垒家弄到美国。
对于诗人卡明斯基来说,流亡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完全同意我列举的布罗茨基等人对“流亡作家”的嘲笑,他说他最看不起“自我怜悯”,我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因1989而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当年做了件多么可笑的事情,20年来我一边嘲笑一边哭泣,矛盾至极,我有两个祖国等于一个也没有,我有两个语言最终都失去了,到头来“流亡”于自我。他说流亡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以使自己回头看过去,以一个新的距离来审视自己。他说他是“苏联犹太人”,但既不认同苏联,也不信犹太教,“犹太”对他来说是一种文化,包括巴别尔、卡夫卡、辛格尔等等在内的文化,他的文学传统包罗万象,有普希金,也有贺拉斯、维吉尔、莎士比亚、有雪莱,拜伦,也有狄金森、惠特曼,当然有荷马、但丁,俄罗斯白银诗人更不用提了,甚至连东方诗人也包括在内,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派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界文化”的追求。他很反感被标为“俄国诗人”或“移民诗人”,甚至连“美国诗人”都不喜欢,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我说在汉语里这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说某某某是俄语诗人,德语诗人,3167dec280c1bc7e6671d24780c3388e汉语诗人,只提语言,不提国籍。他说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载体,他写诗不是用语言,而是借用语言。我想起大约两个月前我对诗人冷霜说过同样的话,冷霜立刻纠正我,
“语言不是工具”,我想这个话题太大,一时半会争论不完。卡明斯基曾经在一个访谈里说,诗歌超越一切语言。但如何超越,是我正在琢磨的问题。
第一首《作者的祷告》是卡明斯基的诗歌宣言,“我必须赞美/最黑暗的日子”。他赞美失去听力,赞美失去祖国,赞美睡眠,赞美活着,“谁知道自己明天能否醒来?”他不知道失去听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有听力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活着是多么快乐。他不同于贝多芬,他四岁就失去了听力,他用一种他没有听过的语言写作,写得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说美国人都怎么了,为什么只写愤怒的诗,悲哀的诗,生活这么美好,他要“见证”活着的快乐,要随着内心的音乐而舞蹈,而且要瞎跳,要调皮捣蛋。
为什么他喜欢重复标题,因为他跳的是双人舞,与另一个自己。他将诗与散文穿插在一起,让诗与散文对话。他不用“散文诗”这个词,散文就是散文,他偏要写散文,他把街头用语,甚至菜谱都写进诗集里,气死“正统”诗人。但他是少有的年纪轻轻就享受最大荣誉的诗人。而你如果见到他又会觉得他极其普通,一个大孩子而已,充满阳光的笑容。
这个大孩子有着比常人更孤独的童年,但孤独在他记忆里也成了一种美好。“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声音,多么神奇的东西,鸣响四年之后戛然而止,世界从此只有黑白之分,“乌鸦和鸽子”。但不久之后,乌鸦和鸽子飞出一些彩色线条。上个月在贝多芬故居的多媒体音乐室,看见交晌乐作品被影像呈现出来,一阵惊喜。回想那些跳动的光线,我突然明白卡明斯基在失去听力之后是如何“看见”声音的。千万不要以为一个聋子的诗不会有乐感,恰恰相反,他的诗每一句都如同直接从琴上流出,而翻译中流失最多的却又正是诗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