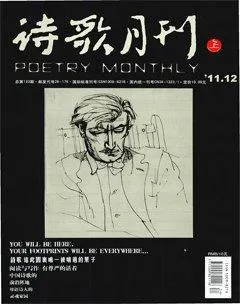诗与真
2011-12-31丁修侠
诗歌月刊 2011年12期
在古代思想家里面,对中国艺术与诗歌影响最巨者大概非庄子莫属了。庄子谬悠荒唐、瑰玮恣纵的文风,及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出世之姿,让历代文人倾倒。举凡历史上的大艺术家、大诗人,包括陶渊明、李白、王维等,哪个不是庄子的私淑弟子呢?但悖论的是,庄子又说过很多否定艺术和诗歌的话:“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庄子把“五声”“五色”“文章”“文采”等这些具象的、声音的、语言的艺术,统统视为违背本然之真的人为之物,并认为这些人为之物会蒙蔽人的“聪“明”。当然,庄子所说的“聪“明”不是一般所理解的理知能力,而恰恰是在排除了理知之后才能够获得的“朝彻”与“见独”。
无独有偶,庄子的同时代人、西方哲学与诗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柏拉图,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艺术与诗歌。他通过其著名的“床喻”提出,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而艺术和诗歌又是对感性世界的摹仿,因此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他言词激烈地攻击古希腊人素所崇敬的诗歌之王荷马,认为荷马既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也不能教给人以有益的生活方式,还要把诗人们赶出自己的理想国,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而且“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会让人的心灵受到激情的控制,动摇人的阳刚之气,滋养出不健康的哀怜癖,让人表现得像个小孩子,乃至像个女人。总之,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家和诗人没有理性,不掌握真正的知识和真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只是“神灵附体”的产物,而非出于他们自己的创造。然而,正是同一个柏拉图,年轻时曾经写下很多诗篇,并梦想在雅典戏剧比赛中折桂。他的摇曳多姿的对话体著作,灌注着诗的气韵,无疑受益于荷马史诗及其后的悲喜剧,同时也成为后世文学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何以两个对诗歌满怀敌意的人,竟成为后世诗歌与诗学的最重要源头?这真是一个千古之谜。在哲学和诗学史上,人们对这个谜已做出了深入探讨,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论争。笔者不想涉入这一论争,而是想由此探讨一个相关问题,即诗与真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巨人否定诗歌的理由几乎是相同的,即后者缺少或违背了一个在他们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真。那么,何谓真?
在庄子这里,真是具有本体意义的一个词。“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所谓“天”即是道,所以他有时又把道称之为“真宰”“真君”,“真”即是道的性质,它内化于人与万物之中,是人与物存在的根据。万物有了这种道之“真”性,就能够自自然然地存在、生息,各得其所,各安其命,逍遥自在,不假外求。强行改变物之本然状态即是“伪”,即是悖于道,这样不但使物失去了自然的光华和灵性,也使其失去了最可宝贵的自由。而他所认可的是“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匆失,是谓反其真。”。但是人不同于物,总是有着过多的欲望和心知,所谓“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这些人心中的欲望和理智驱使人介入外物,从而蒙蔽本性之“真”,为欲所害,为物所累,并且“灾及草木,祸及昆虫”。
出于这种理念,庄子曾在《大宗师》里反复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真人”形象:无嗜无欲,无忧无虑,循道而行,一片天机自然,谨守其本心而不失,随物宛转而不牵于物。而在《刻意》里篇,对“真人”的这种与天合一的理想生命状态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概括:
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这里的“纯素”指的是心灵的纯素,何以谓纯素?指的是心灵不与物相交,排除一切好恶忧乐,由此获得的一种“超分别相的直观、智慧”。这种直观、智慧,不是一般的理智,而是几于“神”的一种心灵活动,它自由无障,能够“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这“神”正好与“真”相表里: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悲者虽哭不哀,强怒者虽严不成,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不严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是存在的本质,神则是真的发用流行,它是无形的,却是形的真正主宰者。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一群小猪围着一只已经死去的母猪在吃奶,突然它们惊觉起来,于是丢下母猪四散逃走。为什么小猪逃走了?“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德充符》。)也就是说,外在客观形态不是真,内在的决定性的本质才是真。
由此,庄子建构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存在结构,那超越于现象界、高居于流俗之上的真,才是真正的价值源泉。至于仅存于现象界的一切器物、事实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技能,皆属无意义。艺术与诗歌,作为人类的一种技能,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在柏拉图看来,真又是什么?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也即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这两个世界又可以分别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世界的第一部分是影像,第二部分是影像的原本,即具体事物,这“两部分有不同的真实程度,摹本之于原本,正如意见领域之于知识的领域”。可知世界的第一部分是数理理念,即几何、数学及相近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理念以可见世界中的实物为影像,其真实性高于可见的实物;第二部分是伦理理念,是“逻格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而达到的那种知识”,包括美、正义、勇敢等,最高的理念是善。犹如可见的事物世界由太阳所主宰,可知的理念世界由“善”的理念所统治。同时,善的理念又是两个世界的最高主宰与根本依据,“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是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也就是说,是最高的、绝对的真。与上述两大世界四个部分相适应,人的灵魂也有四种不同的状态,从低到高依次为想象、信念、理智与理性。这四种状态也相应地具有从低到高的真实性。
由此,柏拉图构建起一个关于存在之真等级秩序模式。在此秩序的上层是理智与理性所能认知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较高和最高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永恒不变的自我完善的整体和事物存在的目的,也是下层可感世界的原型和存在的根据。在此秩序的下层则是人的感官可感知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具有较低的真实性,这—方面是因为人的感官对存在的认知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摹仿”,其本身就是理念的影像而已,这些影像生灭变化无常,只具有个别性、偶然性和相对性。人的心灵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世界,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掌握真理。艺术和诗歌,在柏拉图看来,只是对可感世界中那些模糊的影像的摹仿,也就不可能引领人的心灵向高贵的理念世界超越,而只会让人更深地沉溺于感性之中,因此在本质上是有害的。
庄子与柏拉图对于真的具体内涵的看法不同,庄子的真论侧重于真之主体性,柏拉图的真论则侧重于真之客体性;庄子认为返本归真之路在于彻底排除理性认知,而柏拉图恰恰强调理l陛对于求真的极端重要性。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在人类的认知领域,真才具有最高的价值;真不存在于一个即目可见可闻的几俗世界,而是需要透过“灵魂的眼睛”或“听之以气”才能体验到。
那么庄子与柏拉图的反诗歌的思想何以成了诗学的源头?在这里也许我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即虽然他们否定了诗歌,但他们否定诗歌的理念所指向的恰恰是诗歌本身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对既存世界的超越。人类之所以有哲学与诗歌活动,究其实即在于不满于感官世界的有限性,而要向一个超验的世界作无限的超越,以寻找到一个真实的存在根基。人类不能像动物那样浑浑噩噩地生活,而是要超越世界与自我,这正是人类的高贵与尊严所在。正如罗蒂在谈到柏拉图派哲学家时所评论的那样,“他们坚持主张,人类有资格自尊,只是因为他们让一只脚跨出了时空的界限”。不管是哲学还是诗歌,不管是为了心灵的安宁还是心灵的骄傲,跨出时空的界限,跨出人类感官领域去寻找真实,都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必然需求。庄子和柏拉图虽然否定诗歌,但他们在否定诗歌时对精神超越性的强调正体现了诗歌的根本冲动,这或许正是后世诗人们—方面坚持不懈地反驳他们对诗歌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热爱他们的原因。
柏拉图对于艺术和诗歌的否定引发了西方文化史上漫长的诗与哲学之争,在诗学史上则形成了著名的“诗辩”传统。柏拉图之后,首先为诗歌做辩护的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后者在把诗歌与历史作比较时认为,诗歌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只叙述个别的事,带有更多的偶然性。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提诺通过对柏拉图诗学观念的改造提高了诗的地位:诗不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摹仿、也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是分享了神的光辉的。锡德尼针对有人称诗为“罪恶的天堂”的偏见,热情地为诗一辩,认为一切学问从属于自然,而诗则在摹仿自然时创造另一个自然,这另一个自然是以“应然”而不是“曾然”为根据的,因此更加符合道德,与历史相比更能促人向善,而与枯燥的哲学相比其形式上的美更具怡情阅性的动人效果。雪莱则一方面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诗的创造再现了上帝的创造,反映了上帝的心灵,像上帝那样使美善统一,把人的心灵引向永恒、极乐的境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诗歌辩护士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强调诗与真的关联,诗的合法性即在于诗以特殊、有效的方式表现和揭示了真。
近代以来,随着康德把真善美这三大人类认识领域作了区分之后,诗歌就被归入到美的领地。美成了为诗歌进行辩护的最强大后盾。极端如王尔德,直承艺术与诗歌就是谎言,这谎言就是美,与真无关。而在当代,后现代思潮几乎把真的观念摧毁了,诗与真的联系就更稀薄了。然而诗歌真的能够做到把美当作唯一的安乐窝吗?诗歌真的能够面对人类的悲剧性存在处境闭上眼睛吗?失去了“求真意志”的诗歌,还如何能够点燃人类的激情?面对这样的艺术状况,阿多诺激愤地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的”,其意即在于警醒我们:诗歌不能在美的麻醉下失去反抗的力量,沦为既存秩序和规则的认同者和维护者,而是要时时刻刻以揭示存在之真为最高目的。
奥德修斯的航船难免会为塞壬的歌声所吸引,乃至迷失航向;但要回归故乡,他就不能逃避大海上汹涌的浪涛。诗歌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