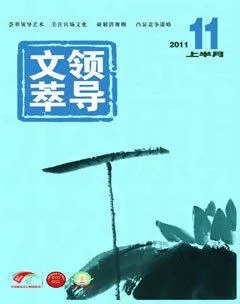黄万里的悲壮人生
2011-12-31述弢
领导文萃 2011年21期
三门峡位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早年在此进行现场勘探的德国人曾得出结论:在三门峡筑坝,等于修建一个危害关中的死库。这个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也研究过,都不敢定案。然而1954年年底苏联专家科罗廖夫拿出规划来,我们就定案了(其实科罗廖夫只懂工程,对河流一窍不通)。邓子恢副总理在人大会议上豪迈地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1955年,周恩来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对关于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均交口称赞,只有一人发言表示反对。这位名叫黄万里的清华教授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黄万里发言何以底气十足?原来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后因目睹黄河水患频仍,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出国留学改修水利。他曾驱车45000英里跑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又风尘仆仆,行程3000公里,6次徒步考察了长江的支流金沙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对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情况可说是了然于胸。
1957年,在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再次力排众议。他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本来河道里的泥沙起到了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而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既违反自然规律,又不现实,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争辩7天无效后,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但水库施工时仍然坚持按原设计将6个底孔全部堵塞(1970年代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不幸而言中。三门峡水库蓄水后,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即淤积了15亿吨泥沙。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水库尚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即全部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1961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雨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这是后话。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针砭时弊的《花丛小语》。惹得龙颜大怒,斥之曰:“这是什么话?”于是钦定右派黄万里受到批判斗争,工资连降两级。父亲黄炎培系同盟会会员,与中共合作多年,当时虽身居高位,也爱莫能助。
耐人寻味的是,黄炎培老先生1945年曾访问延安,与最高领袖有过一次关于“兴亡周期率”的对话,即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最高领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言之凿凿。黄炎培所著《延安归来》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在国统区影响很大。许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有人甚至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谁知事隔十余年,黄老先生的三子黄万里仅仅因为在校刊上发表《花丛小语》,从此失去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黄老先生膝下竟有6个子女和1个女婿划成右派,堪称“右派之家”。所谓“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也者,成了绝大的讽刺。
尽管遭到如此巨大打击,黄万里仍痴心不改,1964年,他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
此次系上书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总算有了回音。水利部领导约见黄万里,嘱他提出改进计划。黄万里日以继夜,用60天的时间完成《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可惜黄万里的建议未予采纳。
这一年的春节座谈会上,领袖向黄炎培提到,“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这分明是一个信号。当时只要黄万里写个检讨认错,就可以顺势摘掉右派帽子,可他却并不领情,更赋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态度如此决绝,就是不低头。既然这么“不识相”,那摘帽之事自然搁浅。
1966年夏天,“文革”的狂飙席卷而来。黄万里首当其冲,饱受皮肉之苦。下放疫区劳动期间,年近花甲之年的他也得干重活,曾因体力不支,中暑晕倒,险些丢命。尽管如此,他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
1981年,他终于在阔别多年之后,精神抖擞地重登讲台,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授课,并继续研究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策略、华北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明渠不恒定流力学等问题。黄万里还对三峡工程建言献策。可惜已经时日无多。
2003年陕西遭受洪涝灾害,本是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所造成的后果却相当于50年一遇的洪灾。此次洪灾黄万里已经无从得知了,他早在2001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了,带着太多的遗憾和困惑,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