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企业老板:跑路与跳楼的背后
2011-12-31张锐
澳门月刊 2011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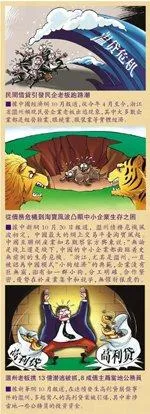



在民营资本湧动的溫州,企业老板负债出逃的事件不断上演,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溫州模式”的再度考量,而且也可能招徕公众对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溫州人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与此同时,相比於只对溫州债务危机的表层观察,我们从中作出的透视与反思则更加沉重。
溫州的闹剧与惨剧
儘管企业老板负债而逃並最终留下满地鸡毛的商业现象在溫州已经不算十分稀奇,但进入2011年以来民企老总成群结队撇债出逃的结果还是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特别是当一些知名企业老总也加入到了大逃亡的行列中来甚至引发了跳楼的惨剧时,政府和公众明显感知到了溫州所释放出来的不安与恐慌。
与那些慌不择路而匆匆逃离的老板相比,溫州正得利鞋业董事长沈奎正选择的解脱方式更为惨烈。据银行方面披露的信息显示,沈奎正旗下公司之前曾向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贷款即将到期时,转借民间高利贷2.3亿元,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並未获得期望的续贷。最终,在债权人的跟踪式追债和遭遇恐吓之下,沈奎正当着追债人的面从22楼一跃而下。
资本投机的代价
凭借着“中国犹太人”的聪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昔日裡,溫州人不仅将一个个小作坊经营得风生水起,並且将打火机、灯具、眼镜、皮革、製锁等利润率並不起眼的轻製造业做成了溫州的支柱产业,溫州由此赢得了中国“製造之都”的美名,“溫州模式”也成为了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和国际舆论歌颂的成功样板。然而,人们如今已经很难从无论是媒体实时报道还是专家学者的解读中,听到对溫州人“风风火火办实业”的溢美之词,代之而起的是对溫州商人如今成群结队走南闯北进行“投机”与“炒作”的担忧和诟病。
恰恰相反,实业资本的急剧收缩卻18ccf7df8bdd7924cd15f3d93f89be45f05f8faaa5da326c38f15dc6fd0d1d15成了今天溫州经济生态的真实写照。据央行溫州中心支行披露,2011年仅有35%的民间借贷流入实体经济产业,较2004年逾90%的比例大为下降。无独有偶,溫州市经贸局一项对该市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製鞋、眼镜、钢铁等这些原本支撑溫州经济飞速发展二十多年的行业正普遍面临着规模性萎缩,其中有25%的鞋类、服装、製笔、锁具等企业不愿继续承接或跟进订单。
曾经佔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溫州金属打火机是溫州人的骄傲,但也是今天萎缩程度最为严重的业态。与鼎盛时期1000多家企业的壮观景象相比,如今仅存100家左右的尴尬结果的确让人大跌眼镜。不仅如此,同样令溫州人引以为荣的製鞋业在发展高峰时期曾有超过6000家製鞋厂,但目前鞋企的数量已降至2000余家。另外,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溫州柳市镇,2010年规模以上的企业中,有70%以上的利润没有投资到本产业中。
与实业生态的全面萎缩和凋敝不同,溫州资本向房地产、矿产等资源品领域的流入已蔚然成风。据溫州市官方统计,在目前高达1100亿元左右的溫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中,包括高利贷在内的民间借贷资本有70%—80%流向了房地产等领域。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2010溫州市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除了在房地产、矿产资源以及原材料期货等领域大展拳脚和兴风作浪之外,溫州人介入博彩业则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投机的本性。前不久,海南警方破获一桩赌博案,有105名涉案人是溫州人,其中30多名为女性,涉案资金2000多万。而在此之前,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在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捣毁的一个“团赌”窝点,涉案资金上亿元。该赌场由溫州人开设,主要邀请众多溫州富豪太太驾驶名车或包机前来豪赌,其中输赢以十万、百万元计,一名阔太太在一小时内输掉1700万元。有媒体惊呼,“溫州太太赌博团”已经成为继“溫州太太购房团”之后的又一新生组合。
对於溫州人毫无遮掩的投机行为,人们可能会对其表现出的贪婪嗤之以鼻,甚至上升到商业伦理道德的角度予以鞭笞和诅咒;然而,脱离客观与背离理性的任何评价与批判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和牵强附会。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产能过剩越来越剧烈的产业背景下,以低、小、散为主要特征的溫州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加之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压力,溫州中小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強烈的挤压,其基本年利润收窄至3%至5%。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上演了10年续涨的“神话”,使得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和杠杆效应得以成倍放大。一位溫州老板做实体经济,一千来人的厂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润刚刚百万,可他夫人在上海买了十套房,八年后获利三千万。面对着如此強烈的利润反差,资本必然从实业领域大规模抽撤並向回报率丰厚的资源品地带集中,它所折射的出的是资本逐利的原始本能以及对给定环境的敏感反应。
自2010年以来高密度推出的房市调控政策让房价续涨的神话戛然而止,溫州人感到资金大量沉淀於房地产上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在於,那些依靠从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而投资房地产甚至参与博彩的“投机客”,在一路推高民间贷款利率的同时,也让许多溫州企业老板的偿债压力与日俱增,资金链条断裂的风险一触即发。
“妖魔化”的民间放贷
被称为“草根金融”的民间借贷力量在溫州民营企业的成长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金融危机之前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化生态,不仅年坏账率低於1%,借贷资本年利息也普遍维持在12%~20%之间。这种健康的民间金融环境在维繫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循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造成了溫州人敢於借贷、全民借贷的现象。
实体经济回报率的萎缩以及过去多年房价和资源价格的暴涨催生了溫州民间借贷规模的迅猛膨胀。根据人民银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计算,目前高达1100亿元左右的民间借贷量已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不仅如此,在年利率动辄高达100%甚至180%以上的巨大诱惑力量刺激下,各路溫州民间资本在民间借贷市场演绎出了全民式狂欢的特殊镜像。
镜像之一:担保公司。溫州活跃着约270多家担保公司,由於担保费收入只有3%,所以溫州担保公司99%都不务正业地热衷於民间借贷。一般而言,担保公司在民间借贷中往往承担“过桥”作用,企业注册想要注册资本,担保公司出资注册完成后企业抽逃注册资金归还;企业归还贷款再转贷有困难,担保公司垫资,企业获得新贷款后归还。
镜像之二:中小企业。受高息诱惑,中小企业主也加入放贷阵营。一方面,儘管实体产业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很少,但为保证资本运营,许多企业依然需要这张“壳”来获得银行资信和信贷。另一方面,企业多以扩大产能、技改等名义,用企业资产去银行抵押而获得贷款,然后企业将获得资金放贷出去。据人民银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溫州大约有六成以上的中小企业参与了民间放贷活动。
镜像之三:商业银行。由於利率双轨和商业银行对部分信贷资金的流向存在监管缺失,部分信贷资金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而且其进入方式比较隐秘。一方面,部分银行工作人员利用其社会资源扮演融资中介,通过中介以垫付保证金虚增存款或联合中介为客户垫资还贷等形式从银行套取信贷额度,然后再翻倍放贷出去;另一方面,银行可以低息贷款给上市公司或国企,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高息发放出去,银行收取正常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各得其所。
镜像之四:公务员。在溫州民间借贷链条中,公务员甚至官员的身影频现。在溫州,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不少官员甚至可以获取更多的信贷额度。由於实业投入回报率低,许多公务员选择将从银行获得的低息贷款高息转贷他人。
显然,附着於高利贷链条上的绝大多数放贷主体都与银行的信贷活动保持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货币政策风向标因此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一资金链的风险化程度。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至2009年,扩张性货币政策让溫州的中小企业和借贷人很容易从商业银行获取信贷资金;但是,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在极大地压缩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和能量的同时,也使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之门骤然收窄甚至关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寻求资本。问题的关键在於,在抽资和禁止续贷的同时,银行还纷纷提高贷款利率,受此驱动,溫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路劲升。然而,在只有3%—5%的实业资本利润率以及强大房市调控政策挤压之下投机资本风险骤增的基本生态下,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並最终以逃债和逃命的形式表现出来。
制度扭曲的必然
表面上看来,溫州债务危机主要由溫州资本的过度性投机以及偶发性调控政策引致而成,然而,跳出溫州看溫州,人们会清晰地看到,对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得到矫正与根治的制度性歧视才是引发溫州企业逃债闹剧与悲剧的真正力量。
金融抑制所导致的信贷资源错配是中小民营企业忍受的最大制度之痛。所谓“金融抑制”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決定利率和汇率並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在我国,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官办金融机构垄断了大量的信贷资源,而且无论是信贷资源的使用,还是利率水平,大多是基於行政指令的配置,导致民营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资料显示,在目前我国各类商业银行贷款中,国有企业佔去了贷款总量的80%,而民营企业的佔比却不到20%。然而,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民营企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卻达60%,后者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利率双规制之下的国有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以低成本获取信贷资源,而由於民间金融的长期非法存在,民间借贷利率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而飙升,高成本所引致的资金链断裂危机从民企借贷之日起就已经埋下伏笔。
与金融抑制紧密相联的还有投资模式的国有化偏爱。依靠投资拉动特别是依靠中央政府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在2008年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出台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观察发现,在过去两年大量的财政资金被国有企业腾挪到房地产领域从而製造了一个又一个庞大国企“地王”的同时,丰富的信贷资源更多的是集中在了大干快上的高铁等项目之上。虽然如同溫州的民间资本也参与到了房地产领域的利润角逐中来,但在随后而来的严厉调控政策打压下,首先倒下的就是风险承受能力本已脆弱的民营资本,而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借助其雄厚的资本优势抽身而退甚至毫发无损。至於诸如肥水四溢的高铁等投资领域,民营企业除了无奈承受着由此拉高的原材料价格之痛外,完全没有能够问鼎与青睐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溫州产业空心化与投机资本大行其道可以说是民营企业被“逼良为娼”的结果。
产业垄断是时至今日屡遭国内外舆论反复诟病的主要话题。最近十余年,伴随着产能过剩以及私人资本的日渐雄厚,民营企业急需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地带。然而,扫描国内不难发现,大凡利润丰厚的行业无不都是“国”字当头,如石化行业由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巨头把持,电信领域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几大央企操纵,金融行业的阵地则更是由国有银行悉数瓜分。虽然溫州资本曾经尝试在山西煤炭与新疆油井等局部领域寻求突破,但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私人资本运动清理运动扫地出门,而至於稀土、金矿等令人垂涎欲滴的产业,民营资本更是毫无立足之地。強大的“挤出效应”不仅令民营企业感受到了生存与扩张的艰难,也将其逼上了铤而走险的地步。
凌驾於民营企业身上的沉重税负映衬着中国改革不彻底的尴尬结果。据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我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今年将达到35%甚至40%。除了上缴繁重的税收外,我国企业还必须接受总量达8000亿元之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税费的膨胀折射出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肤浅和辍步不前,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官僚机构的层层寻租以及行政审批程序的错综凌乱,中国企业的成长环境日益恶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国有企业在与权力资本的较量中具有一定博弈能力的话,而那么面对着强大的寻租势力,中小民营企业几无还手之力。
当然,我们可以从官方打出的挽救溫州民营企业的政策“组合拳”中感受到推动民营企业前行的力量,但是,如果不对中国的金融制度进行纠错与再造,继续漠视垄断力量堂而皇之的存续与横行,或者任由权力资本的肿胀与嚣张,类似溫州企业老板背信出逃的闹剧和丑剧还将继续上演。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