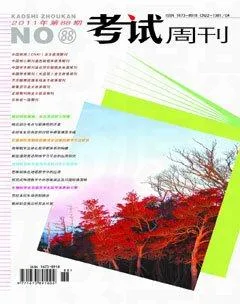试论文学翻译中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2011-12-31钱静一
考试周刊 2011年88期
摘 要: 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方言的处理是翻译过程中时常遇到的问题,给译者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方言对译法在文学方言翻译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根据读者需求提出改进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 方言对译 可行性
一、引言
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各类语言品种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及心理意识的当属方言了。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所谓地域方言,指的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所谓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一个人的话语应是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结合体。
文学方言是“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吴来安,2007:96)。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方言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dialogue)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使用文学方言是真实刻画小人物最起码的要求的话,那么,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则是实现完美再现原作人物形象的最可靠的途径。大量翻译实践证明:只有采用文学方言作为译语,译语读者才有可能像原语读者那样,欣赏到栩栩如生、可亲可信的人物形象。但是方言的处理是翻译过程中时常遇到的问题,给译者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正如韩子满先生所说,方言在作品中不仅传达了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通常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文体功能,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帮助刻画人物、或为作品增加幽默感及讽刺力量等。由于各语言和文学使用方言的传统不同,同时也由于方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差异,这些功能往往很难在译文中加以体现。正因如此,译者们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经常会引起一些争论(韩子满,2002:86)。文学方言的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关于方言对译
所谓“方言对译”,也就是用译入语中一种方言的成分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在西方,方言对等翻译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支持。奈达(Nida)认为罗杰斯(B.B.Rogers)的译作——阿里斯托芬的《亚加亚人》(The Archarians)是“方言对等的突出范例”(Nida,1993:112),译者采用麦加里农民的土话(Megarian farmer’s speech)来处理原文中的方言,将原文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卡特福德(Cartford)也认为,巴黎方言是伦敦土话“合适的对等物”(Cartford,1991:102)。
国内采用方言对译法处理文学方言的例子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张谷若先生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他旗帜鲜明地提倡以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强调要摆脱原语语言的形式束缚。中国的四字格在译文中运用得恰到好处,译者成功地重构了威塞克斯美妙的自然风光,原文中刻画乡土人物的威塞克斯方言凸显了乡土气息,译者采用山东方言对译原文中的威塞克斯方言,从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这种乡土气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功能对等”,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可以充分领略与原作同等的艺术魅力。郭著璋认为其译法“不失为传译原文中乡土气息的成功做法”(郭著章,1984:746)。
三、英汉文学翻译中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1.英汉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对比
长期以来,英汉文学方言的使用一直存在。在文学中,方言的使用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整个作品都是用方言写成,另一种是利用方言词语来塑造人物形象;而后者在方言文学中占绝大多数。英语与汉语本身存在差异,文学作品中的英语方言与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存在。
与中国文学作品相比,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似乎更具普遍性,且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许多大作都是由方言写成的,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历险记》,约翰·斯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社会真实感,同时也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气息。然而,汉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方言使用的痕迹。另外,英语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各地区的方言,如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苏格兰方言甚至黑人英语;而汉语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仅以北方方言为主,如陕西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等。普通话和各地区方言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得这类作品很难获得普遍认可。
基于英汉文学作品的写作模式的差异,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英语文学作品中,方言通常用单引号、单词缩略形式或标准英语中的其他单词加以区分。因此,方言与标准对等语的发音差异便随之而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就有了语音偏差。而对于汉语来说,地道的汉语注重的是表达出词汇的意义,文字通常也反映不出方言的发音形式。因此,汉语书写中要准确表现出方言的发音是不大可能的。换言之,大多数汉语文学作品中,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的意义上。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
翻译文学方言时,译者应谨慎选择翻译方法,以再现其与标准语之间存在的差异。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很多学者通常采用汉语方言翻译英语方言的方法。尽管英汉文学方言存在差异,但是两种方言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即为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展现原文的文体特色。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的对译是可取的。
2.如何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
方言对译法能从某种角度上传递原文所体现的韵味,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提高方言对译的可行性,从而使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首先,要谨慎选择目标语中的方言。一般而言,汉语方言可分为北方方言群体与南方方言群体。在两者之间,北方方言群体的发音更接近标准语或普通话,因此更能被大众所接受。以下例证正好说明这一点。
“And,”added the Mother,“we are,too.”
“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cried Father,“Why don’t you tell a fellow?”
“再还有,”母亲随随便便地找补一句,“咱们也有了。”
“乖乖龙底东!”父亲直叫唤。“你怎么不直爽点儿说哇?”(Liu,1991:134)
整体来讲,译者采用归化翻译法,将“Great jumping grasshoppers”译为“乖乖龙底东”。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拍手称赞。但是“乖乖龙底东”是江淮方言,属于南方方言群体,适用范围只在江淮一带,这对于北方读者来讲,很难理解其含义,不具备广泛的可接受性与认可性。因此,文学作品中采用方言对译时,目标语方言的选择相当重要。表面上看来,北方方言只适用于北方,但严格意义上讲,北方方言涵盖范围极广,且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小,即使是南方人也能很容易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相反,南方方言群体之间差异较大,彼此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大。因此,翻译文学方言时,采用北方方言,如北京方言、山东方言、陕西方言,作为对译的目的语较为合适。
其次,方言对译时要注意结合口语的表达。翻译过程中必须避免太过方言化的表述形式,过于方言化的表述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an’ to kiss and to call’ ee all at once.”(Hardy,1996:51)
“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Zhang,1957:63)
“怎么?她哪儿能一下就把你又搂又抱,又亲又吻哪?”(Zhang,1984:71)
山东方言“抱上锅,撮上炕”太过方言化,没有完全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含义,反而让读者费解。因此,在1984年的修改版中,张谷若先生将译文改为“又搂又抱,又亲又吻”。与之前的译文相比,修正后的译文口语化的表述更忠实与原文的表达,且更易理解。若方言表述不能清晰地表达出原文中方言的隐含意义,口语化的表达更具说服力。
最后,采用方言对译时,要恰当使用注释。许多作品中,原文方言的表述是源语言文化的独特体现,有时在目标语中并无对等。这样的情况下,译者要清晰地表达原文的意义就有所困难。因此,注释的使用可以帮助译者清楚地表达原文的隐含意义,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
在例句“Every one placing her sheaf on end against those of the rest,till a stock,or ‘stitch’ as it was called,of then or a dozen was formed.”(Hardy,1996:108)中,“stitch”在汉语里没有对等的意思,但是在英语的当地方言里却有“麦簇”的意思。因此,张谷若先生在将“stitch”翻译为“麦簇”的同时,也加上了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再现了原文的原始韵味,体现了真实性。
四、结语
长期以来,涉及方言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方言翻译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类型不同,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两种文学方言的使用都具备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原文特色的功能。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的字面意义及会话含义也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汉语方言传达。因此,方言对译在文学翻译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若对方言对译法能加以改进,译文将更具可读性与可理解性。
参考文献:
[1]Hardy,T.Tess of the d’Urbervilles[Z].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6.
[2]Nida,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4]郭著章.语域与翻译[A].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86-90.
[6]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托马斯·哈代著.张谷若译.还乡[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80.
[8]吴来安.文学方言属性思辨及其翻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2):96.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