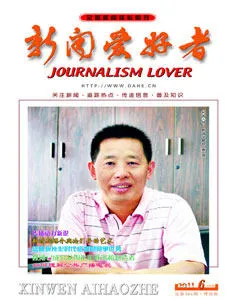民间信仰的环保自觉
2011-12-31李猛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2期
一
民间信仰是根植于民族民间生活习俗中的具有原始宗教特征的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表现,它是本土文化中自发产生的,具有原生性宗教的基本特点。历史上,贵州高原就是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东来西迁的南蛮族群,西来东进扩张的氐羌族群,由南北上的百越族群,由北南下的汉民族,以及在贵州本土形成、发展起来的百濮族群等族群于此融合、冲撞。它包含了民族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因子,因此,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状况和构成,有着其独特的原生态文化表象。
现在的生态文艺学注重研究文艺与人的外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学科。并且,以这一学科来传达生态学的审美理念,从而为宣讲人类的生态意识而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用生态文艺学的视界来看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文化,可以发现,以原生态为主要特色,经由民间信仰为表象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具有审美和生态的双重自觉。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生活在喀斯特山地上,长期与中国西南高原上的山水林泉、悬崖溶洞为伴,靠山吃山,大自然为他们带来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对他们造成许多生存中的艰苦磨难。自然崇拜的产生,源于人类早期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贵州,多数世居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中,自然崇拜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无论是祭山、祭树、以动植物为图腾的崇拜以及一些相关的禁忌,都表达了一种对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绵延至今,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发的对自然物,包括山水、树木、动物的爱护、珍惜和合理利用的观念,而正是这样的自然崇拜观念,产生了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环保自觉。这种自觉饱含一种审美价值和生态境界,比之政策法规指定的保护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到的作用更大。
二
以“摹仿”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传统文艺学认为,人在摹仿意识的支配下进行创作,并将人类融入其中。和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自以为是和为所欲为相比,由传统的民间信仰衍生而来的民族民间文化与自然是一种原生的、天然的亲子关系。因此,重新借鉴摹仿论,用生态文艺学的视角切入民族民间信仰,对于二者而言,或许是一种双赢的路向。
在贵州民间的自然崇拜观念里,万物有灵是一种基本理念。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不仅祭祀山神、树神,大凡自然界里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存在。而灵魂是不灭的,因为鬼魂不死,在鬼魂的世界里,比照人类社会,便同样有了善恶之分。因而在物,则有天神地祇,有山魈鬼魅;而人在死之后,也有灵魂升天或者成为厉鬼的不同。特别是对父母、祖宗的亡灵,子孙们更希望一方面为祖宗灵魂超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让鬼魂留在人间作祟,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
贵州世居民族“万物有灵”的观念源于他们的先民天地神创与祖创,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神秘力量的信仰。在仡佬族的神话里,就既有神造说,也有祖造说。而流传在黔西一带的仡佬族神话《巨人由禄》则说,“由禄的个子,高大无比”。由禄死后,圆圆的脑壳,变成坡头;立立的头发,变成了大茅草;干干的耳朵,变成了树木;明亮的眼睛,变成了海了;“长长的肠子,变成了江河,蜷蜷的腿杆,变成了山弯……”①显然出自于朴素、原生的哲学理念。
贵州少数民族的史诗、古歌中多体现出对于天地的崇敬与祭祀。比如从仡佬族的创世神话《布比格制天,布比密制地》、《太阳和月亮》以及《公鸡喊太阳》、《巨人由禄》里都可以看出那些人格神的存在。在他们的意识里,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神;而地则养育了万物。濮越族系作为农耕稻作民族,与天体与太阳的关系更为密切。几乎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射太阳”、“喊太阳”或“救太阳”的传说。贵州世居的少数民族中多有铜鼓,不论是夷系铜鼓或是濮越人的铜鼓上都绘有太阳,可以推想远古时代必有更为广泛而庄严的祭太阳的活动。此外,在贵州多处岩画中,大多都绘有太阳图像。
太阳之外,人们最崇拜的是雷。考察铜鼓产生的原因,即可了解到雷在百越族系的神话传说中,居于老大地位,因而有“雷王”之称。雷不仅掌管雨水,让人间造成干旱,还能造成洪灾,导至人类几乎毁灭。而在洪水神话中,雷的一颗牙齿又使人类得以延续再生,所以雷在贵州少数民族的心目中实际成了影响人类生殖、繁衍能力的神。百越族系如布依族、侗族、水族等等对月则怀有特别的感情;星对于夷人则是性命攸关的自然物:“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碗星,地上一家人;天上一星座,地上一族人。星好人聪明,星蠢人亦蠢,人死星斗败,人们常说道。”②他们是将天地奉为神灵,侍之如父母的。
除天地日月之外,大凡山、水、石、树、风与火等都是民间崇拜的对象。贵州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敬山神、树神的习俗,前述各民族三月三敬山神的风俗已可见一斑。有的村寨前还将石头立于庙内,披红挂绿作为神灵供奉。又如水神崇拜:布依、水族都兴祭河神,而在“开秧门”的第一天还兴祭水神。又如祭虫神,民间称为“赶虫”或“扫田坝”,多在六月六举行。布依族古歌《六月六》讲述的即是与此相关的故事;彝族的火把节即有焚烧蝗虫的用意。又如树木崇拜,仡佬、布依、侗、水、苗族等村寨一般都有一棵古树作为保寨树,每逢节日即用酒肉进行祭拜等。
通过以上的比较与分析,不难看出,无论宇宙是神造也好,祖造也好,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先民夜郎人总是将宇宙万物的来源归结为物,从物的消灭又回归物的产生。他们的想象与对世界的阐释都离不开可感知的客观实体。这里既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相信万物有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原始宗教的唯心论影子,同时也有着若干朴素唯物的因素。
三
当然,传统的摹仿论并不能彻底地全面地体现一种对自然的尊重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全面而且深入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并且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贵州的民族民间信仰虽然与中原汉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但是,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贵州民族民间信仰自然而然地也吸取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
“天人合一”的传统形成了属于它的既稳定又富有变化的艺术理想及实践模式和过程,所以,在中国,从感物出发进行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在文艺的历史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花鸟画……是如此的神采奕奕,它们与大自然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生态家园。而贵州民间的歌舞、蜡染、刺绣、婚丧嫁娶的生活习俗以及各种巫鬼禁忌,从一种先天性的信仰自觉,比之工业文明,更加有力地维护了这样的传统。
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属于生态文化。这根源于早期的农业生产科技的原始和开发的滞后,但是从人与生态关系的深度思考,这种原始与滞后则推迟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态的破坏。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想,也就再次体现了生态文化的生态禀性,为介入当代的生态文艺学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带有原始思维的特点。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原逻辑思维”,具有这种“原逻辑思维”的人们,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的经验”,因而“不作任何智力的努力,通过与一切人相同的智力过程的简单作用,就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哲学’,一种幼稚而简陋的但无疑完全是首尾一贯的哲学。这种哲学看不见它所不能立刻完全圆满解答的问题”。③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像城市工业文明,是带着一种征服和破坏的欲念,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于自然之上去观察自然;他们就在世界与自然之中,是其中的一分子,所以他们总是以自己为尺度,以人为尺度去观察、衡量客观世界,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这种原始的哲学及思维方式,正好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先民力图与自然亲近,寻求和解,希望达到天人合一的意愿与理想,因而有着明显的人文色彩。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也。“天人合一”交感学说因此在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流中产生。从工业化社会转向生态化社会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那么,对民族民间信仰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分析,去除其中陈腐而愚昧的部分,将其中的哲学、文艺精髓提炼出来,对民族民间信仰本身以及其研究而言,将会真正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生态境界。
注 释:
①《民间文学资料》第四十九集,第4页,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印。
②《物始纪略》,第二集第56~57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③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版。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