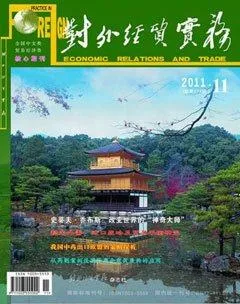美国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分析
2011-12-29刘友法
对外经贸实务 2011年11期
美国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已成为国际焦点问题。本文谨探讨美国债务危机的基本概念,探究危机的成因,并分析上述危机对世界经济及我国发展战略的影响。
一、美国债务与债务危机
(一)美国外债基本构成
美国对外债务由政府债务、公司债务和美国居民的债务三大部分组成。据统计,美国目前14.3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系指联邦政府的负债,并未涵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约2.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得到政府信用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约6.6万亿美元的债务。
从债务构成情况看,美国现有公共债务里,约4.45万亿美元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债务持有国,占12%左右。美联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美国债持有主体,持有额占10%左右。由此可见,美国国债中有将近70%由美国政府或本国投资者持有。从债务规模看,在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的总债务共计约3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GDP的246%。据美财政部统计,2008年以来,联邦政府为实施紧急救助和刺激经济复苏,导致国债陡增5万亿美元之多。再加上金融部门共14万亿美元的债务(内含“政府支持企业”约6.6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债务规模超过5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43%。进而言之,美国还存在大量隐性债务。美国长期实行高福利政策,以期维持和促进社会稳定。随着美国人口不断扩张,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美国在社保基金、医疗保险等领域负债经营状况愈发严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10年,全国范围社保基金隐性负债多达13.5万亿美元,医疗保险隐性负债则高达85.7万亿美元,两者相加,政府隐性总负债高达102万亿美元。
(二)美国债务特点
目前看来,美国债务主要呈现下列特点:
其一,隐形债务规模庞大。观察美国债务风险大小,不仅要其联邦政府负债,而且要看地方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负债;不仅要观察现有债务规模,而且要看其增长态势。这是因为,债务危机一旦爆发,所有部门的债务风险会迅速转化为主权债务风险,进而推高美国政府和机构的融资成本,导致信贷萎缩,驱使经济下行。据美国政府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执行董事长大卫·沃尔克(Laurence J. Kotlikoff)估计,2007年全球GDP大约54.3万亿,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与当年全球GDP总额基本持平。再加上100余万亿美元的隐性债务,美国早已进入破产状态。
其二,美债增长态势难以控制。美国于1985年结束了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此后,海外各界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外债负债率分别为62.3%、70.4%、75.0%、83.6%、95.4%、95.2%、95.9%和96%。至2010年,美债总额已占全球债务余额的24%左右,且以每年9%的速度上涨。与此同时,美国常年可持续的经济增速仅有3%。更为重要的是,二战以来形成的7,800万婴儿潮人口均已进入高龄状态。据美国劳工部数据,未来15至20年间,美国政府每年需要支付养老金人均40,000美元,年均总量3万亿美元。因此,美国经济迟早会受债务危机牵连。
其三,美国偿债能力难有保障。依据国际惯例,美国需要在每个财年内将其外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或上一年出口收汇额的比率控制在20%以下。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12月,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665.1亿美元。其中,出口1629.6亿美元,进口2035.5亿美元,逆差405.8亿美元。服务贸易方面,进出口总额798.3亿美元,出口464.1亿美元,进口334.2亿美元,顺差129.8亿美元。从财政收入方面看,2001年至2010年间,美国财政收入每年基本稳定在20,000万亿美元的水平,其中一半左右需要依法支付国民的福利开支,因此政府历年需要大量举新债,还旧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福利开支,尤其是养老金缺口将构成未来美债的黑洞,迟早将拖垮美国经济和债务清偿能力。美国债务总量已经大大超出政府的实际支撑能力,债务危机已经到达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
二、美国债务危机成因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因素
经济全球化先后通过资本链将生产和服务网络推向全球范围,进而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组织生产与销售,最终通过金融创新将衍生产品的销售推向实施对外开放的所有国家和经济体。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主导并且充分利用全球生产与消费领域的信用革命,将世界经济与本国的资本、货物、技术和信息市场融合在一起,将全球信用关系融入到本国经济与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最终通过债务关系主导和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正是在上述全球化经济发展态势作用下,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酿成国际金融危机,并且由虚拟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进而致使许多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最终美国也未能幸免。
历史地看,诱发这场仍在扩散的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创新,而这场金融创新的发源地是美国。为满足资本扩张对消费扩张的需求,美国金融业长期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当局与政府部门受本国经济发展利益驱使,对金融创新疏于监管,导致衍生品市场交易泛滥。以房地产领域次级住房贷款为例,在金融机构层层创新和保障下,原先每单元仅值100美元的产品,通过证券杠杆最终放大到5,000至10,000美元。起先总额仅仅数千亿美元的问题次级贷款,经过层层包装形成金融衍生投资品,在全球范围流通,每个单元的衍生产品被交易N多次,最终在金融市场被放大成几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窟窿。正是这个窟窿,最终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实施全面紧急救助,并将美国再度拖向债务危机边缘。
(二)国际货币制度因素
美元和美债构成是推动美国经济运行的两个车轮。依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不能发行美元,只能通过发行国债进行融资。与此同时,美联储也不能任意发行美元,而必须依据购买国债的数量发行相应数量的美元。因此,美元本位制实质上成为美债本位制。在这个体制下,美国通过印刷美元轻而易举地从全球范围获得劳动力、商品、资源和市场,而世界各国则用对外贸易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债和美元金融资产,进而为美国债务融资提供资金来源。就这样,上述状态周而复始,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通过美元和美债把全球经济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基本上纳入到本国债务循环之中,通过货币发行获得“铸币税”,通过利率获取“通胀税”,并通过汇率变动相应“写掉”本国的外债。同时,美国推行的经济、财政与金融政策也不时将美国推向债务危机边缘。
(三)政党政治因素
美国国会的立法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政府控制债务的能力。在现行委员会制度下,每个委员会及其相关成员对诸多法案拥有生杀大权。各委员会成员出于选区利益或集团利益考虑,经常在诸多法案中搭载与本选区相关的发展项目条款,并且利用法案审议规则形成相互支持对方提案的“选票交换”制度。例如,不同的委员会今天会联手支持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提高农业补贴的法案,明天又会联手支持退伍老兵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提高退伍军人医疗保险的法案。其结果,大量“民意和民生工程”不断将美国债务推向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在选举政治作用下,政府官员和立法成员为迎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