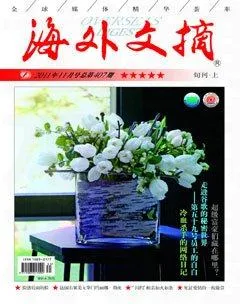我成了“坐牢”专业户
2011-12-29法布里奇奥.梅西亚欣哲
海外文摘 2011年11期
我本是一个安分的作家,如今,我落入了监牢。
在我痛诉我的入狱经历前,我想先做一个客观的说明:墨西哥的司法就好比至高无上的信仰、就像宣扬教义的礼堂、末日审判的再现,但能证明你清白的不是证据和证词,而是钞票。
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就只信奉因果报应,不相信坏人的存在。大家都认为如果你做好事的话,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的家人从不与人为敌,把一切恶事都归咎于经济、无知、年少、卑鄙或是厄运。
1998年,一件糟糕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一个忧郁的作家,他准备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写一本揭穿恰帕斯游击队员真面目的书。这支把争取“土地与自由”作为行动口号的农民武装队伍,自1994年1月发动武装暴动以来,与政府军冲突不断。这个忧郁作家的行为明显是为了迎合当时政府。我很气愤。
6个月后,忧郁作家写成了这本书并且出版。庆祝聚餐时,一些采访游击队员的专家团——他们是墨西哥政治谜案的英勇卫士,其中3人把这本虚假的关于萨帕塔主义的“历史书”撕个粉碎。 但那位忧郁的作家却认定这是我的主张,因为我说这是一本专为政治量身订做的书,而告我诽谤罪。
我的罪行得遵照墨西哥司法部门的处理:在进入法庭前,我必须赤身裸体地面对一位医生,警察在我身上拳打脚踢的印记也已经消失,医生还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我。
法庭上,我递给法官一本我自己的小说,希望他能理解、帮助我,可他把书扔掉,就像丢手榴弹一样,生怕我会与他同归于尽。1998年的那天,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对于世上无恶的观点彻底将我摧毁。我开始哭泣:我要去监狱了!
从此,墨西哥司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权有钱便是王法。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等着被害。从1998年到现在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墨西哥针对犯罪的斗争愈演愈烈,警察和士兵走到大街上,向着嫌疑人开火,然后逮捕,随意关押。这样,我又进了监狱。
那天,收垃圾的卡车没有来,我提着我的垃圾袋——里面基本是烟头烟蒂,把它放在广场上一个绿色的桶里。紧接着,一辆黑色吉普车挡住了我的去路,下来了8名警察逮捕了我,将我带上车,也拿走了那个垃圾袋,好像它是塑胶炸弹。
“把嘴闭上,不许说话。”在我不停地问他们为什么逮捕我时警察对我说。
早上我还听着情歌,吃着饼干,正在构思我新写的小说的第三章节,现在我却到了警察办公厅的一条乌黑走廊里,面对我的是监牢。
“垃圾不可以这样放,年轻人。”一位警官对我说,他拿着法院卷宗,而我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抓着扶手。“没事的,你是位作家,可以将你13个小时的监禁减刑变为罚款。”
“但我只是去把垃圾扔进了一个垃圾桶里啊。”我仍辩解着。
“那是个装沙子的桶,不是垃圾桶”,他说,“你还算个读书人呢。先待13个小时吧,之后告诉我你的感想。”
“长官,您也是读书人吧”,我对他说,“我请求把我的那袋垃圾给我,让我带回家,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让我浪费这13个小时的工作,谁会知道那不是垃圾桶呢?”
“不是为了这个关你”,他叹气道,“是为了钱。因为你没给他们钱。”然后他打开了牢房的门。
“而且还有指标问题,每月总得抓几个进来,说白了就是为了关你才要关你。”
就这样我又进了监牢。这是一个水泥牢房,墙上画得斑斑点点,就像以前的茅房一样。墙上还有一些字——“莫切斯到此一游”“泰格雷在此撒尿”等等。在我对面的牢房里关着两姐妹,南希和哈克莉内,分别是21岁和16岁。
“你俩为什么进来的?”才进来几分钟,我便像个惯犯似的问起她们来。
“因为买啤酒喝。”南希对我说。
“但这不犯法呀。”我说,脑海中又浮现起我的中产阶级家庭灌输给我的思想。
“因为天太热了,我们就在大街上打开了一瓶。”她微笑着说,“那些警察说我们随意在公共场合酗酒。我们还没有喝到一滴酒就被一群警察围上了,他们罚我们2000比索(墨西哥货币单位)。法官要关我们25个小时,虽然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喝酒,但今晚不得不在这过夜了。”
“今晚我也在这了,因为向一个装沙子的桶里扔垃圾。”
两姐妹笑了……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与犯罪抗衡”,这就是一个装满警察的国家。
[编译自西班牙《进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