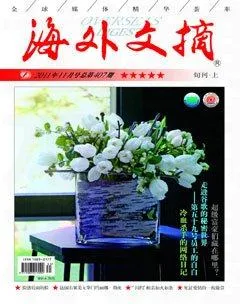“闪约”相亲如火如荼
2011-12-29叶莲娜.巴雷什娃郭丽姝
海外文摘 2011年11期
今夏以来,上至网络下到民间,各种相亲形式在俄罗斯如火如荼。由美国人发明的传送带式“闪约”相亲在俄罗斯非常流行,《星火》杂志派出记者亲历了一次“闪约”。
“该不该系领带?”我的朋友万尼亚拿着一条黑色领带站在镜子前。
“系什么领带呀!又不是去办公室上班。”
“好吧,那就穿牛仔裤,戴棒球帽。”
“这倒适合去健身。”
“白衬衫!穿白衬衫你总该满意了吧?”
真爱难寻
5年来,我多次给我的朋友万尼亚制造相亲机会。刚从新西伯利亚来莫斯科求学时,他甚至希望在大街上或地铁车厢里认识女孩,结果鼻子被打破(他上前搭讪时,女孩的男友就在附近),还领教了几句粗鲁的谩骂。
此后,他造访了各种潮流俱乐部和交友网站,仍一无所获。姑娘们用万尼亚的钱尽情享受,却换不来一点真心。直到万尼亚看了美剧《豪斯医生》,这部剧集的主人公通过快速交友方式(美国人称之为“闪约”)结识异性。第二天,万尼亚就把30份致力于解决人类孤独问题的公司名单放在我面前。原来,闪约在俄罗斯非常时髦,两年前这种服务机构还不超过5家,参与者也都是知名人士,现在“闪约”已经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办公室职员、公司经理和小型企业主成了它的常客,简而言之,都是些没时间和精力约会的人。
“闪约”的实质是传送带式的。组织者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要相亲,那就该让他有所选择,也就是说得多多提供候选人。为了不使大家感到别扭,约会以交谈方式进行,在几分钟之内介绍一下自己,再问问对方的情况,5-7分钟后信号灯响起,男士换到下一张桌子跟另一位女士交谈,不必感到难堪。“这是一场交友方式革命,适合事业有成却无暇相亲的成功人士。”维基百科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问问大脑的意见
万尼亚骄傲地递给我两张门票,晚上7点,我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俱乐部门前,这里每周有两次“闪约”。我们走上三楼,装出互不相识的样子。一位负责人把万尼亚领到吧台面授机宜,把我安置到围坐桌前的姑娘当中。
我暗下决心:我可不玩这游戏,太无聊了,我不想在传送带上找男友,短短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对一个人作出正确评价。然而“闪约”研究专家认为,时间越少,人们选择的可能性越多,就越清楚喜欢谁不喜欢谁。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大脑已经选择了可能符合你的标准的异性,任何短暂印象都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意义。无怪乎60%的俄罗斯人相信一见钟情。
依靠大脑的结果
他们发给我一个胸牌,号码是13,我暗中窃笑,但大脑却开始紧张起来。负责人鼓励女士们说:“就把这当成一次奇遇好啦!”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指令是,不要向男士询问工作和财务状况,这会让他们紧张。在我看来,“闪约”现场的女士显然都很富有。我左边的邻座一直在跟办公室通电话,确认货物何时到达;而右边的那位女士用电话向一位难缠的客户提供房产咨询。
有人给我和其他女宾拿来了“喜好卡”,这是“闪约”的另一个必要环节。短暂的接触过后,交谈双方要在卡片上给对方划上加号或减号,把它交给相亲会负责人。两天之后,他们会把互相中意的人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发给对方。卡片上还写着成功速约的处方:“由男士先开口说话,建议您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的兴趣爱好,跟对方聊聊对某些事件或影片等的观点和看法。”
负责人像马戏团训兽员似地发出讯号,于是男士们被领进装着女士的“兽栏”。
市场法则
“我想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聪明、漂亮、爱我、跟我的工作时间一致的女友。”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位陌生男子刚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就做了上述声明。“我第一次来这里,同事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喜欢的姑娘,就这些。您还想听我说点什么吗?”
“您叫什么名字?”我事先并未准备腹稿,想了半天终于找到这句话救场。
“尼古拉,34岁,在一家大公司当会计,没结婚,也没孩子。”
铃响了。负责人让他们串坐,我的尼古拉已经跑到下一张桌子前去了,看来我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下一个交谈对象叫瓦季姆,核物理学家。
“为什么这里全是技术型人才?”我问,“没有一个人文工作者。”
“技术人员都是实用主义者”,瓦季姆解释道,“我们脑子里对适合自己的女人有清晰的轮廓,来“闪约”的目的是想优中选优。在这里2小时内能认识很多姑娘,一年里都不见得认识这么多。”
我得找点话说……有了!我提起了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手镯,他大大夸奖了一番父亲送我的这份礼物。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滔滔不绝地谈着对装饰品的爱好。
下一位是35岁的大学法学教师,我胡编了一通自己多么赋于烹饪才能的话。他立刻向我索要电话号码。“我是不是下意识地希望给他留下一个我正是他需要的那种家庭主妇的良好印象?”我自问。不过我对面的人很快换成了维达利,一名汽车服务部老板,我跟他说我特别喜欢长途旅游,吃烤肉串,不是居家型女人。新娘市场自有一套行为法则,可我却用令人惊异的花言巧语迎合着每一名谈话对象的口味,叽叽喳喳地捏造着恭维话。
这时,我听见了万尼亚的声音:他就在附近,离我两张桌子,还真快呀!“我非常喜欢狗”,他的声音传到我耳边,“男人需要把缰绳拿在手中,这有助于他……”
万尼亚坐到我的邻桌了,他对那个女孩说,他是电视节目制片人,能安排她试镜,还说自己酷爱旅游,今天上意大利,明天上瑞士,可爱的小路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群山中蜿蜒不绝……看来男士在他们扮演的马匹的角色中也不轻松。
“噢”,万尼亚扑通一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真累。”
“撒谎累着了?”我暗示道。
“去喝点咖啡吧。”他权当没听见我的挖苦。
酒吧内空无一人,我们是惟一有勇气打破这僵局的人,也许大家认为我们是一见钟情的幸运儿。
“怎么样,看上谁啦?”万尼亚问。
“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坦白说,“这小伙子来俄罗斯寻找真爱,澳大利亚人很透明,不会掩饰自己。不过我也没什么跟他说的,但我诚心诚意地给这位来自悉尼的比尔划了加号。”
过了两天,我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闪约”俱乐部的通知:“叶莲娜,您好!我们发去跟您的喜好相符的那些人的联系方式。”下面是工程师尼古拉、澳大利亚人比尔、瓷砖销售员瓦连金的电话号码,还有两个人,我甚至连他们的长相都没记住,不过我确实给他们划了加号。我读了两遍来信,想了想,为了以防万一,暂时关掉了手机,要是当时我喜欢而现在却记不起来的那个弗拉基米尔打电话怎么办?最糟糕的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都对他胡说了些什么,因为在相亲现场,一切以快字当头。
[译自俄罗斯《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