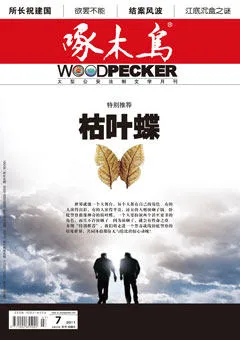危情百宝箱
2011-12-29吴建发
啄木鸟 2011年7期
1
上午没事,舒雨淇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看《洗冤集录》。临下班时,突然有两个女人走进他的办公室。前面的那个三十来岁,手上提着一袋子行李。她皮肤黝黑,体态臃肿,五官倒是很精致,大眼睛含情脉脉。后面跟着的女人个子不高,小巧玲珑,高胸、细腰、圆臀,曲线分明,很难一眼就看出她的实际年龄。
“您是舒队长吧?太太要我带她来投案自首。”走在前面的肥胖女人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舒雨淇。
“太太?谁家的太太?”舒雨淇心里在猜,并没说出口,只是从转椅上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她是申坤——申县长的老婆,叫胡丫丫,我是她家的保姆,叫包子月。”包子月赶紧补充道。
舒雨淇这下明白了。十几年前,他刚到警队报道不久,有一次参加大会,就曾听过申坤作反腐倡廉报告。那时申坤是县监察局的科长,后来申坤调出去了,一路升迁,如今已是邻县圩埔县的县长。“二位请坐吧,有话慢慢说。”舒雨淇感觉这事来得有些蹊跷,不管这胡太太是不是真的有罪,犯的是什么罪,来者便是客,还得以礼相待。
“我杀人了,我把我丈夫推下楼,他死了。”胡丫丫凄惶地说。
“真的死了?”舒雨淇当然无法相信。申坤高个子,身强力壮,这娇小瘦弱的女人怎么可能一推就把他给推下楼去呢?
“是死了,真的死了。”包子月说,“他俩吵架,太太不小心把先生一推,先生从二楼掉下去,就摔死了。”
“不,不是不小心,我是故意的。”胡丫丫抢着说,不停地抽泣。
舒雨淇心里琢磨着,这女人内心无疑隐匿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很明显是在急着要承担杀人的罪责,便忍不住转过头盯着她细瞧。她皮肤白皙,前额微微地住前凸,鼻头稍有点尖,齿白唇红,大眼睛单眼皮,一张很迷人的瓜子脸上写满郁闷、悲伤与沮丧。舒雨淇对这个申太太早有所闻。她在百姓中口碑载道,传说她性情温柔,待人接物温文尔雅,人缘也好,见人笑眯眯的,做人又很低调,夫妻俩结婚二十多年从未吵过架,连红过脸的时候都没有。她没有工作,在家专心相夫教子,一儿一女都很出色,儿子在北京,女儿在深圳,都是重点大学毕业,事业有成。社会上有议论说,申坤能有今天,全凭妻子积的德,这样一位贤良淑德的女人怎么可能谋杀亲夫?“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你丈夫?”舒雨淇问。
“我没工作,在家里无事,喜欢写诗,他不让我写。我在旧厝二楼上看我的诗集,他突然上楼来,抢走了i1ks1fzUHFoi0AmdQ4MlYw==我的诗集,撕了。我一怒之下,就将他推下楼,他就……就死了。”胡丫丫呜咽着说得话不成句,生怕舒雨淇不能相信她所说的话,不无顾虑似的,神色凄凉。
“其实申县长也不是不让太太写。”包子月补充着说,“申县长只是不喜欢太太把诗拿到报纸上发表。”看得出来,包子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
“为什么?”舒雨淇问了一句。
“我们也不知道,申县长做人低调,不爱家人抛头露面,大概是吧。”
舒雨淇“哦”了一声,站起来说:“走吧,我们去你家看看。”
“不,我不回去了,我杀人吃罪,我愿意坐牢。”胡丫丫显得十分执拗,死活不肯跟舒雨淇一起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性情温文尔雅的女人,叹息也如此轻盈。
“也好,你就到对面的招待所住着,我叫人带你过去开个房间。”舒雨淇转身对包子月说,“走,你带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场。”
2
舒雨淇赶在下楼前给助手李慧打了电话,当他走出楼梯口时,李慧早已经发动了警车。包子月从没坐过警车,神情颇有几分兴奋。她左看看,右瞧瞧,然后才伸出右手去拉车门。舒雨淇一眼发现她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便问道:“你手上的玉镯蛮漂亮啊,能让我看看吗?”
胖保姆将右手伸向舒雨淇说:“戴上去的时候我的手还小,现在发胖了,手太大,脱不下来了。舒队长您想看,只得连我的手一起看喽。”说着她瞅了舒雨淇一眼,抿着小嘴,露出一丝羞涩的笑意。
舒雨淇大胆地拉起她的手,仔细地审视着那个玉镯,许久才说:“这是一只镶金的雕凤玉镯,唐朝的精品,还有一只雕龙玉镯,一龙一凤形成一对,那可是价值连城哦。能告诉我吗,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六年前在地摊上买的,才花了三百元,仅这一只,不知道还有什么雕龙的。真能够价值连城,那我就发财了。”她明显是在撒谎,撒了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舒雨淇从她闪烁的眼神中发现她在说谎,但并没有拆穿她。十几年的刑事侦查工作经验,他学会了捕捉蛛丝马迹,也养成了这方面的习惯。当年江洋大盗胡大大在上海一个前清太监家中抢劫,杀了那个前清太监和他七十岁的老母亲,在抢劫的珠宝中就有一对龙凤镯。这事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震惊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史书上早有记载,舒雨淇当然知道。问题是,包子月的这只玉镯是不是就是被胡大大抢走的龙凤镯中的那一只?如果是,这里面又隐含着什么样的故事?
“快上车吧。”李慧在车里嚷嚷。
舒雨淇和包子月先后上了车。警车向申坤家驶去。
“包子月,你到申家当保姆几年了?”舒雨淇对坐在身边的包子月问。
“十五年了,”包子月回答说,“那时还是小姑娘,现在都成老太婆了。”
“嘿嘿,你不老啊,很耐瞧,多看几眼会越瞧越好看。”李慧转过身夸了一句。
“这位女警察还真会说话,”包子月被李慧说得心里甜甜的,却谦逊地问道,“我真的还好看吗?”
“那你当时是怎样来到申家的?”舒雨淇问。
“这事说来话长。”包子月说,“当时我在县合成氨厂做工,那时申坤是厂长。厂里突然发生了一次意外,是一次大事故,汽缸爆炸,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男朋友。当时我们都准备结婚了,”包子月脸露悲凄,抬起那只戴着雕凤玉镯的手,用袖子擦眼,接着说,“当时我痛苦得不行,真的是生不如死。是申厂长他可怜我,才把我叫到他家里做保姆,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几年,更没想到他会……”
3
说话间,警车驶进了大同巷。
这是一条刚好能开进一部轿车的小巷子,两边是红砖黑瓦的平房,闽南风格的老式建筑。申坤与胡丫丫的家在187号。根据包子月的提示,警车很快便在他们家的门口停下。
大同路的房子都很深,三米来宽,四五十米长,站在门口望不到底,当地人称之为“竹竿厝”。申坤的家也一样,进门是客厅,十来米长,地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落伍了的红砖地板,四面墙壁是几年前才重新抹过灰的白墙,两边摆着几张藤木沙发,足足可容纳十来个人落座。屋里阴暗潮湿,大白天还得开灯。客厅的后面有个小门,出去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右边是方方正正的天井,走廊的尽头是一座两层的老式小楼。舒雨淇与李慧并没上楼,而是径直地走下天井。
天井里有一个洗衣池,洗衣池旁边摆满盆花,月季、杜鹃、鸢尾、菊花、仙人球,相互拥挤在一起。申坤的尸体就躺在洗衣池旁边,看样子是从二楼摔下来的。舒雨淇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一眼二楼,也是红砖黑瓦,楼上的门在正中。两扇嵌着毛玻璃的木门敞开着,门前是一个狭长的阳台,一根长长的毛竹一头系在阳台前的立柱上,另一头往下垂,一直垂落到天井水泥地上。
包子月说:“阳台上本来是有围栏的,前些天整个围栏被台风刮落,来不及重新安装,太太就到市场上买了根毛竹用绳子系上,权且当作栏杆。哎,没想到……”她叹了口气,眼里滚着泪花。
舒雨淇蹲下身子去察看死者的脸部:眼睛是睁开的,眼珠子翻白,唇开齿露,牙关紧闭,手脚屈曲,嘴巴和眼睛歪斜,两边口角与鼻孔里有涎沫流出。他想起了刚刚从《洗冤集录》中背下来的一段话:“卒中死,眼开、睛白,口齿开,牙关紧,间有口眼涡斜并口两角、鼻内涎沫流出,手脚拳曲。”
“这不像是摔死的?”舒雨淇心里在说,但鉴定死因是法医的责任,他也没再怎么细想,便离开天井走入楼内。李慧与胖保姆尾随而入。
楼下地板同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落伍了的红砖地板,四壁同样是新抹过灰的白墙,除了一张粗糙而陈旧的木梯,别无他物,显得尤为空旷。
舒雨淇爬上楼梯,李慧与保姆又紧随其后。
二楼的房间与底层一般大小,没有隔墙,长长的狭狭的四五十个平方,墙壁也是不久前才抹过灰的白墙,绕着四壁堆积着杂七杂八不少东西,只有中间留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空间。
“唉,这里不住人,那你们人住哪里?”李慧一脸狐疑地问。
“住在新厝啊。”胖保姆回答。
舒雨淇与李慧不约而同地转身朝后门看去,才知道那里还别有一番天地:一大片的龙眼林,粗估一下大约有四十来棵;树底下是草坪,绒绒的绿茵;草坪上有条红色的空心水泥砖铺就的小路,弯弯曲曲点缀其间;四间白墙琉璃瓦房在浓荫掩映下显得神秘莫测;瓦房并不连接,而是选择在树与树之间间隙较大的地方独自而立,再由小径相连。
包子月介绍说:“最靠西的那间是厨房和餐厅;第二间是我的房间,同时也储藏一些食物和用具;再过来是太太的卧室;最靠东的那间才是先生住的。”舒雨淇收回目光,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这间“旧厝”里,因为这里才是出事的现场,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翻翻这个,看看那个,一切都十分正常,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房间的正中空旷处有只小圆桌,两只矮凳子,似乎有点异样。什么异常呢?他一时也摸不着北,抽了一支烟,突然顿有所悟:对,这小圆桌和矮凳比屋里的任何东西都要干净,一尘不染,洁净度与周围的物品不相称。也就是说,小圆桌与矮凳不久前有人使用过,而且是经过擦洗的,其他的东西只是储存物,好久没人动过,沾满了灰尘。舒雨淇又仔细地查找了一遍,在墙角上发现有根牙签。舒雨淇不敢用手去拿,而是从自己的裤袋里掏出钱包,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名片,用那名片将牙签挑起。李慧赶紧从提包中抽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拉开口子递到舒雨淇面前。舒雨淇将那牙签装进塑料袋内,对包子月说:“好了,去看看你们住的房间。”
4
在胖保姆的引领下,舒雨淇与李慧穿越龙眼树林,走进胡丫丫的卧室。这卧室装潢极具现代气息,与临街的“旧厝”相比,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
“他们夫妻俩是不是经常吵架?”舒雨淇问胖保姆。
“哪里?家里的事都是太太在安排,先生的衣食住行太太照顾得体贴入微,哪还有什么事值得两人吵架?不过夫妻吗,磕磕碰碰的事还是有的。我来他们家十几年了,他俩是吵过几次。先生是有文化的人,彬彬有礼,不常发火的人偶尔发起火来,还真吓人。”
“噢?为什么事?”舒雨淇问。
“有一次,太太写的诗在杂志上发表,那是在四五年前吧,先生知道了,大动肝火,还扇了太太一个耳光。”包子月生性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心里的话不说出来就会如同她身上的赘肉一样,极力想抖掉一些才会舒服。她眨了眨眼,极力压低声音轻轻地说,“先生不让太太抛头露面,有外人来家他也特别敏感。我跟随他们十几年了,他俩就只为这事吵架。有时候家里有烟头被先生发现了,先生一定要太太说清楚是谁来过,太太如实相告,先生还要打电话证实了才放过。有一次,我在蒸馒头时不小心被蒸气烫伤了手指,先生回来后,却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责问太太是谁来过我们家了。我和太太都说没有,先生不相信,硬说来人在家里过了一夜。先生的话让我俩都一头雾水,只好默不作声。后来先生从卫生间里拿来牙膏,追问太太:要不是有人在家过夜,牙膏怎么会是这样用的?因为我们家使用牙膏都是从底部往上一点点地挤,后面一段干瘪前面一段饱满,当时我烫伤了,拿牙膏抹伤口,一急,就从最饱满处往外挤。先生说了,使用牙膏的人因性格不同挤压的方法也不一样,要不是有外人来过我们家,牙膏是不会这样挤的。我和太太听了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先生得知真实情况后哑口无言,这事才算过去了。”
从胖保姆的话中,舒雨淇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申坤害怕妻子胡丫丫与外人接触,甚至接近于恐惧的程度。那么这个“外人”又会是谁呢?
局里的法医和痕迹技术人员已经在天井里忙着,舒雨淇想起刚才在旧厝二楼上发现的那根牙签,于是便提议道:“我们到龙眼林里看看。”
胖保姆带着他与李慧绕着鹅卵石围墙走了一圈。围墙上有扇小门,铁门紧锁着。舒雨淇要胖保姆打开铁门。门下面有五级石阶,下了台阶是湿漉漉的泥土地,一条砖块与碎石铺就的狭窄小路直抵荆江溪,溪流清澈见底。包子月说:“这个小门是专门下到溪里洗东西时才用的。一般是家里大扫除需要拿东西到溪里洗的时候才开门,平时是不开的。”
舒雨淇走下台阶,发现泥地上有串脚印,一脚深一脚浅,凭他多年的经验,断定是一个跛脚男人留下的。这个跛脚男人会不会就是申坤害怕他妻子接触的那个“外人”?旧厝二楼的那根牙签会不会就是这个“外人”留下的?舒雨淇心里想着,蹲下身仔细察看,见那些脚印十分清晰,上面水渍尚在,断定是清晨下霜之后留下的,于是要李慧去把技术科的老庄叫过来。
5
数百里之外的胡家坳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之所以闻名就因为那里有座老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天我们俩去一趟胡家坳。”舒雨淇对李慧说。
“真的?”李慧像小孩子似的一蹦老高,兴奋地说,“舒队你怎么会想到带我去旅游?”
“你以为我是想带你去旅游?做梦去吧。”
“不去旅游我们去干吗?”
“你不知道吧?申坤早年曾在胡家坳插过队。”舒雨淇说,“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是乘大巴还是自己开车?”
“当然是自己开车。”舒雨淇说,“你把车子准备一下,保养保养,油要加满,高速公路,不能……”
“好了,你不要婆婆妈妈的。”李慧打断了他的话,她最不喜欢舒雨淇那副“谆谆教导”的样子。
次日一早,俩人开车来到了胡家坳。
这座豪宅占地十余亩,除了主楼之外,还有五步楼、十步阁、息亭、花坛、假山。主楼是典型的客家传统民居围龙屋,占地四千多平方米,三层土木结构,以正堂为中心轴线贯穿整体,左右横屋相互对称,上下跑马楼四通八达,八厅八井十八堂,共有八十三个房间,蔚为大观,而且游客如云,络绎不绝,让舒雨淇和李慧饱尝了一顿视觉大餐。
宅子是胡大大留下来的。当年他偷了大量的财宝,于是回老家盖了这座宅院,给了他最贴心的九姨太后自己出逃香港,从此杳无音信。
舒雨淇和李慧在胡家坳住了两个晚上,了解到不少情况。原来,胡丫丫就是易兆芳的女儿,而易兆芳就是胡大大的九姨太。胡大大跑路后,易兆芳才十九岁,后来嫁给当地的贫农胡吉利,生下胡丫丫这个唯一的女儿。所有的故事全都在舒雨淇的预料之中,但原来只是猜测,胡家坳之行得到了证实。舒雨淇信心满满地与李慧回到警队,准备与胡丫丫正面接触,好让她说出事实真相,却听说包子月跑了。
6
好在舒雨淇早有防备,在去胡家坳前就指派警队里的小周和小罗盯紧她。得知包子月并没失踪,只是回了自己的老家圭坑村。舒雨淇放弃了与胡丫丫接触的打算,与李慧随即赶到圭坑村。
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江中往来船只,帆樯历历可数;西沉的红日,傍着山头往下坠落;灿烂的晚霞,是太阳的葬礼。舒雨淇和李慧赶到圭坑村时,包子月也是刚回家不久。
她是申坤家的保姆,其实也是申坤的地下情人。
申坤位高权重,本来有好几次住高楼大厦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当年他买下那座老房子,是看上了那块空地,以求日后地价不断攀升,事后证明申坤确实有眼光,现在那块地的价值已经翻了好几番。但更重要的是申坤想在龙眼林中建单人住的套间,一人一个房,才能背着妻子与包子月巫山云雨颠鸾倒凤。那时候包子月年轻貌美,身材苗条,亭亭玉立,申坤送了她那枚雕凤玉镯,还许诺日后再给她金条和珠宝。可是,随着日子的不断推移,包子月发胖了,赘肉横生,申坤也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原先的承诺就像放烟花似的,一声炸响,天空五彩缤纷,眨眼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地上的一堆纸屑。包子月知道申坤还藏有金条和珠宝后,心里就一直想得到它。申坤死后,胡丫丫前去自首,家里就只剩她一个人,于是她四处寻找,果真在申坤住的屋里找到了一只铁皮箱子。铁皮箱子是上锁的,她找不到钥匙,拿起来摇了摇,铮铮作响。她坚信箱子里面的东西肯定就是申坤说的金条和珠宝。她丝毫不觉得这是偷,因为主人早就说过,是要给她的。她没再多想,拿了箱子便连夜赶回老家,并不知道身后有警察盯她的梢。她刚到家才三个多小时,叫她哥拿来了螺丝刀撬开铁皮箱子:天啊,金灿灿的金条,成堆的戒指、玉佩、项链、耳环,还有银杯、银筷、银簪,那枚舒雨淇所说的雕龙玉镯也在其中。包子月兴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嘴唇打着哆嗦地说:“哥,快叫爸、妈和婶子过来看,我们发财了。”
一家人围拢过来,兴奋不已地大呼小叫,舒雨淇与李慧突然出现他们的面前。包子月蒙了,一家人全蒙了,大呼小叫的动作还没来得及收回,全都目瞪口呆地伫立着看这两位从天而降的警察,像一群形态各异的雕像。
“我,我……”包子月喃喃地不知说什么好。
“你是保姆,却偷了人家的财物。”李慧厉声喝道。
“不,我不是偷,申先生说过,这东西是要给我的。”
“可是你拿的时候,申坤已经死了,申太太知道吗?”
包子月自觉理亏低下了头。
7
包子月被带回警队询问,她如实地交代了自己这十几年来与申坤的关系,以及偷珠宝的过程。
这时,舒雨淇在旧厝二楼捡到的那根牙签, DNA检测结果也出来了,牙签上面的唾液既不是胡丫丫的,也不是包子月和死者申坤的。也就是说,在申坤出事之前,他们家来过一个外人,这个人在旧厝二楼吃过东西,用过牙签。荆溪河边留下的那串神秘脚印,技术员老庄说是一个男人的。此人身高一米六三左右,体重不到五十公斤,瘸腿,驼背。这男人是谁?与唾液留在牙签上的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与申坤和胡丫丫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包子月对此一问三不知。舒雨淇也相信,这个外人来到她们家,胡丫丫是不会让包子月知道,更不会让她看见的,于是找胡丫丫当面交锋。胡丫丫起先拒不交代事实真相,坚持说申坤是因为与她吵架被她推下楼摔死的。
“胡丫丫,你身材娇小,要将身高一米八零、体重将近一百公斤的丈夫推下楼,你真的能做到吗?”舒雨淇慢条斯理地分析道,“除非是在你丈夫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可你说是在你们俩吵架的时候把他推下楼的。人在吵架的时候精神亢奋,精力集中,大脑反应尤其快,动作也会特别灵敏,你胡丫丫出手推他,他肯定会迅速作出反应,只要他轻轻一挡,你胡丫丫根本敌不过他。说真话吧,胡丫丫。”
“我杀人,我吃罪,我说的就是真话。”胡丫丫十分固执。
舒雨淇叫李慧搬来从包子月那里缴来的铁皮箱子,掀开盖子让胡丫丫看里面的金条和珠宝问:“你见过这些东西吗?”
胡丫丫摇了摇头,神色淡然,看得出她以前真的没见过。
“这些东西是你丈夫的。”舒雨淇把包子月与申坤的关系以及她偷了金条珠宝的过程简单地向她说了,但胡丫丫还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淡淡地回答:“你说的这些与我无关。”
李慧看她如此漠然处之,心里有些急,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去过你家的老宅。”边说边盯着胡丫丫的眼睛,就想看看她作何反应。
胡丫丫果然一怔,脸上的皮肤紧绷起来,洁白的牙齿咬住薄薄的嘴唇,眉毛也竖了起来,不发一语。
也许豪宅里少年时代的故事才是她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她说出真相的钥匙。李慧心里想着,有着一种初战告捷的兴奋,接着说:“1976年,你们家的大宅里来了十几个下乡知青,不久后下乡知青一个个回城,只剩下申坤和伊勤酬两人,而申坤后来成了你的丈夫……”
“别说了,求求你们……”胡丫丫双手抱头,泪流满面,情绪异常激烈,“既然你们都调查过了,你们去找伊勤酬吧,他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们的。我实在是不想再回忆过去的那些事情,再说下去,我会发疯的。”
“那也好,我们就不难为你了,请你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伊勤酬。”舒雨淇说。
“我没有他的地址,不知道他住哪儿,只能给你们他的手机号码。”
李慧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笔,让胡丫丫写下了伊勤酬的手机号码。
8
结束了同胡丫丫的交谈,舒雨淇拨通伊勤酬的手机,对方问了句“谁啊”,一听是公安局的,立马掐断线。舒雨淇要李慧用她的手机再打。李慧接连再打了两次,却只能听到“您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的回复。改用办公室里的电话拨打,对方还是不接,后来干脆把手机也关了。
“怎么办呢?”李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舒队,你说怎么办呢?胡丫丫不说实情,伊勤酬找不到,这案子还怎么搞下去?”
舒雨淇抽了支烟:“别急,我有办法。”
“你还有什么办法?”
“他不是关机了吗?我们给他发条短信,然后就去睡个安稳觉,我不相信他伊勤酬能沉住气。”
舒雨淇说完,沉思片刻后编了一条短信:“伊勤酬,胡丫丫杀了她丈夫,想要见你最后一面,速与我联系。”舒雨淇编完短信没有直接发出去而是先把手机拿给李慧看。
“舒队,这条短信会不会太冒险了。”李慧说,“要是伊勤酬真是杀人凶手,我们不是在打草惊蛇吗?”
“不,他也不是凶手,申坤是自己惊吓致死。他坠楼的时候,人已经死了,或者说,他的死与坠楼同时发生,反正,他的死因并非坠楼所致,而是中风身亡。”
“你就那么肯定?”
“卒中死,眼开、睛白,口齿开,牙关紧,间有口眼涡斜并口两角、鼻内涎沫流出,手脚拳曲。”舒雨淇默念了《洗冤录集》里的一段话,“当时查看现场时,我就认为他是被吓死的。呶,你看,”舒雨淇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这是中午食堂吃饭时杨法医才拿给我的,他的死亡鉴定结论与我当初猜测的一致。我现在可以很坚定地相信,申坤是看到伊勤酬后被吓死的,用法医学的术语说是病理性脑出血死亡,也就是宋慈说的‘中风’。”
“那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害怕见到伊勤酬。胖保姆不是说了吗,他害怕太太胡丫丫见外人,得知太太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就大发雷霆,发现家里有烟头就追根究底,甚至于挤牙膏的习惯不对他都会无端地猜忌,可见他疑神疑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已经不仅仅是害怕,简直是恐惧。你说,一个恐惧到如此程度的人,在他害怕的事当真发生时,能不被吓死吗?”
“那又是什么事让他恐惧到如此程度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等见了伊勤酬,一切都会明白的。”
李慧把手机还给舒雨淇,舒雨淇将短信发了出去。而后两人各自回家睡觉。
9
次日一早,伊勤酬果然给舒雨淇回了电话。舒雨淇要他到办公室里来谈,半小时后,他来了。
他一头蓬乱的头发,趿一双人字拖鞋,驼背,跛脚,一身邋遢,犀利的目光四处张望。李慧要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并给他泡了茶。舒雨淇拉了一张椅子,坐到他的身边,并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烟,动作麻利地掏出打火机点燃,猛吸了一大口说:“你们警察真好,我这人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礼遇,没抽过这么好的烟。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犀利的目光柔软了下去。
他又狠狠接连抽了几口烟,那烟就烧去了大半截。舒雨淇又给了他一支:“我们就是想知道,那天申坤从楼上坠落时,你是否在现场?”
“是的。我找丫丫找了大半辈子,不久前才得知她已经嫁给了申坤,住在县城大同路187号。我找到她的家,是晚上八点多,丫丫给我开门,她见到我时,并没有立即认出我来。我走上前去,告诉她我是勤酬,她惊讶得差点没站稳身子,我赶紧扶住了她,没让她瘫倒在地。后来她叫我洗澡,换衣服,还叫附近的菜馆送来了几盘菜,安排我在旧厝二楼喝酒吃菜,并交代我此事不要让保姆知道。当晚,我们俩人就在旧厝里谈话,一直谈到快天亮。之后,我就趴在圆桌上打了个盹,她回新厝睡觉去了。天亮后,她给我送来早餐,盯着我吃完。之后,她收拾了碗筷,离开旧厝回到新厝去。临走时她对我说:‘你在这里待着,要是申坤回来,你就躲着不要出声,他一般不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回来也不会到这里来的。’没想到她离开后不到十分钟,申坤就回来了。当时,我正在抽烟,申坤特别敏感,一进屋就闻到了烟味,嘴里叫嚷着‘谁来我们家了’便径直上了二楼。我赶紧躲藏在一张废弃了的旧桌子下面。申坤高声大喊:‘是什么人?还不快出来,不出来我就叫警察了。’这下子我才从桌子下钻出来。当时申坤站在阳台上四处观望,听到响声,转身一瞅,看到是我,随之大惊失色,两眼翻白,浑身颤抖,身子向后一仰,瘫了下去。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他已经坠下楼去了。当时我也吓了一大跳,丫丫闻声赶来,她反倒比我镇静,将房里的东西收拾了一遍,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说密码就是我的生日,里面有四万多元,是她自己的私房钱,要我赶快离开,以后再也不要找她。我听了她的话,就下楼从围墙的小门离开了。唉,报应啊。”
“申坤,他为什么会害怕见到你?”李慧问。
“大概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看到了鬼,要不就是因为我的出现对他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他才会如此恐惧。”伊勤酬向舒雨淇又要了支烟,点燃后继续说,“1976年,我们十几个知青插队在丫丫的家乡,就落户在她母亲易兆芳留下来的大宅里,这事你们也许已经知道了。后来知青们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我和申坤。我俩与丫丫父女成了一家人。丫丫喜欢写诗,与我有共同的爱好,日子久了,我俩便相爱了。可是丫丫的父亲更喜欢申坤,他人高马大,上山下田各种农活都比我行。但丫丫死活不依她的父亲,每天晚上都躲在我的房间里与我谈诗,常常谈到深更半夜。申坤也爱丫丫,那时的丫丫小巧玲珑,聪明伶俐,没有哪个男人见了会不动心的。申坤得不到她,心烦意乱,有一天趁我们仨人一起上山砍柴的机会,将我和丫丫的父亲胡吉利一起推下悬崖……”伊勤酬眼眶里滚着泪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申坤把你推落悬崖是为了得到胡丫丫,可胡丫丫的父亲胡吉利与他无仇无冤,他为什么也要杀他?”舒雨淇问。
“为了一箱子珠宝。”伊勤酬说,“丫丫母亲的前夫留下了一箱子的珠宝,死后那箱珠宝交给胡吉利保管,没人知道,连丫丫也不知道,是我那天见到她后才告诉她的,她还不肯相信,我对她说了,她到现在仍半信半疑。”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舒雨淇问。
“丫丫的父亲在一次喝酒时无意中对我和申坤透露了此事。事后他对这件事就缄口不再谈起,他越是不想谈,我和申坤就越发认为那是真的。”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在李慧的再三追问下,伊勤酬才接着往下说:“胡吉利当场就摔死了。而我命大,没死,就在人迹罕至的山涧里躺躺爬爬,摘野果充饥,喝山泉水解渴,嚼草药治伤。七天七夜后,我才走出深山老林,以后就采草药卖钱,再也没有回过胡家坳。唉,一晃就是三十几年。”
“那你现在干什么,住在哪里?”李慧问。
“卖草药啊。我居无定所,上山采草药卖,走到哪里卖到哪里。”
10
舒雨淇和李慧把伊勤酬带到对面的招待所,让他与胡丫丫见了面。
和煦的阳光从窗户外照进来,温暖的光芒中微细的灰尘在上下飞舞。
舒雨淇和李慧将他俩送下大楼,送出公安局大院。望着俩人手拉着手离去的背影,舒雨淇百感交集,李慧也是感慨万干,眼眶里盈满泪花。
责任编辑/筱谢
绘图/王维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