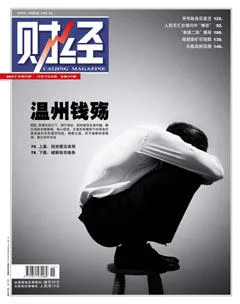中国科研体制获奖难
2011-12-29贾鹤鹏
财经 2011年24期

像往年一样,在中国人享受国庆长假的时候,诺贝尔奖新鲜出炉。颁奖之前,《印度斯坦时报》曾撰文《亚洲科学家将终结美国“垄断”》,认为亚洲的科学家们将成为诺贝尔奖的新宠。该报援引曾经成功预测十位诺奖获得者的评论家大卫·彭德勒布里的话说,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很快有更多人获得这个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并成为获此殊荣的“生力军”。文章称,美国人多年来在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上的“统治地位”将在数年内宣告结束。
这样的分析无疑满足了国人心理。今年的诺奖却仍是以美国人主导。
生理或医学奖由美国得州大学教授布鲁斯·巴特勒、法国斯特拉斯堡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朱尔斯·霍夫曼,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加拿大籍的拉尔夫·斯坦曼因在免疫系统方面的贡献获得。
物理奖几乎被美国科学家垄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索尔·珀尔马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天文学教授亚当·里斯以及持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赖恩·施密特获得了这一殊荣。
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舍特曼因发现准晶体获化学奖。以色列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亚洲,但在传统上仍然被认为属于欧洲。而坊间呼声很高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也没有得到这一殊荣。
游戏心态
回顾国内多年对诺奖纠结的讨论,最早一批“预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做出,其中说道20年内中国必将有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预测已经失效。
诺奖之所以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正如《科学家将研究视为游戏得诺奖 惊醒国内科研工作》一文所指,“因为我们在看待科学研究问题上走了两个极端,要么把学术行政化,以为凭借行政指令就可以把学术成果‘计划’出来;要么把学术神圣化,以为不通过高深莫测的‘登天绝技’不能研究出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把研究工作视为“游戏”是海姆和康斯坦丁团队的特点之一。西方科学家确实有不少人将研究工作视为“游戏”,这一点也可以从诺奖颁发前一周在哈佛大学举行的“Ig Nobel”(国内翻译为搞笑诺贝尔奖)中看出来。
今年Ig Nobel的生理学奖,颁给了英国、荷兰和奥地利的科学家有关海龟打哈欠传染问题的研究;生物奖送给了雄甲虫错把啤酒瓶当成雌虫盯上的机制;心理学奖的研究是人们为什么会叹息;而医学奖则授予了尿急时人们会对某些事情作出更加正确的决策,而对另外一些事情作出错误决策这一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奖不是杂耍,而必须是发表在知名国际科学期刊上的正经论文。只是研究者们在其中揭示的,并非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题目。例如,有关海龟打哈欠传染的研究,其实是很严肃的问题,动物打哈欠为什么看起来会传染,其中是否蕴含着特定的生理机制?
在Ig Nobel总共21年的颁奖历史上,大部分获奖者都来自西方。中国科学家唯一一次获得Ig Nobel奖是在去年,也就是2010年,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发表的有关果蝠的口交(Oral sex)性行为,获得了当年的生物学奖。这一研究的有趣之处,也恰恰是其意义所在:“人类性交前广泛使用口交,但这种行为很少在动物身上被观察到。”
但中国科学家做的这么有趣的研究实在太少了,而如果科学研究不是靠兴趣推动和驱使,那又怎么可能产生出新奇的贡献?
现阶段,我们真正缺少的可能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待遇,而是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待匡正。
模仿式赶超
当然,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因素保证,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如何能“匡正”呢?
wm2A2RloccJgEwbLdlKN2GCk5vKkXtg/liGCX1UtFKE= 从短期科技政策来看,我们倾向于实现以国家意志为基础的追赶和超越。在工程技术领域,这或许可行,如高铁虽事故不断,但中国毕竟建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高铁网络。
但在科学领域,重大的创新则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这在中国科研界存在很多障碍。首先,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基于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所发表的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学术界衡量期刊质量的主要标准,为全年该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数值越高说明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受人关注,期刊更加优秀),来考评科研成果的做法,也就是被科学家戏称为“论文的工分制度”的做法,让模仿已有思路进行新条件下的测试成为发论文的捷径。
其次,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有证据。如果证据是国外已经搞出来的,已经有文章发表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赶超战略的依据。
第三,中国的科研管理其实已经被标准化、程式化。随着PI(课题组长)制度的普遍确立,从PI的课题组成员到PI,到管PI的科研处长,再到管科研处长的所长/校长,固然不能说手里完全没有机动灵活的经费,但每一分钱都要看到花这笔钱值得的“证据”,这样也只能让科研人员跟着已有的研究成果、至少是研究思路走。
第四,在中国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花钱时,省着花钱(怕搞不到下一个课题以致团队解散,且资助款项往往划拨滞后)和突击花钱(结题前需要按标书花完钱)两种现状并存,导致人们很难以研究自身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科研安排。这种情况,同样导致了尽可能去模仿已有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因为如此才可让正在进行的研究经费安排更加有把握。
第五,在课题“交差”,也就是结题后,原创性的研究被人认可需要时间。即便发表,与短期之内对科研成果要产生影响的要求相比,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将一个已有的成果做得更加细致,条件做得更加极端,或者应用范围做得更广泛,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创新,但想达到获诺奖的成就,这样的思路肯定行不通。
最后,在中国的科研决策或者科研项目资助的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大项目决策过程中,有时会存在着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协调问题。即A院士投票支持B院士主导的课题的前提是,B院士支持A院士的课题。这一过程本身对科研工作的阻碍自不必说,而“交换支持”的前提,其实也需要大量的“证据”,而现阶段最好的证据,当然就是国外已有成果及中国的赶超了。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曾谈道,今年的诺奖新科状元巴特勒胆子非常之大,当年为了一个课题研究,把实验室所有的其他题目全部停掉,而这个题目有非常大的风险,但巴特勒看中了这个课题就全力以赴,非常执著,有冒险精神。
在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下,把各种并行的课题停掉,责任之大恐非一般研究人员所能承受。
而不得不承认,能取得诺奖级成果的精英,必然有大师的智慧,也必具有挑战权威的勇气。此次化学奖得主谢赫特曼的发现当时引起极大争议,为维护自己的发现,他花费数月试图说服同事,挑战了当时的权威体系,后不惜离开研究组。
长期政策短期化
而制度性的因素,固然有短期的科技政策的影响,但长期政策短期化,也让人难以做出真正创新性的研究来。
上述的种种制度性因素,要特别加上一点,那就是执掌科研资助权力的官员的任期制。
以行政官员主导科研资源分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倾向于在任期内取得成果,将风险留给任期外。
但真正的科学家,这一职业基本为终身制,所以在没有上述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下,更有可能作出长线判断。
首先要承认,世界上各个重视科技的国家,没有哪个像中国这么重视计划的,美国人会做很多计划,但包括美国科学院在内的很多预测和计划是智库行为,而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则是有组织的政府意志。
即便中国不断做出中长期科技规划,2020年之后又做到了2050年,但一旦具体到花钱和用人这两个环节,一定会祭出上述的衡量短期行为的参照标准。原因不外乎官员在任期之内希望获得显性成果,同时不愿意承担风险与责任。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很热衷于做计划,与目前主导短期行为的因素在逻辑上一脉相承:正是因为缺乏真正负责的人,所以同样缺乏信心(信心和责任真是高度相关);正因为缺乏信心,所以需要规划出来“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缺少的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经济待遇,而是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待匡正”的说法,就要更进一步,“我们真正缺少的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经济待遇,而是有没有条件让我们有正确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不过,普通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还是偏低的,特别是考虑到科研资源聚集的地方房价都奇高无比,这一点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优秀科研机构很分散,不少在生活成本很低但同时也很方便的小镇上。
作者为科学媒介中心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背景
2011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解析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于10月3日、4日、5日分别颁布了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揭秘免疫系统的激活密码
由于发现了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来自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的三名科学家布鲁斯·巴特勒(Bruce A. Beutler)、朱尔斯·霍夫曼(Jules A. Hoffmann)、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 Steinman)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免疫系统是人体和动物的“健康防御系统”,共有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先天性免疫,又叫自然免疫。当人体被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后,先天性免疫反应会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消灭“入侵者”。巴特勒和霍夫曼发现,人体许多细胞中都有一种重要蛋白质,这就是“toll样受体”(TLR)。它可识别不同病原体,并在细菌入侵时快速激活先天免疫反应,从而启动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适应性免疫,又叫获得性免疫。一旦先天性免疫被攻破,适应性免疫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斯坦曼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免疫系统的树突状细胞,这些细胞有着激活并调节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本领。
三位科学家的发现,对开发新型疫苗以及增强疫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清宇宙的宿命
“他们通过观测遥远的Ia型超新星而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而且逐渐变冷”。由于这一“震动了宇宙学的基础”的发现,美国人索尔·珀尔马特(Saul Perlmutter)和亚当·里斯(Adam G. Riess)以及持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布赖恩·施密特(Brian P. Schmidt)获得了201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Ia型超新星被科学家称为“标准烛光”,它是由像地球一样大、却与太阳等重的超致密老年恒星爆炸产生。这类超新星爆发时,产生的“绝对亮度”总是保持在同一个水平。
珀尔马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和施密特与里斯的研究小组观测了50多颗这样的超新星,发现它们的亮度比预期亮度更低——这表明宇宙膨胀正在加速。
宇宙的加速膨胀,暗示着宇宙正在“分崩离析”。这种演变被认为由“暗能量”推动,目前已知暗能量构成了宇宙的大约四分之三,但对于暗能量是什么,人们还知之甚少,这也是今天的物理学面临的最大谜题。
颠覆性的原子镶嵌图
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舍特曼(Daniel Shechtman)独自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其贡献在于发现了准晶。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家看待固体物质的方式。
1982年4月8日的早晨,舍特曼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一幅迷人的镶嵌图:它是规则的,但彼此之间又不是简单的平移对称。此前人们一直以为,在所有固体物质中,原子都以周期性不断重复的对称模式排列构成晶体,而这种重复的结构是形成晶体所必须的。
舍特曼得到的画面显示,在他的晶体里,原子并没有以简单重复的模式排列。这一发现在当时具有颠覆性,因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相关论文曾被学术期刊断然拒掉。然而,他的抗争最终迫使其他科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对物质本质的认识。随后,科学家创造了几百种具有多种组成和对称性的准晶。2009年,在俄罗斯的矿物样品中首次发现了自然生成的准晶。
诺贝尔化学奖的揭晓也为今年诺贝尔全部科学奖项的公布画上了句号。
本刊实习记者贺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