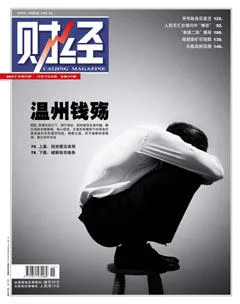天宫使命
2011-12-29孙滔
财经 2011年24期

9月29日21时16分,“天宫一号”在酒泉成功升空,这是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
“天宫一号”的主要任务为两个飞行器的交会对接。目标飞行器,即“天宫一号”首先发射升空;追踪飞行器,即未来发射的“神舟”系列飞船入轨后将主动接近“天宫一号”,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八号”为无人飞船,“神舟十号”执行载人飞行,而“神舟九号”是否载人,则依据之前任务进展情况决定。
中国于1992年确定载人航天三步战略。第一阶段载人飞船阶段已经完成,“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相继实现了载人进入太空,并且安全返回。第二步中,“神舟七号”突破了出舱技术。而前两步皆是为第三步建造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做准备。整个空间站的建设需要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这就要求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天宫一号”正是空间实验室阶段的成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对《财经》记者分析,要有效开发空间资源,就需要长期在轨的空间站,而空间站需要人员往返运输和货物补给。只有达到足够的技术成熟度才能突破交会对接,建立小型空间实验室,并最终建设空间站。
可以说,“天宫一号”正是中国未来空间站的雏形,它将展示中国要建成一个完全成熟的空间站所需的关键技术,完成中国所设定的在2020年建成空间站的目标。
少花钱多办事
目前,“天宫一号”已进入高度355千米的一个接近圆形的绕地轨道上,它将以自动模式运行,并受地面监控。它由实验舱和资源舱两舱构成,全长10.4米,舱体最大直径3.35米,起飞重量8.5吨。其中实验舱可容纳三名宇航员。
与飞行几天即返回地球的飞船不同,“天宫一号”是长期在轨飞行的载人航天系统,将在太空运行两年,随时迎接航天员驾乘飞船入住。
“天宫一号”可谓身兼多职,将分别与“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进行交会对接,还要完成空间科学和再生生命保障研究等空间医学实验,以便为将来建设空间站以及航天员长期驻留进行准备。美国和前苏联早期进行的类似发射任务则目的单一,仅为进行对接试验。对此,《国际太空》杂志编审庞之浩称,“‘天宫一号’少花钱多办事,确是一个创新。”
国际空间实验室类型并不相同。前苏联的早期“礼炮”系列航天器和美国的“天空实验室”可自主在轨运行,并可以多批次乘组执行多项科学实验。而欧洲的空间实验室只是实验舱,没有自主飞行能力,需搭载美国航天飞机,并由航天飞机向其提供能源、环境等支持条件。
“天宫一号”与早期“礼炮”号功能类似,只有一个对接口,可以短期载人。周建平分析,这主要是8.5吨规模限制所致。一个对接口使得空间实验室有很大局限,在载人飞船对接时就不能同时对接货运飞船,因此其资源补给能力有限,只能支持短期载人飞行。而将人员送至太空还应遵守一个准则,就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个载人飞行器伴随航天员身边,以便在意外发生之际,让航天员能够依靠载人飞行器安全离开。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朱毅麟对《财经》记者分析,以交会对接为主要目的的“天宫一号”设备不一定很完全,其工作时间、寿命、可靠性没有完全按照正式空间实验室的要求来做。“天宫一号”会在飞行两年后,再进行改进,以提高可靠性。真正的空间实验室可能是“天宫二号”。
对接如太空穿针
如果今年11月“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顺利,中国将是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完全独立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与美国和前苏联早期进行的交会对接试验不同,“天宫一号”可支持多次交会对接,减少发射次数。美、苏当时均以飞船和飞船对接,每次对接试验需要发射两艘飞船。
所谓交会对接,是指将宇宙飞船等航天器在空间轨道上连成整体进行轨道飞行。作为目标飞行器的“天宫一号”要调整到预定的交会对接轨道上,摆好姿态,等待交会对接。之后发射“神舟八号”飞船,“追”到目标飞行器后进行对接。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并不顺利。1966年3月16日,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手动操作“双子星座”八号飞船与无人“阿金纳”目标飞行器对接,但因人为扳错开关、造成姿控系统故障,对接后飞船猛烈滚动旋转,阿姆斯特朗不得不将两者分开。随后为确保安全,飞船紧急返回。
在人类进行的300多次交会对接中有10多次失误。庞之浩介绍,前苏联和美国由于交会对接经验不足,交会测量设备出现故障或对接机构出现问题,甚至还曾出现追尾。
交会对接技术要求轨道飞行器有较长在轨寿命,运载火箭入轨精度要求也高,同时交会对接过程也甚为复杂。未来“神舟”系列与“天宫”系列将上演异常紧张的求偶行动,追踪飞行器“神舟”系列飞船将在地面测控的支持下,经过若干次变轨进入到能捕获目标飞行器“天宫”的范围,这个距离约为15千米-100千米。之后,“神舟”需测得与“天宫”的相对运动参数,靠近至其0.5千米-1千米范围内。两个飞行器距离约100米时,其相对速度约每秒1米-3米,此时“神舟”需要利用摄像敏感器和接近敏感器精确测量两者距离、相对速度和姿态,同时启动小发动机,最后以每秒0.15米-0.18米的停靠速度与目标相撞,实现连接。
周建平将交会对接比作“在太空穿针”。尽管其中各个阶段都有风险,但最大的风险当属最后近程交会阶段,这主要依靠飞行器自主测量和控制的精度。
其原因是,由“天链一号”卫星、国内外16个陆基测控站以及三艘远望号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只能完成远距离导引,即地面只能测量其绝对位置和绝对姿态后换算为相对量,当两个飞行器距离较近时,测控网就无法满足其对精度的要求。同时,地面仿真模拟与太空中实际情况也有差距。
周建平分析,飞行器相对测量为高精度测量,空间环境对微波测量和光学测量有影响,如镜头对着阳光直射,光线很强之际,光学测量易受干扰。另外,真空环境、高温变化等,亦可能影响其精度和可靠性。
空间站未来
在低地球轨道运行的成熟前辈当属国际空间站,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耗资最多、研建时间最长、合作伙伴最多的空间站。国际空间站除欧洲航天局的“哥伦布”实验舱、日本“希望号”实验舱及加拿大提供的遥控机械臂外,基本上是由美国和俄罗斯两家的舱段、系统和设备所组成。
此前,中国曾多次提出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一直未果。朱毅麟认为,这首先是政治上的问题,因为航天技术是敏感技术,多与军事技术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反对声音很强。
不过,等到“天宫一号”与“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对接之后,中国将实现独立完成载人航天三大基本技术的突破,即载人航天器的成功发射和航天员安全返回、出舱活动技术和交会对接技术。之后,中国将建立自己的空间站,以期更有效地开发空间资源。
在初步规划中,中国空间站将运行十年左右。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公开表示,2020年之前中国要发射一个20吨左右的空间站核心舱,这个核心舱将与一个载人飞船、一艘货运飞船以及两个实验舱交会对接,整个重量100吨以下。核心舱需长期有人驻守,能与各种实验舱、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对接。
空间站舱段规模较大,需要更大的运载能力。但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尚不足,目前将卫星或者飞船送入太空并平稳运行的能力仅为10吨,而美、日等国均已实现20吨。中国正在研制的“长征五号”火箭,将作为将来20吨级空间站舱段的运载工具,而海南文昌在建的航天发射场,将承担这一发射任务。
对于中国载人航天的进程,庞之浩认为,中国在发展较快的同时,也顾及了国情与实力。受到技术基础限制,很多技术中国要从头做起。与前苏联过于强调循序渐进以至于常常重复试验、美国航天政策与政府更迭关系很大不同,从“神舟”系列飞船到“天宫”系列空间实验室,再到空间站,中国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较为稳步。
在载人航天设计理念上,前苏联过于强调继承,美国则强调新技术飞跃,而中国介于两者之间,风险也较小。
除了对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健康和工作效能进行深入研究外,建一个空间站犹如在太空中建一个家,需要继续发展出舱活动技术,以及大型空间设施的维修操控能力;还要为其提供多方面的货物补给,主要是人员消耗品、推进剂和维修配件、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和实验样品等固态、液态和气态物资的补给。周建平介绍说,其中,推进剂补给尤为精密,因为其他货物可以装载在货舱中,在飞行器对接后可以人工搬运,而推进剂则需要实现密封管道输送,将推进剂从货运飞船储箱转移到空间站储箱中去,其中牵涉很多技术问题。
尤令研究人员关注的是,与短期飞行器不同,由于长时间在轨运行,空间站需要实现最高效、可循环再生的生命保障技术。人类在太空中会产生很多废弃物,例如尿液和粪便,呼气和出汗等会生出水汽、二氧化碳等,考虑太空运输成本很高,这就需要一个经济的手段实现可循环利用,即需要电解制氧、冷凝水处理、二氧化碳吸收并还原出氧气、尿液处理等复杂设备和技术。
因此,“天宫”系列还要进一步验证再生生命保障、航天员居留和工作的医学问题等研究,同时还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如空间环境材料试验、生命科学试验等。按照计划,直到“天宫三号”,仍然要继续验证上述技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