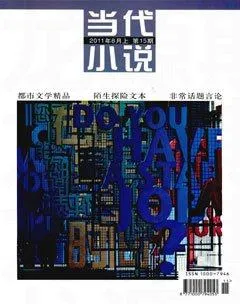老叶
2011-12-29于德北
当代小说 2011年8期
老叶是我早年的一个朋友,他在一所类似于职工大学的学校里教书。教政治经济学。他爱好书法,爱好泥塑,还爱好古董——所以,他喜欢别人说:“老叶是搞艺术的。”老叶家有一个大书架,上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书法方面的报刊、书籍,也有几件他的泥塑作品,当然更有“秦砖汉瓦”在那里偶露峥嵘。我认识老叶的时候,他已经快四十岁了,是“青书协”的理事,他戴一副平镜,头芯儿处有一块脱发——医学上称之“斑秃”。他说话时爱带儿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他爱人家在农村,后来考上了市内的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粮食系统辖下的一家小企业做出纳。我们这一帮人都不知道他爱人的名字,每次去家里见了,只叫她嫂子。嫂子是个实在人,不太爱笑,更不会听笑话,所以,我们从来不曾和她开玩笑。
说老叶写字,颇有家传,他祖上出过翰林,留下过笔迹,老叶最初练字,临的就是祖上的“帖”——有点像虞世南,字架匀称。
老叶学泥塑是自悟。
他自己讲,去过天津,去过无锡,见人捏小人儿,觉着有趣,就琢磨上了,三琢磨两琢磨便上了手,一捏,还有那么几分意思,就一路“悟”下来,悟出了自己的门道。老叶曾给我塑过一个“金身”,把我捏成个“金刚”,谁知,这个“金刚”进门没几天,就让孩子失手给打破了——不是老叶的手艺不行,是我的命承不住这个“金刚”之身。
泥人拿回来,妻子问:“谁呀?”
我说:“细看看,这眉毛,这眼睛,这胡子。”
妻子又看半天,依然没认出来,就自顾忙些别的事去了。
唉!人家老叶可是主动热情地给我塑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老叶收藏古董,什么宋纸呀,明纸呀,什么宣德炉啊,什么定窑的瓷器呀,吴越的古剑啊,总能遇到奇货,且不用花几个钱。老叶亲口对我说过,他用的一个砚台,是晚清一位写小品文的大家曾用过的,聚着格外的仙气呢。他自豪地说:“平时不敢用,平时不敢用。”又说,“用上这块砚,那感觉……”
那感觉一定不错!
我的手里,老叶的字很多。他写字爱拉大架儿——要么“铁马秋风蓟北,杏花春雨江南”;要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要么“大风起兮”;要么“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收的学生很多,因此,给他写文章的人也很多,他的学生介绍他,说他“真草隶篆”样样精熟,碑文拓片了然于胸,至于临的帖子,不计其数,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书法家。老叶家的嫂子,也是他的学生,虽比老叶小七八岁,但有了笔墨缘,想必日子也是十分融洽。
老叶的字,多半是行书,他在国内获奖的作品,也多是这种体。他得过一次国家级的银奖,得过几次省级的金奖和市级的“特奖”,在他书架里,除了书,除了泥塑和古玩,还有十几个证书,红色居多,绿色居少,常常给人一种绿肥红瘦的感觉。
老叶的书房叫“集雅斋”,他有一个别号,集雅居士。他祖籍是河南开封,所以,他有一枚章,刻的是“叶开封”,有时,他给人写字,落款也用“叶开封”这几个字,只是,落这个款的字不多,我的手里仅有三幅,另外,我在一家手擀面的牌匾上见过一次。
老叶时常出去讲书法,他讲课的地方多的时候有两三处,这里讲完那里讲,赶场子似的。有时讲不过来了,还安排他的学生代课,他爱人也替他讲过几场,据说效果还不错。有了这些课,他每月除了工资,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这可能就是他玩古董的资本吧。我没听过他的书法课,所以,对此不能妄加评说。
和老叶相交了五、六年,觉得他人不是坏人,但过于精明;学问一般,爱卖弄,有时不懂装懂,还特爱谦虚。这些总归不是大毛病,多多少少可以让人接受。
可是有一件事,使我渐渐地疏远了他。
就是古董的事。
我的一个邻居,做服装生意的,发了些财,就在市内比较好的地段买了房子。装修完了,觉得屋里少点什么。少什么呢?少点身价的象征。于是,想到了古董,想弄一个值钱的瓶子或罐子,摆在客厅里,制造一点雍容的氛围。
我带他去找老叶,向他说明情况。
老叶忖度了半天,才说:“好吧,我让一件出去,谁叫咱们是朋友呢。”
我和邻居都很高兴。
老叶从床下拿出一个纸包纸裹的大瓷瓶,指着瓶口有一点残缺的地方说:“万历的,不太值钱。”
我的邻居多少有点历史常识,千恩万谢地出了一个老叶满意的价格。
老叶说:“如果不是收的时候花了钱,您就拿去玩玩算了,放谁那不是放呢,真不好意思。”
邻居千恩万谢。
一年后,偶然的一次机会,邻居认识了雅宝斋的一位老师傅,于是求他来家里给鉴定鉴定。谁知,那个师傅只看了瓶子一眼,就说:“这个呀,叶老师找我鉴过呀,是民末的仿品,他怎么说是万历年间呢?开玩笑吧!他一定是送您的,不可能收您那么大的价钱。”
听了这件事,我十分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