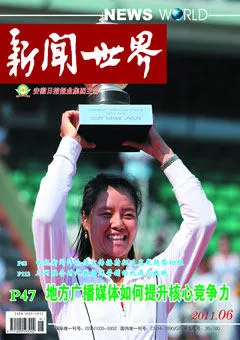从《大公报》看民国传媒公共领域构建
2011-12-29赵传芳
新闻世界 2011年6期
【摘要】新记《大公报》秉承“四不主义”原则,发挥着媒体所特有的公共话语权的作用。它的一些理念和实践对当今新闻界有哪些启示?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公共领域 《大公报》 传媒 特色
1926年-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时期,也是《大公报》百年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在天津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提倡“文人论政”,经过众人苦心经营,新记《大公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大报。
其办报理念在当时更是有较大的影响。1921年9月1日《大公报》续刊号上,总编辑张季鸾以“记者”名义发表《本社同人旨趣》,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决心使《大公报》成为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党派,不求一己私利,不以言论做交易,不随声附和的独立报纸,它标志着中国民营新闻事业经营理念的成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大公报》迅速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报。
现在看来《大公报》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早期的咖啡馆、沙龙等等公共场所之上,而作为中国的公共领域却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有人说中国社会没有公共领域,这种看法是基于将哈贝马斯的理论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国,发现契合之处甚少,所以就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走不通。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形成了,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是公众、公共话题、公共意见这三个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西方列强的入侵瓦解了传统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现状,同时也俘虏了中国的政治当权者,在这种情况下,探寻国家前进的道路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责任,《大公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和发展的。在《大公报》的历史上,其公共话题是国家的命运和公民的利益,并以“四不”方针为准则。可见《大公报》强调报业独立于政治势力,努力成为公民的独立舆论机关,沟通社会各界,形成公共意见或者是形成舆论压力对当权者制造压力氛围。在实践上它对北洋军阀、国民党进行了批判,对劳苦大众的凄惨生活也做了悲天悯人的报道。中国文人确实是想借助于《大公报》这样一个公共媒介打造传媒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整齐划一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只有脱离了封建社会才能拥有人身自由,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开始积累并拥有物权,才能给公共领域提供这样一个经济保障;公共领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者是大众的权利,并且形成这样一个团体对国家或当权者进行质疑和批判。其中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基于臣民和公民这两个概念的比较形成的,其划分标准是物权和人权的情况,处于初级的臣民社会是民众物权和人权都不具备的社会,中级的市民社会是民众拥有财产权而没有政治权的社会,而处于高级形态的公民社会是民众拥有财产权和政治权的社会。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种开放的公共领域并进行讨论,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社会都是一个金字塔的阶层模式,臣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都是掺杂在一起,不可能出现整齐划一的形态。特别是在中国的民国时期,《大公报》的名记者,在张季鸾、胡政之以下,有曹谷冰、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费彝民、萧乾、王文彬、徐盈、李纯青、孟秋江、彭子冈、杨刚、李侠文等,他们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使得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有关国家前途和民众利益的讨论当中,所以公共领域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或者说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和能力参与公开讨论的,而这种限制不是人为的限制,而是社会划分的结果。也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只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利用报刊这一公器批判社会,推进社会的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精髓在于其批判性。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聚集的领域,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公共领域本身就是由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也就是说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生命力所在。《大公报》是具有批判性,但是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它的批判是建立在一定的立场之上和一定的范围内的。
提到《大公报》的批判性,就必须提到张季鸾著名的“三骂”。1926年12月4日张季鸾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1927年6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痛骂蒋介石不学无术,身为总司令的他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之际竟在后方散布没有美满婚姻就不能使革命进步的怪论。社论中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些社论犀利透辟,但是张季鸾或者说《大公报》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立场不会变,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言论渐渐有亲蒋倾向。如“九一八”以后发表过“缓抗”社论,支持蒋的不抵抗运动。也就是说《大公报》在发挥批判功能时有一个批判的标准,对于各个派别或者是各个政党的批判不是一味的,而是基于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自己所处的阶层,《大公报》是隶属于资产阶级的,所以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所提出的批判都是基于在方向上认同的基础上的,不是毁灭性的,而是建议性的。对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是留有余地的批判,并没有对公权力进行挑战,一切都只是在有限度内的进行批判,但同时也要保存自己,这也是《大公报》的生存哲学。但是不管批判与否都是建构在爱国这个主题之下的,救亡图存是《大公报》的立场。
《大公报》积极发挥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一则讨论公共事物,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二则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
中国新一轮的媒体转型正在进行着,如何让媒体成为不仅是发表新闻的机构,而且成为公共意见的载体,发挥着媒体拥有的话语权的作用,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是值得业界人士思考的。目前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有着公共领域弱化的表现,表现在舆论监督类节目减少,娱乐性质的内容增加,公共讨论的平台上多种意见的缺失,以及新闻被商业力量所摆布。
《大公报》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值得推崇的地方有很多。首先是对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在“救亡图存”这个时代主线下开始设置公共议题,开始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立了媒体公信力。其次是组建一支人才队伍,《大公报》内部人才济济,有一批赫赫有名的记者,他们每个人都为《大公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从商业的范畴来说《大公报》作为一家公司,胡政之的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尊重人性的管理方式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无疑是给知识分子莫大的精神上的鼓舞,报社内部的和谐的环境,更是对其公共领域的构建起着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大公报》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大公报》的公共领域的构建是基于能够存活这样一个基本底线的基础之上,它必须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就是说《大公报》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的生存哲学。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下构建了传媒公共领域,发挥其话语权的作用,其中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当今社会构建媒体公共领域时,对《大公报》的审视,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②方汉奇、陈业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③周占武,《新记大公报公共关系研究》[D].暨南大学,2003
④黄钦,《解读新记<大公报>之传媒公共领域建构》[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6)
⑤郭奇,《把媒体打造成公共话语平台——解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传播学》[J].《协商论坛》,2007(1)
⑥彭立群,《从“思变”到“变思”——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嬗变》,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
-HQDX200702003.html
(作者:安徽大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