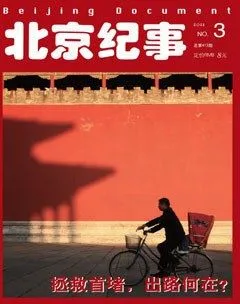谁动了我的停车位
2011-12-29九儿
北京纪事 2011年3期


前不久,有个同事问我:“你知道网上有卖地锁的吗?”我一头雾水,说:“地锁?你要那玩艺儿干吗啊?”“哎哟,你可不知道,现在我们小区抢停车位都抢疯了。”同事火急火燎地接着说,“这两天我上班都是坐的公交车,为什么啊?只要你刚把车开出来,立马就有人在你的停车位安地锁。所以现在院里,不安地锁,车谁也不敢开了。”我很不以为然,说你安了也没用啊,到时候物业都给你们拆了。同事呵呵一笑道:“我那房30年前的,哪来的物业啊!”
停车难,难于上青天
北京的机动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2300辆,1966年发展到2.8万辆,1978年,机动车拥有量也只有7.7万辆。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发展,1997年2月,机动车达到了100万辆,此后北京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07年5月26日,北京市机动车突破300万辆,户均拥有0.68辆,这标志着北京进入了快速机动化的“汽车时代”;2009年12月18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大关,达到4001426辆,驾驶员达567.9万人;截至2010年9月6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50万大关,达到450.3万辆,驾驶员达到609.4万人。
北京的老百姓个个都作好了准备,进入汽车时代,但似乎我们的交通配套设施还有些反应“迟钝”。一些老司机应该深有体会,原先开车出门办事,也就是一些商业区、旅游区汽车位难找;可现在您开车回家,竟然发现自家门口停车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笔者曾经和广安门外某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聊过一次小区停车难的问题。这个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所建,院子里的停车位不过二十几个,但经过居委会统计,小区拥有汽车的人已经超过百人。这些有车族曾向居委会提议:适当缩小院内绿化面积,把花坛拆掉改建停车场。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小区里老人们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第一,这些老人根本就没有车,所以停不停车与他们毫无关系;第二,小区绿化带里有很多植物都是老人们亲手所栽,有些树已经在院里长了十多年,不可能被铲走。两边的人居委会都不敢得罪,问题也只能就此搁置。居委会的大姐和我说:“院子里停不下就只能停在外面街道了。现在我们这街道两边全是车。”笔者特意站在街道中间望了一望,虽然现在才下午4点不到,但街道两边已是一个接一个首尾相连停了满满两排车了,这两排车就像两排整齐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的尽头,汇成了一个交点。居委会的大姐告诉我:“这还不是这条街最‘辉煌’的时候,你晚上9点多来就会发现,这里要停三排车,两车相遇根本没法会车,街道都变成‘胡同’了。”
我的一个朋友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多年,虽然小区有物业,但仍然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停车位依然是稀缺资源。他曾经去小区物业问过管理小区车辆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每个月交80元管理费,就可以停了,至于停哪,你自己去抢,抢到你就停,抢不到你就自己想办法找,这么大的小区肯定能找到停的地方。我那朋友就问了:“交了80块还不管你有没有地方停,那我交的钱是管什么的呢?车子被碰了、被划了你们管吗?”得到的答案就两字——不管!
似乎只要小区里有足够的停车位,在自家门口停车就不是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困扰着有车一族。拿笔者所住的小区为例,2000年以后的房子,停车位200多个,满足本小区的停车需要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因此院里停车就没有人管,院外附近又有两座写字楼,白天小区的人开车上班了,两座写字楼的“白骨精”们蔫不出溜地把车停了进来。一般写字楼一个月的停车费都是300元起,这下他们省了。可这些“白骨精”又好加班,7点多了也不回家,这可苦坏了我们小区的人,只能无奈地把车停在院外头等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下班回家发现院里车停得满满的,就只能停在外面,可他偏偏又不放心,总觉得把车停院外头不安全又有可能被“贴条”,7点多吃饭了也是吃两口就去窗边看看。咦——正好有个“白骨精”下班开车走了,他赶紧撂下筷子,下楼挪车去。看着父亲的背影,有时候觉得,哎——停个车咋就这么费劲呢?
“圈地运动”来到我家
“抢车位”原本是风靡网络的一款网页版小游戏,但现在这种“游戏”从虚拟走到现实。我原本以为,之前同事和我说的“圈地运动”只是个案。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相邻的两个小区的地锁已然遍地开花,我才觉得“抢车位”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果不其然,周日早上我睡意正浓,就听楼下“嘻嘻嚷嚷”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怎么了?有人打架了?我探着脑袋鸟瞰,密密麻麻的一群人都是小区里的,他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人群的中心有个工人模样的人,手拿电钻,钻头朝下打着地砖,工人旁边有个东西特别扎眼——竟然是地锁!
“爸、妈,咱家也开始抢车位了⋯⋯”说完了,没人回应,才发现他俩早下去了。笔者小区最先发起“圈地运动”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家住一层。小伙子很有心眼,为防止安完地锁后有人“报复”他的爱车,他先在自家一层的墙上安了个摄像头,然后联合几个年轻的车主发起了“圈地运动”。小伙子说话有自己的一套:“小区没物业,尽是外面的人进来停车,我们住这的人倒没地方停车,这地锁你说该不该安啊?”当然小区里也有些车主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的车都停在院外面,吃不着葡萄只能先说葡萄是酸的。邻居家老王就是,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里来回踱着步子,他车停在院外面了,自家院里的人风风火火地抢车位,没他的份,他能不急吗?一会儿他媳妇也从楼上下来了,他叫她在院里等着、看着,一旦有周末串门的或是什么其他原因开车走了的,就打手机叫他,他现在去院外找他的车,在车里等她的信。小区里像老王这样的人不下10个,他们都等着、盼着,希望有人开车出门,他们好当这个替补。我们家还算幸运,车停在了院里头,看着这吵吵闹闹的场景,我问我爸:“爸,咱家也安地锁吗?”我父亲眨了眨眼,说:“大家要都安,咱们就安吧。”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洪洋介绍,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泊位总数之比最低应为1∶1.2,其中居民自用车位满足率应该达到100%,即“一车一位”。在此标准下,车辆停泊才不会对交通运行与城市管理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车位供给无法达到这一标准。
不久前,吴洪洋对我国15个主要城市中心区的停车泊位供应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显示,除厦门外,没有一个城市的车位满足率达到80%。不仅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无法满足“一车一位”,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的车均拥有泊位率竟然还不足25%。
如何解决停车难问题
停车问题是城市交通发展的瓶颈之一,它既受制于城市交通的发展现状,又反过来影响着城市交通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认为,应把停车设施建设与管理作为动态交通需求调节的有效手段给予高度重视。
“解决城市停车问题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的一部分,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吴洪洋表示,一是根据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尽快修订规划与建设标准,保证居民自用停车的刚性需求;二是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加强部门协调,尽量挖掘类似城市广场、路侧停车和单位的公共车库等可利用资源,也可尝试错时借道停车,提高道路利用率,扩大车位供给能力。如果前两项都没有起到作用,就必须用价格杠杆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提高车位利用率。
提高收费就能解决问题吗?北京提高重点区域收费后,表面上该区域地面停车需求减少。殊不知,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免费停车攻略”在网上热传,车流涌向周边区域,造成了这些区域的车位高度紧张。上海南京西路、淮海路、徐家汇等繁华地带的写字楼车位月租都在1000元以上,有的高达2800元,结果上班白领将车停在周围体育场、小区,造成了重点区域停车位“里松外紧”。
针对这一情况,吴洪洋表示,收费管理的精细化,车位管理的动态化、信息化,正是相关部门亟须研究的课题。价格杠杆不是单纯的涨价。哪些车位涨价、哪些区域涨价、涨到什么程度、价格如何回调,都应该依据不断变化的车位供需关系而不断调整。
首先,政府应该进行出行选择的经济影响评价。2006年吴洪洋在成都作过类似调查。当停车费从1元涨到5元时,18%的受访人群选择放弃买车。可见只要使用成本提高到位,就能达到需求侧管理的目的。
其次,对于价格手段应该更精细化,并对车位供需变化实行动态监控。在新加坡商业中心停车,第一个小时收费很便宜,此后每小时按大比例递增,停得越久越贵,提高了车位利用率。在香港,商业区的停车价格按供需关系浮动,车多,价格上浮,车少,价格降低,从而调节供需。在伦敦的商业区,以拥堵点为圆心,以不同半径画圆,停车价格逐层递减,防止了车流向拥堵点周边区域聚集。
而目前,国内一些城市的停车收费仍处于“停多久都是一口价”的水平。一些城市繁华地段的停车资源在收费提高后大面积空置也没有及时降价引流,这些僵化的、粗放式的管理,显然都不利于盘活停车资源。
此外,精细化的停车管理离不开信息化与产业化的支持。随着信息化、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停车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城市车位信息与价格联网公布,哪里有车位,哪里价格更低,车主可随时查询。“这将有利于停车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减少人们开小汽车出行的盲目性,降低停车的难度,减少由此造成的交通拥堵与违章。” 吴洪洋介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私家车出行要先用电话或网络预订目的地的车位,出行无车位将遭遇高额的罚款。
专家们一致认为,解决“停车难”还是要立足长远,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运输,提高替代小汽车出行方式的服务水平,使人们自觉调整出行结构,减少车位需求的无限增长。
编辑/韩 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