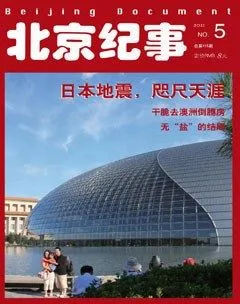吹糖人儿
2011-12-29北京爷们儿
北京纪事 2011年5期
北京的老行当灿若星辰,就像这遍布四九城的胡同,数也数不清,伴随着六朝古都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历经数百年。那魂系市井胡同,京腔、京韵的吆喝,再配上不同的响器,声声不息,一代又一代地传诵着。其间也有因时代的需要而演变的,吹糖人儿的便是其一。
吹糖人儿的敲一面小铜锣儿,声音清脆而紧凑。据说此行在唐代就已盛行,那时的糖稀中含有一股特殊的香味,糖人放在印模中制成,所以小贩都吆喝“香印”。到了宋代,赵匡胤做了皇帝,“印”“胤”同音,为了避讳,只好以小铜锣来代替吆喝啦。吆喝虽然变了,手艺没变,肩上的挑子没变。
挑子一头是个带架的长方柜,另一头是半圆形开口木笼,里面卧个熬糖的小炭炉,炉上置大勺,用文火把蔗糖熬成棕色的糖稀,上端木架分为两层,每层都有很多小孔,为的是插糖人。吹糖人儿的肩挑货担,不走大街,专串小巷,足迹几乎遍及四九城的小胡同儿。每人则往往有自己的路线,到点儿准来。有些孩子一到钟点,就盼着“当当当……”的锣声了。
挑担人等这帮小孩子们聚得差不多了,撂下挑子,慢条斯理地用一柄中空的短芦管,一头蘸上点热糖稀,在空中反复摇晃,待其稍凉,迅速放在涂有滑石粉的木模内,用嘴衔芦管徐徐吹制。不一会儿打开模子,一只腹内中空、活灵活现的小动物就出现了,有小熊、金鱼、耗子、公鸡等等。吹糖人儿的拿出竹签儿,按上去,然后再插到木架上的插空里一排,迎光看去,金黄透明,煞是可爱。
孩子们见着就走不动了,沉不住气的都动了心,纷纷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钱,买一个现成的。实在没钱的也不肯离去,眼巴巴地盯着这些糖人。这时,小贩就用上了拿手绝活“猴拉稀”:全凭手艺,用芦管凭空将糖稀吹成一个小猴,立在小苇子杆上,中空的猴肚子透明,从猴背上敲一小洞倒入糖稀,再在猴屁股上扎一小孔,让糖慢慢地流出来,下面用一个小江米碗接着,用耳挖勺大的江米勺舀碗里的糖稀吃,直到糖稀流完,则连孙猴以及江米碗、勺一块吃掉。
一股诱人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
孩子们最后的防线崩溃了,纷纷举起积攒好久已经汗湿的零用钱。这不包括我,能求的都求遍了,最好说话的姐姐们的私房钱,也基本被我搜刮净了。还好,那时候可以不必用钱来买,而是用牙膏皮来换。两筒牙膏皮可以换一个小糖人,孙猴要三筒牙膏皮。吹糖人儿的总能见,牙膏皮难攒,一筒牙膏要用很久。我眼瞅着三姐把牙膏皮从下至上卷过去榨出最后一滴,这才归了我。您说,我容易吗?所以我手里偶尔会有一个牙膏皮,换不了小糖人,孙猴更没门儿。
没钱有没钱的法子。我只好把目光投向了“转糖画儿”,搁现在就是轮盘赌,也叫撞大运,以小博大。每个摊子都配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红漆方盘,沿其边缘彩绘鸟兽鱼虫于大小不一的格子,它们也各有含义,如鲤鱼预示“鱼跃龙门”,花篮代表“花团锦簇”等。出钱(仅需一筒牙膏皮)就可拨动转盘正中的竹制指针,待它飞转后停在哪格,便可得到这格的糖画,如指到空当处,得,白忙活,浪费了难得的“赌资”。转糖画儿的最高境界,是转到一条龙(相当10筒牙膏皮)。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的悻悻离开,我终于收获了一条龙!满心欢喜地看吹糖人儿的“运勺如风”,用小铁勺,趁热舀出少许糖稀,然后在一块光滑如镜的青石板上淋出条腾云驾雾红彤彤的龙,最后用一根竹签放上一按,齐活儿,图案与竹签就粘在了一起。
举着这条亮晶晶、甜蜜蜜的好运龙,我在小伙伴们中间别提多显摆了。举着给这个看看,给那个瞅瞅,那小头儿昂的,激动的小脸儿红扑扑的。
慢慢的,那糖龙凉了,不小心还会蹭个洞。到这个时候,总是自己舔一口,然后伸向最好的伙伴儿,让他也舔一口,围在身边的,都是最好的铁哥们儿,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最后那竹签头儿,噙在我嘴里,直到满嘴竹子味儿了才舍得扔。
现在庙会上还能见到糖人,只是再也闻不到那股诱人的甜香了。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