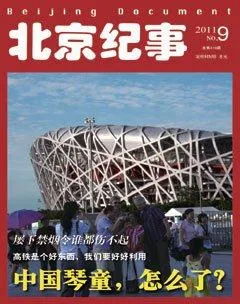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及人的精神内核
2011-12-29易明
北京纪事 2011年9期
《北京日报》2011年6月29日刊登北京壮景之二,一幅涵盖了故宫、人民大会堂及相邻的国家大剧院照片。看似风格迥异的三种建筑文化,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线索。与往东的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往西的中南海等,构成我们民族最宏大的首都文化气场。
平时就人流滚动,七八月望去更是一片人海。倒退30年,广场是可以练自行车的,而现在走着都费劲。毛主席纪念堂一直是免费,等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怨言,光站在那儿就会融入强大的气场。当年,我曾参加过修缮纪念堂旁边公共厕所的劳动,幸福得忘乎所以,想想修故宫、大会堂、大剧院的工人,也一定有着不可复制的精神优越感。一幅临空拍摄的图片,解答了很多次站在广场的思考,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它给予的影响。同时,我们相信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穿越历史。
第二幅照片是昆玉河,图中略微成弧形的河流,不长,如梦里的江南水乡。这让居住在北京的南方人多了几分亲近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人背山临水而居,阴阳合一,繁衍生息。5000年,黄河子民几次南迁西行,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及海南、西南等。去江南就离不开水,现在福建、广东还有终其一生在江海船上的“民”,人数已经很少。
有意思的是,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新中国,南人又聚集到北京——北方的这块风水宝地。现在有火车飞机汽车,古人行路方便舒适就是船,沿着已经消失的京杭大运河北上。这让我们想起了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当年引昌平白浮泉到积水潭三海,走的就是昆玉河的前身高粱河。运河行船安全,就是慢。不像现在的高铁,充满高科技含量,创新需要突破,系统需要稳定,看似矛盾。“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错不在技术,而在世人浮躁的心态。发展需要速度,速度需要安全,安全需要发展,相互间没有绝对冲突,而是力量的平衡稳定。科技领先会产生真正的国力竞争力,出口贸易才会不廉价、不吃亏。
说水有一种自然启示,好多人都会重复老子的话,咱就不啰嗦了,只讲现实的事。昆玉河开挖于上世纪50年代,50米宽,西北连接颐和园昆明湖,东南与过去的八一湖现在的玉渊潭相通。以前两岸是土堤,水草丰沛,据说能吸引来白洋淀的渔民(今年有白洋淀人到王府井金街做旅游宣传)。昆玉河是北京目前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达到2〜3级,并被列为一级水源保护区。但两岸分布着数十个雨水口,其中,车道沟桥南侧以西至玉泉山之间数公里范围内的雨水,由于未实现雨污分流,周边单位和小区的部分污水会越过污水管线和雨水管线间的截流坎,通过雨水管线进入河内。
下雨本是龙王爷的恩赐,比如北方人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南方人叫吃天水,这好事怎么就变坏事啊。7月24日,北京下了今年最大的雨,相比6月23日的雨灾,全市可谓应对有序。刘淇书记提出:要将雨水收集纳入地方立法,指出立交桥尽量减少下挖式设计。这都是治本之道。现成的范本,如报上说北海团城600年不旱不涝,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集雨工程,相信是有科学的含量。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就记住了,水利是国家的根本。
与水关系密切的建筑就是桥梁,古人把修桥铺路视为善举。桥在地方的是一座碑,要代代相传。像赵州桥,成了世界名桥,进了我们小学课本,听孩子们一读,都勾起儿时的往事。60年代进北京,过长江,火车要乘轮渡,看正在修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难得的风景。回福建过了杭州钱塘江大桥,就觉得离家乡不远了。赵州桥1400年,南京长江大桥43年,钱塘江大桥74年。记一段钱塘江大桥之父茅以升的回忆录:
1933年春天,我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请我赴杭州,在钱塘江上兴建一座现代化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做“钱塘江造桥”——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破坏力量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冲即被涮走。江底石层上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人们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我想,建设厅长曾养甫邀请我来杭州造钱塘江大桥,分明是要我做不可能成功的事。究竟能不能成功呢?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我作出一个结论: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从科学上看,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相信科学,还要善于利用科学。
1935年,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曾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界人士听说后,也想不再支付贷款了。曾养甫当时已调任铁道部次长,把我找去,厉声厉色地对我说:“如果桥造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跳!”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我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我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我们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力量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
以上摘自《奋斗——科学家的成才之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说这些的缘由是网上热议“桥坚强”——钱塘江大桥。桥设计之初,时速20公里,荷载铁路面轴重50吨、公路面15吨。当时,平均每天仅有150多辆汽车、4.9对火车通行。70年过去了,在这座桥上,动车可以跑120公里、汽车跑100公里的时速,汽车40吨、60吨照样走。一天汽车一万辆、火车150列,没事,说明质量真的过硬。茅先生,生于1896年,江苏省镇江人,1916年唐山工业学校毕业,清华官费赴美留学,1920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
上世纪70年代,我见过老人家,很是自豪。茅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造成的桥,就老呆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它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负担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伤’,就乐于接受”,“有时桥还在,但下面的河却改道了,或两头的山崩陷了,连山河都未必能和它相比”。
茅老您是说桥还是说人。
伟大的建筑师,是百姓的福音。看方庄住宅小区这张照片,20多年了,还是那么漂亮、宜居。中间圆形的高楼,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烂尾楼之一,听说终于有人接盘,高兴。因为曾经居住的房子阳台天天对着它,看到它有生的希望,我们的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乐观坚强,就是我们的精神内核。
(编辑 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