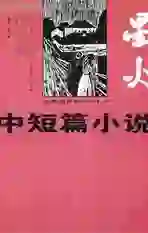小姨的外遇
2011-12-29刘半园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1年3期
“你老姨回来,可不让她再走了。这鸡鸭狗猪的,我一个老太太可侍候不了。跟人家学出外打工,也没看见拿回来几个半子。”姥姥用她那不利索的牙咬着半青半红的柿子唠叨着。她满口剩下不到十颗牙,后面的大牙又活动得不成样子,她在吃饭的时候还故意把牙用舌头一顶,一颗牙齿在嘴唇上倒出来似的让我们看。无论是她吃东西还是说话我都能感觉到牙在她嘴里哐啷啷的声音。要她去补,她又舍不得钱,说是活不了几天了。这几天在她嘴里一说便是五六年。
“妈,妈,快来帮帮我。”没见小姨的人,便听见了她哨一样的声音。我和姥姥出去迎她,小姨身上穿了条新牛仔裤,我猜得一百多块钱。
“小姨,你这裤子挺贵的吧!”我拎着小姨买回来的苹果,边走边问。
“老姨就老姨,还小姨,听起来都不顺耳。”姥姥耸着她那张布满岁月痕迹的脸。
“呵呵,嗯,新买的。一百二!”小姨显然满脸得意。
小姨的屁股可能是刚粘到炕沿,姥姥就挎起了她的小包袱说是这就走呀。小姨最了解姥姥的脾气,她若是打定了主意,是谁再说什么也没有用的。
姥姥八个孩子,小姨是最小的一个。在众多姨姨舅舅里我和小姨是最要好的。在外人眼里我们不像是姨姨和外女,更像姐妹或者朋友。小姨一米六八的个子,典型的东北女人。她爱用粉饼,让本来就白皙的脸看起来更加地诱人。小姨涂粉色的口红,她长着樱桃似的小口。和村里的同龄女人相比。小姨显得年轻好几岁。小姨的脸上没有被黄土刮过的痕迹,手也没有被镰刀磨过的钢锈印。小姨说她讨厌她的单眼皮,一心想要割成双的去,有一次都到了医院门口却因她怕疼而退了出来。我倒觉得她很适合单眼皮,薄薄的单眼皮上涂上淡蓝色的眼影,很是可人。我很喜欢和小姨在一起呆着,所以基本上每个假期我都是在她家度过。
村里现在流行外出打工。这种流行像浪潮一样越翻越勇,把小姨的心也翻得不安生了。这次她跟隔壁的李大头媳妇一起走的,说是找了个饭店刷碗的活。从小姨这次回来的表情和打扮来看,她这工是打得好了。
“小姨,在外面活干得咋样啊?我姥可烦人了,她家也没啥活她就是想回去玩,和那群老太太看牌。”
“呵呵,我还不知道你姥,这么大岁数了随她去吧。你看。”小姨说着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个手机来。
“啊,小姨,你都买手机了?可贵呢吧。”我拿过来把玩着。“呀,摩托罗拉!我同学他爸用了一个,得你一个月工资呢吧?”
“我这个是二手的,没有多贵。你放多少天假啊?”
“四十五天。对了,我姥把黄瓜籽柿子籽都买了,让你回来种呢。”
就在我们聊得正起劲时,小姨的手机响起了刺耳的铃声。小姨看了看来电号码,拿着手机转身去了外屋。电视声夹杂着风声我听不清她在电话边说什么。再次回到房间的小姨异样的笑容挂满了整个面部,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翘。我问她是姨父打来的吗。她告诉我姨父还不知道她有手机呢。
春天里的柳树发芽了,春天里的小路变得泥泞了。春天里的蚂蚁搬了新家,春天里的人们开始播洒希望了。
小姨换下了新买的牛仔裤,穿上了穿了几年的蓝裤子,黄胶鞋。像其他妇女一样戴起了三角巾,举着二尺勾勾着那她再熟悉不过的土地,迈着她那迈了许多年不尽相同的步伐。
小姨干起活来非常地利索,一会功夫就把地勾得垄是垄帮是帮了。她又拿起锄头在垄上铲出一个个小坑。再打来几桶水,在坑里洒上些水,最后把菜籽一粒粒地埋在坑里。见她收起围巾抹着脸,就知道她要收工了。
“小姨,你手机响啦。”我的声音或许还没传到她那里,只见她撇下拿在手里的围巾,大踏步地跑过来。想掩饰却又掩饰不住的期待。
“哪响了?”小姨望着那哑巴似的手机,埋怨似的望着我。
“该是短信的铃声。”
小姨转脸迅速打开手机,伸手解开了领口上的一颗扣子,屁股一歪侧坐在炕沿上。她按着手机键盘的手背上还留着些许的泥点,可以看出她丝毫没有注意这些。全神贯注地投入在手机上。
“小姨,是谁呢?”我瞪大眼睛望着她一下不眨。
“一个同事。”小姨显然是在躲避。
“小姨,是谁呢?”我的眼睛依然不眨。
“哎呀,都说了是同事了。”
“切,我会信。”我的眼睛随着头扭转了方向,望向蔚蓝天空中的一朵浮云。
姥姥家很穷。虽是那个时候没有富人,但和同村人相比姥姥家生活得更加拮据。姥爷有气管炎的病,什么重活也干不了。一年到头地在炕上躺着,还要不停地打针吃药。下地的活就全都交给了姥姥,说起姥姥也真是不容易。记得母亲和我讲有一次姥姥家里的粮食所剩无已了,姥姥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上一些,自己躲在外面吃灰菜。后来脸肿得像个猪头,脚和胳膊也肿得锃亮。那些灰菜显些要了姥姥的命。
在那个时候女子是不招待见的。为了给小舅舅娶媳妇,小姨十八岁便被嫁到了姨父家。我曾问过小姨是否喜欢姨父,他们可曾谈过恋爱。小姨讽刺又无奈的表情我是不会忘记的。她说,喜欢?谁管你喜欢不喜欢啊,家里着急给你老舅娶媳妇,让嫁就得嫁。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恋爱不恋爱的。过日子呗,就是过日子。哪像你们现在,年纪不大就开始处对象。我们那时候要是被发现,腿不打折了才怪。可以看出在关于恋爱或是感情的事情上,小姨心存遗憾。
“你咋回来了?”正在背地的小姨望着行李袋、头发上尽是黄土脸上淌着汗渍的姨父。
“别提了。工头都跑了。”姨父把行李卸下,用手抹着脸。坐在院内的土墙上。
“啥?咋回事?”小姨撂下手里的镐头,走向姨父。
“眼看着要完工了。大伙都乐颠颠商量发钱的事。”姨父点起根一块二一盒的达西烟。“工头跑了。事后我们想想,早发现这工头不对劲了。哎……”姨父拍着自己的大腿,发出连连叹息。
“那,那这活就白干了?你们找去啊。你们合伙找去啊。”
“找,人家是跑的。让你找着,让你找着那叫跑吗。”
姨父是和同村的男人一块出去打工的。在一个工地,做些推车、搬水泥、递砖头的活。去的时候讲的是一天四十,现在倒好,一群男人战败的公鸡一样垂着头回到自家的土炕上。三个月的汗水就这样自流了。
包工头携款逃跑的事常有发生。东头陈有才去年干了六个半月,说是半夜有人看见工头携着包坐小黑车跑了。包工头,黑着呢。想方设法地把人骗去吃苦卖命。开始时给些甜头,干半个月就给大家发些钱。这样便稳定了人心。工程一大半以后,人们便开始要钱。工头找着各种各样的说辞不给发。人们又不愿让以前累白挨,只能忍着盼着。结果,还是落个空。
“生子不是说这包工头他认识吗?说保准没事的啊!”小姨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想起生子。
“狗屁。他认识,他认识个鸟。他认识泥瓦匠,泥瓦匠认识木工,木工的大姑的外甥的邻居认识包工头。”姨父的一只裤腿挽得老高,用鞋使劲泯着烟头。
两口子都蔫了的茄子一样在自家墙头上坐着。火辣辣的日光照着姨夫那无奈委屈灰土土的脸。和小姨同岁的姨父此刻苍老了许多。
小姨猛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拍大腿。叫姨夫去生子家看看,别是生子一个人拿到钱了,别人不知道。
待姨夫走后小姨转身进屋,拿着手机递给我说:“这手机,你姨夫若问起来,你就说是你的。听到没?”
“啊?”
“啊啥啊,他钱没拿回来,白干了三个月。要是知道我买了个手机,不心疼死他啊。”
“哦。那来电话找你呢?”
“全挂全挂,不接不接。哪有那个心思了。哎……这累就这么白挨了,这些挨千刀的工头。妈了个x的,都是车撞死的货。”小姨愤愤难平。
一场春雨过后地里的菜籽发出了嫩绿的芽。小姨的手机放在了我这。我给挂了几个来电以后,便不停地传来短信铃声。
被骗也就骗了。生活还得继续。
邻居杀了个猪叫姨父喝酒去了。小姨向我要去了手机。她的表情随着手指的翻动速度而变化。一会满脸歉意,一会害羞似的低下头,还小声嘟囔着什么。最后把手机搁在大腿上,长长地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望着落下去的半边夕阳。
“去过澡堂吗?”小姨问我。
“没。”
“过些日子,我带你去。那里面特别有意思,人们全都脱得光光的。搓澡时,一个个地躺在那,和案板上的猪似的。”小姨边说边捂着嘴笑。
打了酱缸,浇了菜园子。告诉姨夫中午别忘了给猪添食,给狗喂点水。小姨拿了洗发精,香皂,毛巾,乳罩和内裤,这就带我去澡堂。
“你在这洗,慢慢洗,洗干净了。再搓个澡,我把钱给交了。”小姨嘱咐我。
“那你呢?”我忙问。
“我有点事,我一会来接你。你要是洗完了,就在这等我。”
“那,你不洗吗?你去哪里?”
“我有事。等我啊。”小姨只拿走了乳罩和内裤。
澡堂里的女人真的全都光着身子。除了肚子的大小以外,其它地方都是一个样。搓澡时的女人,像是褪了毛的猪,白白的肉肉的在搓澡工手底下晃动着肉身。小姨没有和我一起洗澡,但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她的乳罩是新的。是今天拿着去的那个。
“妞,你说爱情是个什么东西?”小姨突发其问。
“我也说不清楚,我还没处对象呢!”
“真没处?”
“真没处。”我俩相视而笑。
“妞,你说,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抛弃自己的家庭,带着你远走高飞。你说这男的是不是真好?”
“小姨。你咋啦?”
“没事。”小姨那紧锁的眉头出卖了她。“你说,想着一个人,见不到就心烦气闷的。脑子里不停地浮现他的笑脸。你说这是不是爱情?”
“这该是爱情吧!”我知道小姨不对劲呢。但我不知该和她说些什么。
早晨我的眼睛刚一睁开,炕上早已摆好了小姨做好的饭菜。四个菜,桌子底下还放着一瓶白酒。姨父挂着满身的露水进屋。
“哟,今儿这是咋了?啊,啥日子啊?大早上的做这些好吃的。”姨父边抖落着露水边说。
“给你做好吃的,你还不愿意啊。做你就吃。没啥日子就不能吃好的了。”小姨边说边端进来一盘拍黄瓜。“妞,起了起了。”
“好。五个菜!”
家显然是被小姨精心收检过。那一直乌涂涂的镜子也擦得锃亮。晾衣绳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衣物。铺着红砖的屋地,也被小姨擦得格外养眼,那块块红砖似是块块羞红的脸。小姨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陈狗子,你说你爱不爱我。”狗子是姨父的小名,大家都这样喊他,从三岁喊到三十岁。小姨给自己也倒了些白酒,端着酒杯问姨父。
“你没喝就多了咋地?问些啥,两口子过日子。扯啥扯。还爱不爱,你也好意思问出口。”姨父抿一小口酒,看着我们笑。
小姨不再说话。小口小口地咽着白酒。眼圈终于是落下了泪来。她说是酒太呛。
姨父带着醉红的脸溜达去了。
“妞,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晚上接你来吧。”小姨换上了一百二买的新牛仔裤。
“小姨,你要去哪?”
“你不要管了。以后小姨再和你说。这手机你拿着,我给你打电话。”
“我不要。小姨。你要去哪。”
小姨把我抱揽在怀里不再说话。我知道小姨这是要走了,去那个叫爱情的地方了。小姨不会回来了,小姨不要姨父了。
小姨摸摸被子,摸摸枕头。在镜子上哈了口气,拭掉了一颗苍蝇屎。她掀开锅盖,正了正热在锅叉上的饭菜。又扫了扫灶炕门帘。
她回头望了望满地乱跳的鸡,猎圈里那哼哼唧唧的猪……
我望着越来越模糊的小姨的背影,抽泣着木头般站在墙边。
“你老姨呢?”姨父问我。
“噢,买东西去了。说是晚些回来。”我想,只要再晚些爸就把我接走了。
姨夫可怜巴巴地端出热在锅里的饭,问我吃不吃,我摇头。他拿了一个碗一双筷子,没有摆桌子就把饭盆菜盆直接放到了炕边。盘着腿在那吃着。
只见窗前闪过个黑影。狗没有发出丁点声响。我飞快地跑出屋去。只见小姨抱着个十多斤重的西瓜站在土墙旁。我跑过去推开西瓜抱住小姨大声痛哭。
“我那狗给我喂了吗?我那鸡给我圈起来没有啊?那猪食里和稻糠了吗?”小姨冲姨父喊着。
姨父看着地上那摔成八半的西瓜说:“这两人,发啥神经。”转身吃他那半碗饭去了。
“看看,我走一天都不行,哪有把饭盆搁在炕上的啊。这不都是油吗。”小姨换下了那条牛仔裤,放在了柜子的最底层。拿起抹布一边擦炕一边说姨夫。
责编: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