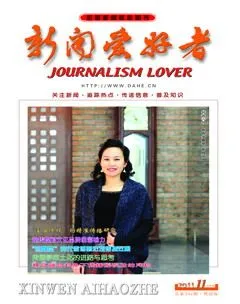周作人绅士梦想的破灭
2011-12-29潘付云
新闻爱好者 2011年22期
周作人的绅士梦想与鲁迅的友爱帮助
周氏兄弟是成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四”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注定他们必然要扮演“中间人物角色”。他们站在了新旧社会的交界处,既背叛了旧传统,又未彻底地割断与旧传统的联系;既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殷切的期待,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们出生于同一家庭,有着同样的教育经历。面对大家庭的败落,鲁迅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他成为周作人生命意识里的引路人。周作人习惯依赖,降低了随机应变的生活能力。鲁迅以自我牺牲守护着大家庭的利益,而周作人却渴望从异域文化中寻求个性解放之路。也许正是这种要求,成为周作人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初动力,并且也或隐或显地决定着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收方向,周作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周作人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阅读《天演论》等著作获得的新认识“明明有我,且明明世界上占有一我之地位”,“一切权我自主,别人不得干涉”。在西方思潮启迪下,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在日求学期间,他同鲁迅一起以巨大的热情译介“具有革命热情与爱国热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另一方面,又通过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文化人类学家茀来则的学说,无限崇拜英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渴望求得个人小天地的“生活之艺术”。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引导督促周作人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急先锋,倡导“人的文学”,反对压抑人性发展的“非人的文学”①,但周作人习惯于享受生活的个人主义取向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邂逅,以自我意志为中心,更强调个体需要,把个性的自由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纯粹的“人”的独立性,追求个人绝对自由与平等,着重个人享乐,国家、民族意识、人民观念相对淡薄。在他的作品中多次申述: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②
“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多雨……在这样的时候,常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③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说来,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好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④?摇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⑤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夜间睡在船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的船只的招呼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⑥
向培良先生评价:“他的态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纯正的绅士风,舒服地享乐着自己的小环境,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趣味,处处以自己做主,并不是从自己出发而归于人类,却是把一切拿来适合自己。”⑦
“周作人是一个绝对个人主义者,所以反抗一切权威,他不如乃兄积极勇敢,他总是带着恬淡避世的态度,他熏染着名士习气,忠实地做了资产阶级的说教者。”⑧这是贺凯先生对周作人的认识。
张中行先生的批评更直截了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就是义不食周粟。”⑨
鲁迅虽在青少年时代,面对大家庭的败落,他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作为长兄,他对周作人的关心与爱护,不单单是显示出血缘亲情的珍贵,而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履行长兄代父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以帮助周作人成名成家。许寿裳常常举出两件事来证明鲁迅对周作人的友爱。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经济拮据,鲁迅就牺牲了自己在国外研究文艺著译出版的计划回国谋职,挣钱资助周作人。在杭州教书一事,还是许寿裳帮忙引荐的。这是许寿裳所说的“以利让弟”。他又“以名让弟”,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记》是他多年辑录的,印行时却署周作人的名字,他的《古小说钩沉》原也想以周作人的名字刊行,因无出版资金而止。鲁迅与周作人同在日本求学,生活工作许多对外事务也完全由鲁迅代办。周作人回忆“我学日语已经好几年了,但一直总是没有好好的学习,原因一半是因为懒惰,一半也有别的原因,我始终同鲁迅住在一处,有什么对外需要,都由他代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⑩。以上事实,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都有说明。鲁迅最大限度地给周作人以强有力的支持,帮助周作人圆着他的绅士梦想,但这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周作人的生活能力。
在绍兴老家,母亲掌管大家庭经济大权,鲁迅自觉维护并义不容辞担当着责任,母亲在鲁迅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周作人习惯于服从,享受着生活幸福。在北京八道湾,仍是这样一个大家庭,母亲年迈,周作人夫人信子掌握着大家庭的经济大权。鲁迅依然努力维护着大家庭的格局,但信子只是管家,不是鲁迅心目中敬畏的家长,没有母亲节俭,消费却很奢侈。资源匮乏的社会,传统的中国人非常强调勤劳节俭,个人必须努力勤劳节俭,不容许懒惰与奢侈;鲁迅用辛勤工作守护着家庭利益,而管家信子则行使着财产支配权。周作人享乐的人生观与信子的财产支配权形成了隐形伴侣,“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的友好,以换取安静”?輥?輯?訛。
1923年,是偶然抑或故意制造的事端并不重要,失和的原因只是表面现象,重要的是鲁迅被驱逐出八道湾。中国封建大家族文化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两种文化取向再无法容于一个屋檐下,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应该也是历史发展、旧式大家庭解体的必然选择吧?
鲁迅站在封建大家族立场指责说“启明太昏”,实际上是周作人立足于个人主义立场无情叛逆,有悖中国传统价值取向。鲁迅先生一路上引导着周作人事业有成,周作人不但没有传统道德要求的回报和受惠者的感激,反而忘恩负义。鲁迅以一厢情愿的付出反复强化了周作人的依赖和安于享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邂逅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并在这个人主义的土壤中生长发育稳固下来。人是习惯的奴隶,一旦养成某种习惯后,行为选择和行为判断中的理性因子就逐渐减少,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因素逐渐参与进来,使之成为“理性缺失”状态下的下意识驱动行为。由此观照,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间形成依赖互利关系也是自然而然的,平时不在人们的意识范围之内。这种关系于鲁迅是感觉舒服,他已经习惯于把整个大家庭甚至民族灾难扛在自己肩上,在物质生活的艰苦中体味享受灵魂的充实;于周作人是有利可图的,他已经习惯于依赖鲁迅,省却了许多生活烦恼。当鲁迅以名利让弟时,朋友间传颂着鲁迅的高尚无私,没有人非议周作人不当得利;中年兄弟失和,尽管原因是个谜,人们只同情着鲁迅作为奉献者牺牲者的痛苦,却没有人指出是鲁迅助长强化了周作人自私利己的行为。周作人与鲁迅互动中形成的安于坐享其成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成为其面对复杂人生自主选择时的性格短板,他所渴望的绅士生活在那个时代也只能是痴人无法兑现的梦想。
周作人的绅士梦想破灭与信仰缺失
周作人生活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是“在”但不“属于”两个时代的边缘人。生活中依赖着家庭和兄长的爱,骨子和血液里渗透了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他怀揣着贵族绅士的梦想,解放后,却成为一个“政治贱民”,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文章,以写文章赚钱来养家度日,苟延残喘着耻辱的人生。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道义和信仰的承担者,因为“人的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成”,“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輥?輰?訛。人存在的意义不单单在于追求的结果,而恰恰在于追求过程本身,人的本质不能仅仅归结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物,而在于他不断创造的精神力量。周作人生活于转型时代,他背叛了所属的那个旧文化传统,除选择现世的享乐外,又不曾寻找到精神上的超越之物——信仰,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其个人人生信仰的支配下,具体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形成一种对个人来说难以轻易抗拒的具有某种神圣性的使命感。而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序》中却说:“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这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显然,周作人毕竟只是说教者,而非行动者。他基本上是远离实际政治斗争的旋涡,早年虽有些亢扬激进的文字,但他不可能有陈独秀那种乐于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的铮铮铁骨,更不会有李大钊、瞿秋白那样为了主义慷慨就义的坚贞和勇气,甚至也没有如胡适那样或入官场或遭通缉而自污清名的实践精神。他固然不是蝇营狗苟的小人,却也不肯和不愿为了信仰理想牺牲个人及小家庭的舒适安逸。日本入侵,他没有听从鲁迅在救国大事上不可以过于退让的忠告;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他又辜负了胡适等朋友敦促他携眷南下的好意,终于由“隐居”而“出仕”,在20世纪40年代初,穿上了日本式军装,戴上了日本式战斗帽,坐上了日本入侵者为他安置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交椅,在自己生命史册上抺下了无法洗净的污垢。他没有坚守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行为失范,失却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尽管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探索了人间很多知识领域,但最终还是迷失了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所能帮助我们解决的只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作为人的根本问题。如哥德笔下的浮士德,在探索了人间所有的知识领域以后,最终不得不和魔鬼打交道。济南失陷前夕,老舍曾抛下一家老小冒死逃出城。他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我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輥?輱?訛很难想象过惯了安逸生活的周作人,他能吃老舍逃难的苦头?他能像老舍一样做一个抛开一切,甚至随时可能是死于沟壑的流亡者?让久在贵族社会的周作人,忽然去吃人间的苦,办得到吗?舍此他还能拥有“阔气排场”的贵族生活?他选择附逆恰恰与他的绅士梦想相悖,尽管他百般为自己辩解,但他的汉奸行为,最终无法得到中华民族的宽恕,“政治贱民”是对他绅士梦想的极大讽刺。
探寻周作人的生活道路及思想流变,当会对我们今天智慧地生存有一定的启示。生命其实就是在生活的海洋里“随风漂流”,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信仰是十分危险的。人有了信仰,人生之路会愈走愈光明;失却信仰之灯,无论有权者、有钱者或有知识者,都难免会跌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
注 释:
①⑩周作人:《人的文学》《知堂回想录八七 学日本语》,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400页。
②③④⑤⑥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序》、《吃茶》、《吃茶》、《乌篷船》,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242页,586页,569页,796页。
⑦向培良:《关于周作人》,见孙郁:《周作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⑧贺凯:《周作人的趣味文学》,见孙郁:《周作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⑨张中行:《苦雨斋一二》,见孙郁:《周作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輥?輯?訛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輥?輰?訛托克维尔[法]:《论美国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9页。
?輥?輱?訛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二十二年》,中国文学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