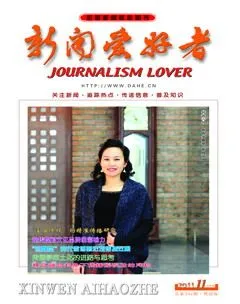心灵的荒漠化与救赎
2011-12-29李猛
新闻爱好者 2011年22期
一
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主要指描写青少年经过生活的一系列磨炼和考验后,获得独立应对生活的知识、信心和能力,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年的小说类型。中国的成长小说起步较晚但生长很快,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直接跨过了《威廉·迈斯特的学年时代》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经典成长类型,以对文学传统中关于意义指涉和道德判断的集体漠视,对传统文化人格的拒载而完成自我割裂与对峙。而伴随着中国的成长小说成长的,是“城市”这个欲望疯长和恐惧错综复杂的精神牢狱,人们把现代文明的高楼大厦当做生存环境的坚硬外壳用来抵御自然界的一切侵袭,而以占有和消费为目的的城市作为成长的终结,却割断了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与交流,使成长失去了生存的本真意义。
成长面对的人格断裂的社会现状使得成长小说面临着巨大的出路困境和迷茫。在新的社会生活和价值重构中,成长面临的是一种缺失传统,逃避现实的巨大迷茫,残酷的现实在冰冷地打击积极成长的阳光的理想主义,传统的断裂和现实的拒绝使成长小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心灵环境的荒漠化。
于是,对峙成了成长小说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对于自我的张扬通过极为森冷的叙述,使成长变得暴力和狂躁。因为害怕融入社会和大众变成社会机器的某一个零件,自我欲望的彰显和强调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而结局却无一例外是为成长主体戴上一个人格面具,躲进远离自然,充满防备和盘算的钢筋水泥躯壳里。成长主体经历成长的疼痛与蜕变,最终怀着深刻的恐惧穿行于“城市”这样的心灵环境,发现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总有人比自己成功,而这些“成功”不断地逼迫成长主体努力去寻找下一个成功,然而所有的“成功”都难以填满心灵世界的荒漠化,对物的无限追逐使成长远离对存在的本真意义的追问。
城市在日复一日不断发展,城市的规划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人类精神却日复一日地风化、分解,城市的扩张伴随着乡野的荒芜,童年的消逝伴随着自然的破碎,成长的结局只能陷入心灵的干涸和枯竭,像《社戏》中那种诗意化的童年,澄清的河水、朦胧的月夜、狡猾而勇猛的猹、可口的蚕豆以及纯真的童心、友善的伙伴,都已经彻底地被最新型的平板电脑所取代。人类再也无法以自然为家,现代都市也再找不到《扬州慢》里“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浓郁芬芳的诗意,而带着一种天然性或者说自然性的面貌出场的成长小说,其荒漠化的速度和程度使得文学精神越来越沦为被嘲弄的对象。
二
人类的功利主义导致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产生,而“现代化侵略性地、积累性地、不公平地将‘自然的’空间转变为‘建构性’的空间”①。这种转变,使人们的心灵环境越来越与城市的环境趋同,而当人们的情感和个性日益受到货币基础的纯粹的理性的漠视时,成长和成长小说在这场城市的盛宴中也不可避免地被同化和吞噬。
在经历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近一个世纪的革命进取主义和人性本能的挣扎之后,在20世纪末,整个文学和心灵世界的生存环境浮现出普遍颓废和衰败的景观,而成长似乎很快就从林道静式的革命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心的荒漠化和精神道德价值体系的严重危机,不是使成长小说增加了更多而是失去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个人的成长是对过往经验和欲望的怀想,又不期然成为人类精神失落的一种隐喻。从林道静的革命理想主义者那种脸谱化的又高又空的人格面具,到余华笔下那些残酷和冰冷的社会现实和生存恐惧影响下的迷茫者和逃避者,再到韩寒、郭敬明这一代人的脆弱和故作天真或者故作成熟,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秩序的傲慢和无礼被复制到饱受戕害的心灵环境中。在成长路上,成长者总是会遇到美好向往和神性理想在与现实碰撞之后不可避免的破碎,这些破碎之后漫天飞舞的碎片充满苦难的意味,这似乎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而充满神性光辉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碎之后,心灵环境的沙化和精神家园的坍塌导致了一种蔓延到整个心理时代的焦虑与困惑。
“都市”是成长小说中物质的远离自然的外部生存环境的象征,物质欲望急剧膨胀使心灵环境受到巨大的挤压而日渐萎缩,如同土地沙化、森林锐减和湖泊干涸一样。随着外部世界和心灵环境所同时遭受的物化吞噬,个体的生存环境陷入令人窒息的困窘,因为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来填补心灵空间的空白,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失去共同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废墟中极度的困惑和绝望,虚无和放纵变成了蔓延整个成长小说的精神瘟疫。叶弥的《成长如蜕》展现了一个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幻灭和向现实妥协的过程,成为一个时代的寓言式概括。石康的《晃晃悠悠》建构了一个彻底丧失信念,颓废和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欲望的无限膨胀留给人们的逼迫感和废墟感直接而汹涌。酒吧是“70年代生”的女性作家书写体验中的一个中心意象,象征着欲望和狂欢,是欲望的张扬之所,在这里,欲望彻底摧毁了任何束缚,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无节制的狂欢气氛,把精神虚无主义进一步推向极端。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与《告诉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以及周洁茹的《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为其代表。“80后”的作者没有经历过苦难,也不想悲天悯人,甚至也不愿意去寻求认可,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编织着一个不愿长大的自我,写的是荒芜的心灵环境中一种寂寞无聊的情绪体验和孤苦无依的心灵感受。郭敬明的《幻城》、韩寒的《三重门》、孙睿的《草样年华》、春树的《北京娃娃》等作品无一不以充满灵气的语言勾勒出一种孤独而叛逆的姿态,不过,优美的文字并不能掩饰作品内容的空洞,强调自我而又在一种强调自我的潮流中失去自我,尖锐和激烈也因用力过度而虚脱,其间弥漫着的暴戾感和残酷感以及作者的冷漠更加缺乏价值判断,缺乏悲悯,叙述全然变成了一种森冷的技术工作——如同南美洲原始森林的伐木工人和日本的捕鲸者一样的工作。
三
舍勒曾经说过,一切都是可以救赎的,人类应该“懊悔”,成长对于过往经验的懊悔和反思,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中寻找重建心灵家园之路,是成长小说实现自我救赎的关键。而海德格尔认为,“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回大地”②。成长小说的审美特质与古人“童心”、“性灵”审美追求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这使得成长题材的作品具备了天然的性情魅力,这种天然性从生命本质出发,在成长的起点,人是一张白纸,带有一种任性自然的特质,各种自然流露的情性和意趣,构成一种独具魅力的审美特征,也使得成长小说更具有拯救的希望。在诸多的成长小说中,既有诗性流溢的乡村画卷,有对人生受难的悲悯和探寻,有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敏锐的才情,也有不断涌现的个性强烈鲜明的新生个体。以少年题材为主的成长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忧郁的审美情怀、真诚的情感价值与和谐、微妙的意境构成了其对美感内涵的独特阐释。
成长小说既有着荒漠化的结局,也有着不少让人感动的另一面;成长小说的作家们有着放弃抵抗,拥抱着内心自私和冷漠的自我逃避到精神废墟的一面,但是那些与现实的生存环境尖锐的对峙和反叛,未尝不是一种陷入流沙中的呼救。作家们笔下的许多少年形象是让人感动的,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许多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美好情怀和作家自身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体验,无数的作家和作品以质问、悔悟、虚构、写实等种种不同的姿态,通过失控的情感和极为残酷的意象,宣泄他们在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悲伤和哀痛。正如同孩子的眼光总是比成人更能发现自然的美,成长小说蕴藏的幽深的憧憬和审美的文学精神,尽管在强大的科技和物质构成的生存环境面前显得孱弱和苍白,尽管其自身精神生态的荒芜使得其“拯救”的理想更容易招来嘲弄和讽刺,但是在日益危急、脆弱的地球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面前,这已经是我们剩下不多的希望之一。
注 释:
①劳伦斯·布伊尔[美]著,刘蓓译:《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鲁枢元著:《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