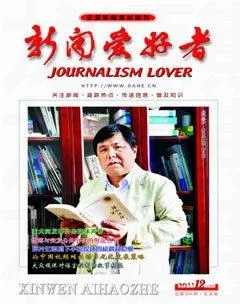论大众传媒中的隐喻
2011-12-29谢竞贤
新闻爱好者 2011年23期
摘要:本文通过赏析大众传媒中的英语隐喻表达,揭示了大众传媒中的隐喻表达具有受众指向性和价值观导向性的特点。传媒中的隐喻呈现出多模态转向;具有明显的文化烙印;具有一定的语义创新。
关键词:大众传媒 隐喻 导向性
引言
大众传媒“通常被认为是新闻和娱乐的来源”。毋庸置疑,大众传媒在提供新闻、娱乐信息的同时,也发挥着说服民众和影响舆论的功能。在新旧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争相吸引大众眼球的背景下,增加新闻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吸引力,是各种传媒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新闻学家查恩利在《新闻报道》中写道:“新闻的生动性如果不是新闻的肉至少也是其调料,它的声音,它的颜色,它的气味,它的形状。它是情绪,是环境,是气氛,是周围人和情感的背景,可以使报道中的主要形象醒目,易于理解。”Quine:人类对感官不可感知的东西主要通过类比的方式描述(而获得感知)。大量使用各种修辞手段是增强新闻可读性和生动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将以大众传媒中的“隐喻”使用为切入点,分析当代大众传媒中隐喻表达呈现的特征。隐喻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众多学说的理论实质都是认为隐喻就是用事物B来表现或说明事物A,即用B的特征来凸显A的本质或本质属性。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认知隐喻观”(Cognition View)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规律,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人类使世界秩序化的方式,也是人自身存在的方式。认知隐喻观将隐喻研究进一步提升到了生命本体论的高度,具有划时代意义。国内很多学者围绕隐喻,从不同维度著书立说,出版和发表了很具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的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如胡壮麟、王寅、束定芳、赵艳芳等。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学者Forceville先生从传媒学角度研究符号学、语言学中的隐喻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通过分析大众传媒中的隐喻使用案例,寻求传媒中隐喻表达的特征。
传媒隐喻使用的指向性和导向性
受众指向性。隐喻语用论将隐喻语义的静态分析转向隐喻生成的动态分析,这是对隐喻语义论的超越和补充。在大众传媒中,隐喻使用呈现显性“受众指向性(audience-targeted)”。与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使用不同,大众传媒中的隐喻往往体现较强的“受众指向性”,即把读者观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分众传媒时代,传媒人士高度关注受众的群体特征:学历背景、职业特征、年龄层次等。据笔者观察,在国内受众定位为600万知识型读者的《南方周末》中,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视角在行文表达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而诸如面向普通民众的地方晚报,相对而言,比较注重语言本土化表达。在国际主流报刊中,因英语为主要语言,受众基本考虑为拥有良好英语背景的读者,其行文思路基本为“英语式”的。传媒人士将这些文章编译为中文时,往往需要考虑国人对这些信息表达的可接受度,尤其涉及一些隐喻表达时,如“pull the rug from under someone’s feet”,就可以翻译为“拆台、破坏某人的计划”;“in the pipeline”为“在酝酿中”;“bread basket”为“产粮区”,而非“面包篮”;“keen bean”为“非常心急做成某事的人”;“hot air”为“吹牛,说空话”;“keep oneself above water”为“避免负债”等。
价值观导向性。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Walter Lippmann较早就认识到媒体对世界的拷贝作用,并认为拷贝世界的产生和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媒体的拷贝世界不是大众媒体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复制或拷贝,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真实世界的加工和制作。”在多元化观点聚焦(multiple-view focused)的大众传媒时代,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多种方式表达。出于价值观取向和说服目的的需要,在用语上都会有导向性选择。如“clear the way for”常常用于政治新闻,表示“扫清障碍”。如用英语表达“丑闻”时,政治、娱乐媒体倾向于使用“gate”一词,以求与其文化渊源保持一致。再如用“airbrush the truth/facts”表示“掩盖事实或歪曲事实(使看起来比真实情况更好)”,用“fat cat”表示“有权有势的人,尤指政府官僚”(贬义),用“new money”表示“新贵”,用“under fire”表示“遭受攻击”,用“drama queen”表示“小题大做的人”;用“chicken coop”或“rabbit hut”表示“蜗居”,这些表达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取向。
传媒隐喻的特征
多模态转向的必然性。胡壮麟指出:自然状态下发生的话语活动往往具有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以前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很少有人从多模态角度分析话语。现在,随着新媒体技术和语料库的迅速发展,对自然话语进行多模态研究已经成为可能。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整合起来,它不仅可以看到语言系统在意义交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可以看到诸如图像、音乐、颜色等其他符号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从而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进而发现人类如何综合使用多种模态达到社会交际的目的。可以说,这类话语分析既可以推动我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符号学的认识。
Kress & Leeuwen认为“多模态(multimodality)就是运用几种符号学模态(semiotic modes),或综合使用若干符号学模态来强化同种意义的表达,或行使补充功能,或进行有层次排序”。O’Halloran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将多模态定义为“综合语言、视觉图像、其他符号资源,构建纸质、数字媒体和日常生活文本、事物、事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众所周知,现代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和信息内容呈现出多模态样式。Forceville作为传媒学者,于1998年出版了《广告中的图片隐喻》,2009年出版了论文集《多模态隐喻——认知语言学的应用》,多角度阐述了多模态隐喻。
隐喻的“多义性”。Forceville先生提道:“隐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受制于它所发生作用的文化和专业背景是隐喻研究的第三个维度。”隐喻作为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语言现象,虽然具有认知共性,但是因为与文化的紧密相连,在跨文化解读中会对读者形成一种挑战。
隐喻的“多义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隐喻的跨域映射决定隐喻的原域和目标域本身就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众多可能的映射中,言者和听者趋向于根据共同的语境和个人经验或体验来取舍意义的对应。根据顺应理论,虽然言者和听者会尽可能寻求“理解”,但是在言者和听者间产生“误解”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文化认知在隐喻解读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如美国零售商JC Penney的视频广告(Every day matters)通过十多个场景,集合视觉、听觉的感官互动描绘出“生活就是魔术”的多模态隐喻。笔者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是没有英语文化背景的人;另一组是拥有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人。结果显示,拥有英语文化背景的受试者很容易理解该广告的内容,体会西式的幽默与欢畅淋漓;反之,对照组受试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趣与关注。
习语隐喻的广泛运用。“许多语言特征也是文化特征。”作为习语意义的明显特征和重要修辞手段,隐喻表达在大众传媒中运用广泛。如新闻中出现的“with flying colors”,源于出航时,每条船都有一面旗帜,英语叫colors。船旗用来表示船只的国籍或所属公司。打了胜仗,战舰上舰旗飘扬,得胜归来,这个隐喻表示“成功地(完成某事)”。再如“Hail Mary pass”是万福玛利亚传球,原是橄榄球术语,是一种成功率低的向前长距离传球,通常在比赛将近结束时使用,这种传球能否成功,就需要圣母玛利亚祈祷了,用到日常生活中,这个短语表示“明知希望渺茫但仍抓住最后机会孤注一掷”。“one-trick pony”则指凭借某一方面的特别才能闯出名堂的人或公司。再如“Alliance says cream of Taliban Fighters Destroyed”,cream 的本意是“奶酪”,但是“the cream of something”在英文中表示“精华,精髓”,这里的“cream of Taliban”就是塔利班的主力的意思。此类的隐喻表达在跨文化翻译中很难把这种文化内涵作详述,唯有依赖读者自身的跨文化知识积累或作者恰到好处的注释。而中国新闻中,诸如“虚假公职”、“幸运符”、“时刻准备着”等表达译成英语时,往往会遵从英美人士的表达法,如“ghost jobs”、“rabb/sX64GS29XRJzuehKs7eyQ==it’s foot”、“wait in the wings”,这完全是基于受众友好型。
“旧词新义”隐喻。除了文化隐喻相关的表达外,新闻隐喻中还时常通过“旧词衍生新义”的方法来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如“snail mail”专指“由邮递员分发传递的传统信件”;“take a leaf out of one’s book”指“效仿某人”的意思;“a pinch of salt”表示“半信半疑”的意思;“ghost writer”表示“代写者”;“looking-glass”、“baby kisser”分别表示“完全颠倒的;正好相反的”、“善于笼络人心的政客”。“sock puppets”原指那种通过在袜子里塞进棉花来制作的简单偶人,此隐喻义就是指受雇在论坛和社交网站等网络场所发表言论,从而左右大众舆论的人,对应中文名称就是“水军”。这些词各自的基本含义都是很确切的,也是很固定的,但是因大众传媒应和时代和表达的需要,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些词,增加了其语义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语义创新”。
结语
本文通过赏析大众传媒中的英语隐喻表达,探讨了大众传媒中隐喻使用的受众指向性和价值观导向性及其主要特征。总体而言,传媒中隐喻使用呈现多模态转向,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一定的语义创新。[本文受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下的隐喻》(项目编号:2010SJD740015)和江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多模态视角下的隐喻》、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与数字技术》联合资助]
参考文献:
1.Forceville,Charles. Multimodal Metaphor-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9.
2.Hudson,R.A.Sociollinguis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Kress,Gunther & Theo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ucation.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1.
4.O’Halloran, Kay L. “Inter-Semiotic Expansion of Experiential Meaning: Hierarchical Scales and Metaphor in Mathematics Discourse.” From Language to Multimodalit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deational Meaning. Eds. Jones, Carys & Eija Ventola.London:Equinox,2008.
5.Quine,WV. Word and Object .Oxford:MIT Press,1964
6.Vivian,John.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7.郭可:《当代对外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
9.王松鹤:《隐喻的多维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
10.谢竞贤:《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隐喻》,《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11.谢竞贤、梅德明:《隐喻性话语的顺应性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12.许明武:《英语新闻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13.张健:《新闻英语文体与范文评析》,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4.朱伊革:《英语新闻的语言特点与翻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