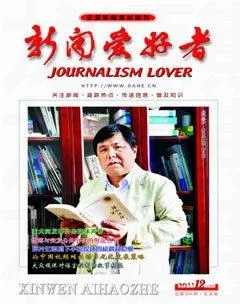大众传媒与灾情预警:科学、新闻与社会
2011-12-29马汇莹
新闻爱好者 2011年23期
中国能在几分钟内预警海啸?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的报道说“我国海啸监测能力逐步完善,近海预警报两分钟内可做出”,中央电视台4月20日“新闻直播间”的报道喜悦地宣称“我国海啸预警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看到这些消息,笔者联想起另一些报道。《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曾报道,目前“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海啸预警,还有不少空白区”。时隔20天,海啸预警能力有了如此鲜明的变化,着实让人感到欣慰。但如果联系一系列有关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和研究,则让人疑窦丛生:两分钟内发出预警,向谁预警?如何预警?
日本如何能在3分钟内发出预警
据央视3月19日的《新闻调查》采访海啸预警专家说,大地震后日本气象厅的海啸预警“估计就是5分钟之内就能发出去”。有研究者仔细考证后发现这个时间是3分钟①:地震发生3分钟后,日本气象厅即向沿海37个市村町发出了大海啸警报。人命关天,预警时间不得不“辎铢必较”“分秒必争”。日本是通过两种途径通知公众的:一条是气象厅向沿海地区居民发出预警,另一条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广而告之。两种渠道都直接指向公众,特别是“沿海37个市村町”,这也是海啸预警真正的价值所在。日本为何能如此迅速向公众发出预警,当时关注于大地震、海啸及核危机的我国媒体鲜有报道,这可能是因为各种灾难接踵而至,最先的预警情况反而容易被忽略掉。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据专家介绍,人类对地震、海啸还无法做到提前预报,只能在其发生后,就可能带来的危害作出预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就是一个信息平台;而日本历来重视灾情预警研究,海啸观测能力也很强。
检索发现,2008年6月,《东方早报》曾对日本的灾情预警体系做了详细介绍。当时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但伤亡很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已研发7年的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安装了接收装置的火车、飞机、电梯等,在收到预警信号后,可以迅速自动停止运行。2007年后,提供预警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国民。2008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发生3秒后,电视上发布了预警,这意味着距离震中3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地震摇晃发生之前10多秒就得到了警报。上述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正集中关注于我国的抗震救灾。
新华网的报道指出②,日本政府从2005年起开始建设“全民危机警报系统”,由地面数字电视、手机短信、入室警报设备等多个媒介组成,当地震仪器监测到初期微动,并且震级达到4级以上时,警报就直接通过电视、手机等媒介发送出去,而不必通过地方政府部门。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远距离强行启动电视机或中断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改为播报预警。在使用这种技术时,只要不切断电源,用遥控器使电视机处于待机状态,就能使电视机收到危机警报后自动开启。也就是说,日本的灾情预警已经能做到以秒计。东京非营利组织“即时地震信息联盟”的资料曾指出③,如果主震区能提前2秒获得警报,其区域的死亡人数最高能减少25%;如果能提前5秒,死亡人数最多则可减少80%——因为人可以在最短5秒的时间内对自己进行基本的保护措施。当然,这是在国民训练有素的前提下。我国海啸预警专家于福江指出,日本“具备将预警消息迅速发送给沿海居民的能力”。灾情分发系统又被称为海啸预警的“最后1公里”,“灾情分发如果到不了政府和老百姓手里,前面的一切工作等于零”。
中国能在两分钟内预警近海海啸?
诸多媒体在转发“两分钟预警”消息时,没有详细提及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手段、向谁预警,是向有关抗灾、应急政府部门预警,还是向最易受灾的沿海居民发出预警。
灾情分发途径、手段方面。我国灾害预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层传递。“业务部门接收到数据,十几分钟即可制作出预报,20分钟可以发布出去。但预报一般只发到省一级,如果再由省转到市,市转到县,县转到乡镇、村,对应急而言,时效太差,效率太低。”④据介绍,目前我国很多沿海地区还没有警报器,手机短信的方式尚在探索中,敲锣打鼓等传统方式的疏散还是必要的。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也说:“在演习这种有准备的情况下,灾害预警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通知到灾区。”
灾情所达的人群或地区方面。据报载⑤,美国研发的系统不但预警海啸的高度、到达时间,还包括海啸淹没情况的模拟图。而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沿海哪些地方存在被淹没的威胁,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说得出来”,海啸预警的针对性和价值显然大大降低。现在能够做到把信息传至“政府有关部门”,但何时能传递到普通公众,实际上是个未知数。
详细分析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结论被相关专家也多次重述):相比日本灾情分发系统的高效运转,“中国的差距相当大”,在灾情分发的“最后1公里”上是个“短板”。难道一个月内我国的海啸预警能力就大幅提高?果真如此,这些进展是如何取得的?
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海啸预警作为一个科学技术问题,非专业人士似乎难有资格评述。但技术问题与制度问题实际上难解难分,技术进步的背后往往是制度、观念的突破。日本气象厅的一项法规即要求,在一场地震被检测到的时候,要马上把有关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警察机构、通信公司、电视媒体、海上保安厅、消防机构等,并进一步发布至民宅、学校甚至船舶等地方。直接面向公众而不是层层传达,这是日本高效的灾情分发体系背后的制度与理念支撑。
“预警”体系既包括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也包括更具社会意义的层面,即如何把信息分发给公众,“跑赢最后1公里”。深究下去,貌似纯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背后也有制度因素,《法制日报》报道说:“如果要进行海啸预警,首先要取得地震资料。在我国,海啸的预警由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地震局3个部门管理。目前,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协调并不是很顺畅。”⑥
技术问题与公共信息发布的制度问题纠缠在了一起。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能不能通过广播电视、移动信息平台等实现强制预警播报,信息直抵公众。据《法制日报》的报道,“目前我国尚无此相关规定”,“相反,每年在电视台发布国家海洋预报相关灾情信息,还需自掏一笔金额不小的占用频道费。同时,灾情的短信群发系统每年也要向移动运营商支付十几万元的短信费”⑦。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意识到这类公共信息的重要性和对提升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性,一般都能及时滚动播出,必要时中断正常节目进行直播。
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预警本身的不确定性,问题就更复杂了。《南方周末》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海啸预警当中,有两种情况要做得准确。一种是大海啸来了,你要预测它是不是确实能强到造成灾害。再一个是,它如果很小,你预测说它很大,然后做了疏散,也会造成很多的经济损失。”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分发预警信息时的慎重不难理解,而这种慎重会不会影响到“两分钟”?
公众如何理解科学
本文意不在班门弄斧考证“两分钟”是否属实,而是借此探讨科学、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和社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历史。1690年9月25日在美国《公众事务报》(Public Occurrences)第一次出现科学报道‘Plague and Argues’(瘟疫与理据——本文作者注)以来,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悬挂的隔帘开始时开时合。”⑧如果这种“隔帘”存在的话,大众传媒应该是让它“时开时合”的力量之一。如今媒体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热衷于科技传播,如果说“公众冷淡了科学”,原因之一就是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公众对科学进展、“器物文明”不再抱有天真的热情和幻想,赶超世界的科技如果没有制度文明的支撑,便提携不了民众“幸福感”,所以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欧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公众态度的转向,只不过原因、背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科学报道主要是亲科学的,媒体对科学报道的口吻是积极的。60年代后对科学报道改变的原因主要是:1.对战后科学颂扬后的失望;2.对技术失败,尤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反应;3.受过科学教育的记者出现。”⑨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经历了一个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转移。什么是“公众理解科学”?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正式发表报告《公众理解科学》,意在改变二战以来英国公众对科学和技术逐步形成的保守、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今,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至少由三方面组成: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可以说,“公众理解科学”最根本的目的是培育理性精神的人,“将科学精神注入国民文化”。“科学的含义不能是想当然的,或者只是由某些有特权的权威提出来的。科学家往往将他们所熟悉的知识作为传播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性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⑩
回顾本次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过程,可以看到科学、新闻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轨迹。传媒报道刚开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好似对中国海啸预警研究的“预警”。负责任的科学家们也第一时间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公众释疑解惑、普及知识。
令人奇怪的正是这“两分钟”报道。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科研进展的发布,则缺乏相关研究方式的介绍,引人生疑。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两分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公众该如何理解这个“两分钟”。从采访来看,这则消息是在海洋局一个不相关的会议上一位专家提到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公众关心的新闻点,但却不见采访其他消息来源。美国“Saturday Review”的记者约翰·里尔说:“对其他领域发生事件进行新闻报道的不受阻碍的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必须成为科学写作的标准。”从编辑角度来看,精心选择这个信息点作为标题,提高了新闻的被关注度,回答了人们心里的问题。但是换成“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这则简讯与其说解答了疑问,不如说引起了更大的疑问:是实验室里的“两分钟”,还是现实社会语境中的“两分钟”?
科学传播需要传播者(科学家、编辑记者等)注意到哪些内容不仅仅意味着科学,而且也意味着“理解”。如果读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海啸预警报道,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篇报道介绍了世界前沿的海啸研究工作和面临的挑战,并回溯了以往海啸预警实际的社会功效和公众反应,说“正在研发中的海啸预报系统发挥了作用,但没有快到足以帮助生活在仙台海岸的居民”。标题是《海啸预警:比较快,但还不够》。(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国际化与本土化:京沪粤港免费报纸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S73;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30102)
注 释:
①《新京报》:《日本政府24小时应对地震:信息公开透明》,2011年3月13日。
②乐绍延:《日本决定在2011年前建立全民危机警报系统》,http://news.sina.com.cn/w/2005-01-04/23075424610.shtml
③中评社:《当日本遭遇地震》,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④《人民日报》:《海啸预警,还有不少空白区》,2011年3月31日,第9版。
⑤黄永明:《海啸预警:比较快,但还不够》,《南方周末》,2011年3月17日。
⑥⑦⑨蔡岩红:《我国应对海啸尚存多种不足》,《法制日报》,2011年3月19日。
⑧⑩李大光:《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13日。
(作者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讲师、博士)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