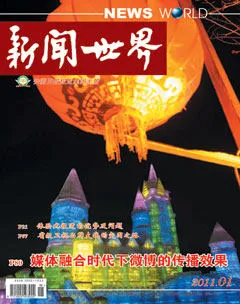媒体对“80后”的形象呈现
2011-12-29赵晓炜
新闻世界 2011年1期
【摘要】李普曼曾指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换句话说,如果某一群体多以否定的、负面的形象被呈现,那么长此以往受众的反应会直接作用于这一群体所处的现实世界。
【关键字】妖魔化形象呈现“80后”
作为在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80后”,从呱呱坠地起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带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他们的个性被媒体不断地挖掘;他们的生活习惯被各媒体专注评论……在不断的信息编码的过程中,关于这一代人在“拟态环境”下的个性特征被媒体所建构,也因为媒介是大众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所以我们不得不正视“拟态环境”下的社会影响力。
一、被“妖魔化”的“80后”
为了吸引眼球,有很多媒体制造以“80后”为噱头的报道。在《南方报业网》上搜索6560篇关于“80后”的报道,其中处在前几页的都是以“80后”为标题的报道,如:江冰解读80后:“生在蜜罐里长在牢笼里”;80后女农民工独立性更强家庭观念更淡;呼和浩特4监犯越狱均系80后;粤悬赏通缉50名命案逃犯 “80后”占六成……根据这些新闻,我们似乎感到“80后”是“垮掉的一代”,是“扶不起的阿斗”。有关“80后”的负面新闻中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婚姻、犯罪、住房、消费等,试问哪一代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搜索“80后”关键词,会出现诸如:心理不健康、没有责任感、问题多多、犯罪等等,这样的报道误导大众。媒体有“妖魔化”“80后”的倾向,从近几年热播的两部电视剧《奋斗》、《蜗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80后”的媒介形象建构。《奋斗》中几个主角,导演将他们塑造成了享乐的一代,剧中大部分情节并没有主人公奋斗的经历,而是一群衣食无忧的年轻人在恋爱的经历。剧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很含蓄,每个人都有张扬的地方,甚至是浮躁。与父辈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剧中父母始终将“80后”青年当做温室里的花朵。而《蜗居》虽是讲房奴的生活经历,但剧情中也讲“80后”的生活恋爱经历。从这两部电视剧中,使观众体会到了“80后”一代共同的特点:小资、敢爱敢恨、啃老族、重义气、自私、爱慕虚荣、娇生惯养,“80后”是被爱浇灌大的一代,他们随时都需要爱的呵护……
二、拟态环境下的异端行为扩大化:从理论视角解读
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同样我们也生活在被大众媒介构建的社会环境中。李普曼对“拟态环境”做过这样的表述,“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
在拟态环境下,最容易产生“异端行为扩大化”。主要用于大众媒介加以协调和充分表达的某种社会反映,被冠以异端的初始行为愈发增加或“放大”的过程。Wilkins对这个概念做过深入阐述。他力主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听信那些针对被贴上异端行为之标签的群体或行为的简化的、刻板印象的、常常是误导性的信息,那么它就以产生更多异端行为这一方式对此作出反应。这里强调的是大众媒介提供信息的作用,特别是在提供有关异端行为的标签与解释的作用。1973年,Rock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解释,包括的步骤如下:
(1)由于大众媒介的精心编排而引起不断强化的公众关注,一个显而易见的“犯罪浪潮”就出现了。
(2)由于大众媒介、压力集团与政治诉求所表达与呈现的公众关注,聚焦于警方与控制机构针对异端行为的警觉之上。
(3)这种连续增强的警觉由于发现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多的明显异端行为而提高了捕人率。
(4)这样又加剧了犯罪浪潮,进一步激起观众的情绪与关注。①
在循环往复的状态中,大众媒体充当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媒体)专注于某个事件时,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一事件,这一事件本身不论在何时都是没有变化的,只是我们的心境受到了影响。而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缓慢的认识过程。当媒体把焦点开始集中于“80后”时,观众意识里也会对这一群体有了初步的概念性的认识,随后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导致了受众/民众对“80后”有了一个印象,而这一印象不是观众自己通过实践得到的,而是通过媒体的构建得到的,因此,对“80后”就产生了错误的构建。在新闻传播过程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本来是非常态的异端事物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或是大众传媒/大众高密度关注后,最终成为常态化的现象。
从异端行为扩大化这一理论角度来分析在拟态环境下媒体对“80后”的报道及其建构。有关“80后”事件的报道常常被写得危言耸听,谴责意味十足。如前几年在对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潜逃一案,媒体做了很多相关报道,制造出马家爵是一个“校园杀手”、“云大屠夫”“混世魔王”等形象②;而有关他本人的报道也多是以负面报道为主,缺少公正全面性。在这样的符号编码中,潜移默化培养了受众的敌视情绪,甚至造成受众的理解偏颇。无论是在标题的拟定上,或是在后续的报道中,媒体都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新闻专业主义素养。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关于“80后”青年犯罪的报道,一些媒体都标准化的运用敌视的语言符号,将罪犯群体化,过多地关注于事件本事的奇观化和趣味性,缺少深层的剖析而将制造罪犯和犯罪的社会背景隐藏起来,给受众一种错误的暗示,在受众头脑中建立起了“80后”的拟态形象。
下面这则报道标题是出自《南方报业网》2009年11月16号上的“粤悬赏通缉50名命案逃犯 ‘80后’占六成”,报道称昨日省公安厅对50名未破现行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