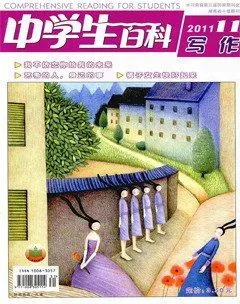运镜的挪移
2011-12-29张维中
中学生百科·小文艺 2011年11期
前阵子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以唐诗为基础,赋予新撰故事的童书时,重读了许多王维和孟浩然的诗作。
如今想起那些诗词里出现的画面时,仍时常令我感到惊艳。
像是孟浩然那首我们从小熟悉不过的《过故人庄》,當我有机会离开东京走进日本的乡间小路时,每一次看见眼前的风景,总是会佩服起當时的诗人将其眼前所见,以笔墨转化成摄像机运镜一样的叙述。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从远景到近景:从放眼望去的绿树环抱、延绵不断的远方山尖,到推开朋友家的窗子,屋外映入眼帘的菜圃与打谷场。最后,视线回到了距离最近的对方身上,自在地聊起田园生活的耕种趣事。
诗人精炼的二十个字,镜头挪移般的画面,已经是一部影像作品里的剧本场景。
那时候,除了肉眼与绘画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存下画面的吧。只剩下了文字的记载。所谓的视觉这件事情,在非电子的时代。是透过某个人的记忆转述,然后,再由另外一个人的想象力去重组,去架构而成。
古代,毕竟跟现代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网路,没有照相机,没有电视和电影,當然也没有用手指滑来滑去的智能手机。如今,这些在生活里随时就能保存下画面的机器,让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成为一个影像先决的世界。
在东京学设计的学校里,每次上完课时,老师还在讲台上,白板前就会簇拥起一群学生。每个人都拿起手机来,开始对老师站着的方向咔嚓咔嚓地按下快门。拍的當然不会是老师,而是他身后白板上的笔记。课题的解说、制作的时间进度或者下堂课要携带的工具,以前总习惯拿纸笔记录的,现在为求方便,拍下来就好。
然而,那个影像,并不是靠自己去记忆的。是借由许多能够拍照的器材,代替了我们的思考,留存在硬碟里。于是,當我们回想起某件事情时,大脑变成是去搜寻档案的存在之处,而非先去回想事件的本身究竟存在着什么文字或画面。
反正有图片就好。下一次,忘了,再打开档案来看。
那一次,當同学铃木一个人在一趟午餐后丢了她的手机时,她怎么样也无法跟旁人完整地陈述,她究竟沿途走过哪些地方,又在哪几个什么样的场所用过手机。
我们试图帮她回想起她可能把东西忘在何处,甚至想要分头替她去寻找,可惜,她无论怎么努力去形容,嘴里说出的语言却是那么地模糊与空洞。
也难怪每次在作品报告时,铃木即使盯着照片,却常常无法顺利地用清楚而完整的叙述去表达影像的含意。
过度依赖影像替代思考,进而失去了用词汇去表现、重述画面的能力,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像是网路的搜寻引擎,可以搜寻到各种文字网页内容,可是一旦碰到文字图像化以后,就束手无策了。
语言表述的退化,将影响一个人的逻辑,以及跟外界沟通的能力。
因此,每當我想到像是《过故人庄》里那样不只用着充满画面感,而且还带着远近挪移的句子去表现出诗人的心境时,便不免遗憾仿佛那将是不少人快要失去的东西。
视觉中的远近感和声光性,如何回到字里行间去用词汇表现出来,比什么都来得更具刺激和挑战。
画面的也好,文宇的也好,所谓的层次感,其实就是这样诞生的。
考运跟官运老是不顺遂的孟浩然,大概也是从这样的层次中拉开了距离。看似平淡的人生,所以也在焦距的挪移间,有了新的视野。
编辑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