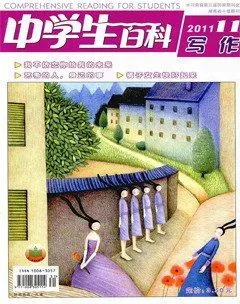杨妮妮:我的文字比我冷
2011-12-29
中学生百科·小文艺 2011年11期
本期主角
杨妮妮,浙江省乐清市白象中学学生,第二届浙江省校园新锐写手大赛高中组第一名及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在“作家杯”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二等奖,在《中国校园文学》《中学生天地》等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有小说《冬天凝结成冰》《余烬》刊于《中学生百科》。
[老师评说]
她不是那种很会说话的孩子。我对她的认识,其实更多的也是通过她的文学。妮妮有灵气,但不那么自信。似乎每次希望她参加什么活动,她都不是说“好的”,而是问,干吗?为什么这样々就像我让她拍照,我明明觉得她挺好看的,她却每次都说照片不好。但她的文字是男一回事。她的文章无疑是深刻的,或许拙于言辞的人,上天就会赐她一手好文笔。她对事物看得很深,能够体会到很多这个年龄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深刻含义。说实在的,我不喜欢那么冷酷的文字,但不可否认的,她刻画出了很多人性真实的黑暗面。
(黄忠)
[自说自话]
很忙很忙,但又没什么好忙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偶尔会有点人群恐惧症,害怕挤在人群中,明明已经使劲踮起了脚,呼吸到的依旧是浑浊的空气。开始慢慢适应一个人走路,有时连紧张也是安静的。所有的心情跟高三有关,这种生活很是乏味,但是还是可以享受每一天。因为在不久的以後,我一定会没完没了地去回味这一年的时光。以後不会再有这样的日子了,可以一心一意地为唯一的目标奋斗,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无心察言观色,可以有幼稚得脱线的梦想。这是一生中最干净的一段时光。即使它还未完结,我也已经开始了怀念。
[杨妮妮作品]
象城无象
当和煦的晨光铺满象城头顶的苍穹时,象城终于从睡梦中醒来,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打着呵欠睁开眼睛。
象城坐落于浙江省的南部,依着几座连绵起伏的山峦,不急不缓地走过了百年的光阴。而在山峦的另一面,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温州市。当那些生活在温州市里的人们喜欢在晚饭後逛遍商业街道的时候,象城的人还是习惯在晚饭後去戏台边听一台老掉牙的戏,然後咬着内部塞满萝卜丝的灯盏糕,一步一步摸着黑走回家。象城是慵懒的,就像那条穿过象城的河流,总是缓慢地流淌着,平静得泛不起一丝波浪。那条河有一个与象城相似的名字一象河。
我家住在象河边的一条巷陌里。
几十栋老式瓦房挤在象河边上,形成一个密集的居民区。居民区的尽头是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水稻田,与拥挤得快要窒息的居民区相比,稻田是一片绿色的辽阔海洋,空气像洗涤过的清新干净。
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一手提着沉重的书包,一手拉着石湘走过象河边气味芬芳的水稻田,走过象河上那座扶手低矮的石拱桥,走过象河边那条边沿参差不齐的老巷子,走过那些属于象河,也属于象城的日渐泛黄的模糊记忆。
李秀莲过了六十岁的生日後,眼睛老花的程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每次我和石湘刚走到巷口时,她总能在大老远处就看见,然後用高亢又带几分做作的嗓音喊道:“哟!两姐妹回来啦。”她说着,语调还会忽高忽低地变化,就像象城的小路,直着直着突然又生硬地转一个弯。每当这个时候,石湘就会握紧我的手,像要掐断我的手那般用力握紧。那时候,我就知道,石湘不喜欢李秀莲说话的语调,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可我们谁都不能说些什么,因为整个象城,十几万的人口,极度热衷于这样的语调,这甚至成了象城的一个特质。
象城偶尔也会爱受风寒,打个喷嚏。
曾祖母从她的小平房开始,走了半公里的路来到我家。刚进大厅,李秀莲便冲进储物房里把那些吃的喝的全都藏进纸皮箱里,藏不了的便直接用几个塑料袋盖住。李秀莲对曾祖母有种异常强烈的戒备感,只有做完了这些,她才可以安心地继续干她刚刚没干完的事。
曾祖母走到我和石湘面前,从怀里掏出两个大概是从庙里拿来的柑橘塞到我和石湘的手里,说:“想想,还有那个……嗯,想想他姐,这东西我给你们吃。”她年纪大了,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比如石湘的名字,比如我的名字。
“石森呢?”曾祖母咧开没牙的嘴巴问道,然後自顾自地往楼梯口走去。一直都是这样,曾祖母的问题,一直都不需要什么回答。
“这老太婆真够烦人,有事没事老往这跑。”李秀莲又开始抱怨了,她看着我和石湘手里的柑橘,皱起了眉,“这是她给的?”
石湘用力点点头,然後剥开柑橘的皮,几滴橙黄的汁水溅到石湘的白衬衣上。李秀莲瞪大眼睛盯着那几点黄斑,一把夺过石湘手里的柑橘尖声骂道:“你看看,又弄脏了。你都多大了,七岁了知道吗?你就不会小心点啊?还有这死老太婆,自己不要的东西还敢拿出来给别人!”说着,顺手把柑橘扔进一旁的垃圾篓里。
石湘呆呆地看着垃圾篓里的柑橘,抬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愣着干吗?快拿毛巾擦干净!你知不知道我洗一件衣服有多辛苦?”李秀莲走过去,像拎小鸡一样拽着石湘往浴室走去。
李秀莲从来都如此固执地讨厌曾祖母,可这真的不能怪她。
曾祖母老得简直像从历史教科书的黑白插图里跳出来的人物,也像恐怖电影里瘦骨嶙峋的僵尸,干瘪的脸和扭曲变形的表情,就连我有时也会忍不住心生厌恶。曾祖母没有名字,也不需要名字。李秀莲喊她“老太婆”,石森喊她“妈”,其他的人喊她:“石森妈”。
石森是曾祖母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
那年,石森刚出世。曾祖母不知从谁那听来的,说她的儿子五行之中缺木,便急得发慌。曾祖父拿着烧焦的木柴在地上写了三个字,“木”、“林”、“森”。曾祖母压根没看懂这是什么,曾祖父说:“孩子缺木,那名字就要取带木的。你看,这个是一个木,‘林’里有两个,‘森’里面有三个木,你看取哪个当名字?”
“当然要三个的!越多越吉利!”曾祖母歪着脑袋说。
也许真的是取对名字了。石森从小到大都有曾祖父母护着,没吃过什么苦,二十岁就娶了十五岁的李秀莲进门。而就在李秀莲被娶进石家那年,曾祖父却因病去世。那时,曾祖母又不知从哪听说,李秀莲的八字与曾祖父的八字相克,石家的老头子定被李秀莲克死的。从那以後,曾祖母看李秀莲的眼神里便有了怨恨。
石森,李秀莲,曾祖母,他们不太平静地生活在曾祖父留下的小平房里。
李秀莲这辈子为石森生了四个孩子。最大的是个儿子,取名为石浩文。然後是两个女儿。李秀莲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是冬天,石森终于攒够了钱,开始在半公里外的象河边上建造一栋属于他们的房子。那个冬天里的每个夜晚,李秀莲总会坐在板凳上等石森回家,然後一边把他被风吹得冰凉的手放在手心慢慢捂热,一边低着头默默流泪。那时,李秀莲还没後悔嫁给这个男人。
当李秀莲的蒲扇扇走了夏天後,石森建好了他的房子,李秀莲也生下她的第四个孩子。李秀莲临盆的那天,石森把自己关在房里关了一天,翌日,他拿着一张写满名字的纸对躺在木床上脸色苍白的李秀莲说:“这一胎是男孩就叫石文海,女孩就叫石玉娥。”李秀莲撑起沉重的眼皮,欣喜地看着石森,使劲点了点头说:“是男孩。”石森顿时乐得找不到东西南北。
秋天快过完时,石森带着李秀莲,他的四个孩子,还有曾祖父的遗像搬进了新房子,唯独没带上曾祖母。因此,曾祖母对李秀莲的怨恨便更深了一些。她恨这个女人不仅克死了她的丈夫,还迷惑了她唯一的宝贝儿子。
曾祖母在小平房里怨天怨地了两个月後,有事没事就爱逛到象河边去找李秀莲。那时,李秀莲刚从新邻居那学会制作腌萝卜头的方法。她上集市买了半个人大小的米缸,然後偷偷到居民区尽头的田里拔了一箩筐的萝卜回家。削皮,切块,李秀莲样样都做得极其顺手。她把萝卜一块接一块放入盛了盐水的米缸里,蒙上麻布袋,准备搬到庭院一角的时候,曾祖母来了。
“弄什么呢?哪来这么大个米缸?”曾祖母手里拿着根牙签挑掉牙缝里上一顿饭遗留下的残渣。李秀莲费力地搬着米缸挪动,喘着气应道:“腌萝卜头。”曾祖母不屑地哼了一声,扔掉牙签不声不响地走到李秀莲旁边帮她把米缸往一旁搬去。李秀莲被突然伸来的手着实吓了一跳,触电一般把手从米缸上收了回来。她一收手,米缸就不偏不正砸在了曾祖母来不及收回的脚上。
当曾祖母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时,李秀莲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
李秀莲到现在仍不能忘记这件事的结局。
现在,每当石森拔来一箩筐的萝卜,在庭院里削皮,切块的时候,李秀莲坐在躺椅上翘起二郎腿像当年的曾祖母那样不屑地哼一声,然後扯着我或石湘说:“你看这老头,当年他多威风呀!说砸就砸了我的米缸,还跟我说这辈子都别想再弄什么腌萝卜!现在倒好,他自己反而腌起萝卜来了。”
自从这件事过後,李秀莲对石森有了怨,她开始後悔自己嫁了这么一个糟老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秀莲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她在象河边洗着一家大小换洗下的衣服,忽然发现大木盆里已经没有孩童的开裆裤了,而自己的眼前却蒙上了一层薄雾,视线里的象河也笼罩着一层薄雾,象城也一样。李秀莲按着酸痛难忍的腰背站起身,捧着大木盆往家走去。她想起当年石森还带着她走过这条沿着象河的泥泞道路,把她娶进了石家,那时,象河边还没有这么多的房子,而时间一晃就是一辈子。现在,象河边的房子越来越多了,大儿子石浩文也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後就跑到广东做生意。两个女儿紧接着各自找了个婆家,一个去了北京,一个去了上海。只剩下从小就受尽宠爱的石文海窝在家里无所事事。李秀莲急了,连忙安排了一连串的相亲,石文海终于也找到了一个对象。李秀莲以为一切都已圆满,以为自己可以安度晚年时,石文海却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石湘与老婆离了婚。
象城做着美梦时,忽的被一个喷嚏惊醒,那个华丽的梦境在须臾间碎成一地废玻璃和雾气弥漫的沼泽。
石文海听说上海那地方好赚钱,不听李秀莲的劝告,硬是扔下石湘跑去上海做他的发财梦,而李秀莲只能在象城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因此,李秀莲的怨气被逼上了顶峰。她怨石湘摔碎了自己安度晚年的美梦,也怨不成器的石文海做些没用的白日梦,就是不怨自己从前把石文海宠成现在这副无法无天的样子。
那一年,李秀莲学会了曾祖母忽高忽低的语调。
那一年,象河里开始长出了水葫芦。
我叫石敏。是石浩文的女儿,十七岁,在象城唯一的一所高中上学。从小到大,我对象城充满了恐惧。先是曾祖母忽高忽低的语调,然後是李秀莲忽高忽低的语调。我曾做过一个梦,梦里,我也像李秀莲那样唱戏似的跟石湘说话,石湘扭过头就没再理过我。
石湘的脾气像极了石文海。石文海从前被父母护着,骂不得的,而石湘被骂後会跳起来还嘴。十一假期里,石文海回了象城,李秀莲又叫媒婆给他介绍了一堆的女人。石文海忙着应酬那些女人,就没时间陪石湘玩那些过家家的幼稚游戏。于是,石湘就像个怨妇一样暗暗生石文海的气,见了石文海就板起张脸。
“你这脾气是哪来的?赶紧给我改掉!听见没?”石文海察觉到石湘的怨气後,用手指戳着石湘的脑袋厉声道。
石湘不理他,把头扭到一边继续玩她的毛绒公仔。李秀莲在一旁戏谑地说:“这脾气能从哪来?黄瓜的种子种出来的只能是黄瓜啊。”李秀莲认为她这话说得对极了,在一旁笑得极其开心。我也跟着笑起来,笑李秀莲太健忘,她忘了石文海这条“黄瓜”是从哪种出来的。
那天,石浩文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他问我:“敏敏,要不要来爸爸这里?爸这里过得可舒……”我不等他说完就说了声“好”。
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是这么迫切地想要离开象城。
象城就像一个外部光鲜亮丽,内部被掏空的蛇果,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光亮後也会开始慢慢萎缩。
过年的时候,石浩文,石文海,还有两个姑妈都回了象城。
那天吃年夜饭时,小姑妈刚满5岁的儿子扯着石湘的衣角问:“姐姐,为什么象城叫象城啊?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大象吗?”
石湘皱起眉想了想,答道:“嗯,可能吧。”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他们的对话觉得好笑。我还记得,两年前石湘刚学会识字的时候,扯着我的衣角问道:“姐姐,为什么象城叫象城啊?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大象吗?”
“嗯,好像是这样。”那时,我不大确定地回答石湘。
我也记得,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也曾扯着李秀莲的衣角问:“奶奶,为什么象城叫象城啊?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大象吗?”
“嗯,应该是吧。”那时,李秀莲也是这么不太确定地回答我。
“象城哪有什么大象啊。”曾祖母听见两个小孩子的对话後,慢步踱到我身边坐下,嘴里反复念叨着:“象城根本就没什么大象啊。”
过完年以後,石浩文带着我离开了象城。离开之前,石浩文问李秀莲:“妈,你要不要也跟着出去啊?外面那些大城市里……”李秀莲不等他说完就摇摇头说:“不用了,外面没自家里习惯。”
我始终无法理解李秀莲对象城的不离不弃。
我走的那天走过象河边时,李秀莲正拿着拖把拨开象河水表面长满的一层蓝藻,然後把拖把放入河水中荡涤几下再拿上来。现在的象河里长满了水葫芦,象河水已经不能再用来洗衣服了。可象城的人依旧不肯丢弃这条与象城一起走过百年光阴的河流,不洗衣服,但还可以拿来洗个拖把或是夜壶。
他们已经把象河融进自己和象城的生命里去了。
五六月份的时候,淮南的梅雨季节把象城笼罩进一片阴雨绵绵之中。而象城躲在几座山峦下,既不打伞,也不披雨衣,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又懒洋洋地闭上,照旧睡得香甜。
创作感言
16岁就像分界线一样,把我的生活分割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
在外地上小学的时候,我学着别人看小说,但总觉得情节不尽如人意,于是就突发奇想自己写一篇。写到一半的时候被老爸发现了,老爸很生气地骂我不好好学习,尽做不三不四的事。还把稿子全撕掉扔掉。我觉得委屈,但也无话可说。
上初中後,我的所谓写作永远跟语文考试有关。因为某次的作文莫名其妙地被老师当成范文朗读,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期待每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开始很用心地写考场作文。但不管怎样,总觉得缺少一种真实感。
16岁回到浙江温州後,我不得不承认,江南水乡的文化底蕴真的很深厚。最初我是非常不适应这种一条河、几座桥、岸边都是瓦房的充满水乡气息的生活。在一年多的磨合期里,偶尔会产生一种想把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作为一个故事的背景来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但想归想,我一直没有行动,直到进了学校文学社。
我笔下的象城,只要是温州人,就会知道它的本名叫白象,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有时候我会觉得它虚无缥缈得犹如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城市,历史沉淀下来的封建与迷信筑成了它残缺破旧的城墙。在厚厚的云层中,它仿若一团雾气似的忽隐忽现,极其诡异。有时候它又会像一块被水流击打得无比圆润的鹅卵石,呈现出水乡特有的柔软以及远离尘嚣的清新。我把这样的象城变成了几千个四四方方的黑体字时,心里顿时充满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编辑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