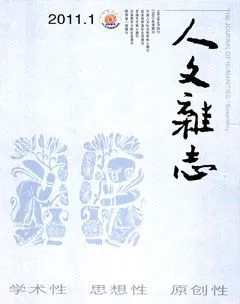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
2011-12-29雷钰
人文杂志 2011年1期
内容提要 丝路曾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融汇交流的商贸通道。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丝路 中国 伊朗 安息 波斯
〔中图分类号〕K373,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38-05
从中国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的陆上通道,是横贯亚欧的商贸大路。通过这条漫漫长路,最早向西方运送并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是中国丝绸,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路是由多条干道和支线排列组合而成,相当复杂。本文所指的丝路是途径伊朗高原、史籍中记载最多的主干道。伊朗高原扼守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是丝路的必经之地和枢纽。伊朗高原先后被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控制,精明能干的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成为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非常活跃的中间人。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从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页。
一、安息帝国时期
在中国史籍里,关于伊朗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传》。安息是中国对伊朗历史上的帕提亚帝国阿尔萨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6年)的称谓。安息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里海东南一带,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在波斯帝国和塞琉西王国时期是一个行省。公元前3世纪前期,一支属于伊朗语族的帕尔尼游牧部落从今锡尔河流域迁徙到安息。公元前247年,帕尔尼部落首领阿萨息斯杀死塞琉西王国的帕提亚总督,以尼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为都城,建立阿萨息斯王朝,是为安息立国之始。
安息建国后,多次挫败塞琉西王国的征讨,不断扩张领土,屡次迁都。阿萨息斯之弟和继承者梯里达底(公元前?-公元前211在位)迁都至里海东南的赫卡通皮洛斯。公元前192-公元前189年,塞琉西王国一再受挫于罗马,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一世(公元前171-公元前138在位)坐收渔利,乘机对外扩张。在东方,他首先进攻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巩固东境;继而西进,占领米底及伊朗西北部各省,并于公元前147年迁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公元前141年攻占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米特拉达梯一世是安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安息已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西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罗马对峙;东北与康居和大月氏相接;东南占有坎大哈,远抵印度边境。安息帝国的强大为丝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公元前126年),经大宛、康居和大月氏,抵达大夏,已接近安息帝国。“张骞追踪大月氏到大夏,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任务,却开通了丝绸之路,创造了文明交往的伟业。”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米特拉达梯二世(公元前123-公元前88在位)统治时期,对内进行军事改革,加强安息骑兵的战斗力,对外继续扩张。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甚至干涉塞琉西王国内政;向东攻占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附近),将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阿姆河一线。公元前90年,迁都泰西封(幼发拉底河东岸),安息帝国达到鼎盛,与东方的中国汉朝和西方罗马帝国并立。为了争夺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夺取通向中国商路的控制权,安息与罗马战事频仍。与此同时,安息却与中国互通有无,友好交往。
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300人使团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访问。公元前115年,汉使抵达安息,两国建立正式友好关系。据《史记》记载,“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回国时,安息王还将“大鸟卵(鸵鸟蛋)及黎轩眩人(罗马杂技艺人)献于汉。”《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2-3173页。 张骞“凿空”西域后,汉朝设西域都护(公元前59年),政令颁行无阻,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此后不久,汉朝政府陆续向葱岭以西的安息、奄蔡、条支、大秦、身毒等国派出使节。有时一年多达十余批,每批人数少则百余人,多者数百人。他们既是使节,也是商队,向外输出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商品,其中丝绸的销量最大。
与此同时,安息帝国也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公元84年(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苻拔;公元101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又遣使节来中国献狮子及条支大鸟(鸵鸟)。参看《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安息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918页。公元148-171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在中国传布佛教,在洛阳翻译佛经35部41卷,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在丝路上,安息人“善贾市,争分铢”,《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3896页。“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0页。甚至垄断丝路的中转贸易。《三国志》引《魏略》记载道:罗马“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得过。”《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四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61页。安息人为了操纵丝路的中介贸易,竭力阻止中国与大秦(罗马帝国)建立直接关系。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当甘英来到安息西界的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口,准备渡海西行时,安息人以路途遥远、风浪险恶为由横加阻挠,甘英遂中途而返。甘英虽未成功达到目的地,但他穿越了安息帝国,走过了大半段丝路,创造了汉代中国使者在丝路上的最远记录。“甘英是史书所载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此行意味着欧亚大陆东西两大帝国的第一次外交互动尝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就安息帝国自身而言,丝路不仅使安息人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丰厚,而且也是联系帝国东西部的一条经济纽带,带动了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帝国已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自东而西,丝路沿线的木鹿、番兜、埃克巴塔纳和泰西封等安息帝国的诸多城市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波斯萨珊王朝时期
萨珊王朝(224-651)又译萨桑王朝,即中国史籍《魏书》中最早记载的“波斯”。萨珊王朝得名于其创立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萨珊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3世纪初,其子帕佩克控制法尔斯省大部分地区,基本摆脱安息帝国的统治。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起兵独立,建立萨珊王朝。226年占领泰西封,并在泰西封加冕,自称“诸王之王”,以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建立中央集权的萨珊帝国。萨珊王朝的疆域扩大到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塔什干,在丝路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绸等货物,无论是越葱岭至贵霜帝国,还是越葱岭达大宛、康居,都要汇集于此,然后再西行至罗马。
贵霜帝国衰落后,萨珊王朝势力最强,在丝路上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不仅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国,而且几乎完全垄断着中国丝绢对东罗马帝国通过陆路的出口,从中取利。无论是东罗马人、突厥人、粟特人、阿比西尼亚人、曷萨人都从未能动摇波斯人的这种地位。东罗马帝国为了打通陆路商道,打破波斯对东罗马丝绸贸易的垄断,发展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先后与萨珊王朝在叙利亚、两河流域、亚美尼亚一带发生过9次战争。东罗马帝国甚至与突厥人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但都未能成功。针对丝绸贸易战争,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签署了种种丝绸贸易条约和协定。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织造业原料,几乎全部依赖波斯进口的中国丝绸。为了维持君士坦丁堡的丝织业和欧洲市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需求,5世纪后,在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边境上指定了许多丝绸贸易城市和关税机构。如: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尼西比纳,亚美尼亚阿拉斯河畔的阿塔克萨塔等。在转手中国丝绸的贸易中,波斯人实行高税率,即途经沙漠的各国商队和波斯湾的船队必须向波斯帝国支付高额过境税。533年,查士丁尼大帝付给波斯帝国1.1万磅罗马金币,以谋求开通东方商路。李明伟等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
波斯萨珊王朝之所以成为丝绸贸易中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一方面取决于其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与中国友好关系。5世纪后,波斯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菲鲁兹一世(亦称卑路斯,459-484年在位)及其子卡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统治期间,多次派遣使节访问北魏,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双方交往频繁。仅455-522年,波斯就先后十次遣使,来到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访问并奉献方物。北魏献文帝时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韩羊皮回国时,“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波斯国王派遣使节上书贡物,并致书孝明帝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