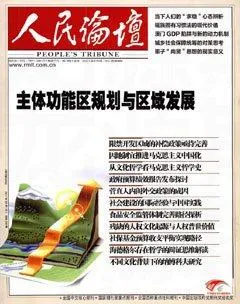残缺的人权文化起源与人权普世价值
2011-12-29曹慧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1年6期
【摘要】建立普遍的人权,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在多个文件中提及的人权教育目标。通过对西方人权根源的分析,从人权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人权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人类只存在具体的、历史的人权价值,人权价值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
【关键词】人权 人权文化 起源 普世性 差异性
人权及人权文化
人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被经常提及并被普遍认可。建立普遍的人权,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众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的那样,“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思想延伸了人类文明的阶梯和平台,并始终不断地得到发展。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这一主要由西方人编纂的人权宣言,却被冠以了“世界”之名。实际上,“人权”这一概念并非专属于西方文化,各国文化都为人权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中国先贤对于人权文化的贡献亦不可忽略,我们仅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答:‘爱人’”。这里所说的“人”,就是广义上的“人”,也就是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位之分,没有贫富之分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这一问题一直都饱受争议,而且尤其是人权的“普世性”问题更是被普遍争论。实际上,“人权”概念本身的发展就一直不停地冲击着人权的“普世性”问题。正如查理·夏顿所说:“残酷的真相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号称它没有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号称这种文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野蛮,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司法独裁,没有经历过任何对于那些政治和精神信仰不同的人进行迫害的过程。”人权问题也一样,从历史上来看,人权状况也是一直在不断地演变着、发展着。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通过对西方人权文化起源进行分析,阐述人权问题一直就不是普世价值,而是需要适应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的。然而文化亦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我们亦无法对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详尽的分析,本文仅选定从哲学、宗教和历史根源层面对西方人权的文化起源进行分析。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权文化进行审视
根据研究,我们发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亚历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中,在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教义中,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以及卢梭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能看到关于人权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希腊思想中的人权。许多人都认为人权概念起源于1789年,如著名哲学家昂德瑞·古奈尔就曾说过“人权概念在18世纪得以发展,并广为人们接受。”然而关于人权的文化根源,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颁布之前就已然存在。
号称人权理论始祖的柏拉图根据当时希腊城邦的状况,提出人类拥有“平等的灵魂”,他认为人类之间的差异只是社会分工的差异,并非灵魂(即区别于其他存在的人类精神)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人类在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上是平等的。然而同时他又把人类分成了哲学国王、公民和奴隶三个等级。在希腊城邦,平等并非原则,而与此相反不平等才是现实。因此我们发现柏拉图的所谓“死后的平等”只是一种保证现实中的不平等的一种工具,而在当时“不平等”才是普遍的。
亚里斯多德强调公民对于政治事务的公平参与权,他认为公民只有充分地参与政治决策,才拥有了寻求幸福的自由。然而亚里斯多德所强调的对于政治的自由参与,仅仅局限于公民这一等级,奴隶不享有任何的自由或平等的权力,他甚至于为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解。我们不能低估希腊思想对于现代人权思想的深远影响,因为正是古希腊思想为人类引进了人权理论的思想基础: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理性这一思想武器,在这一思想武器的武装下,人类开始了对于符合理性的人类本性的探寻。
然而在希腊城邦覆灭之后,当时的权力机构远离了希腊公民,每位公民都平等地参与政治变得不再可能。城邦也无法再回应每位公民的需求,人们必须学会“自给自足”。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寻求到他们所需要的庇护时,人们就必然会寻求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基督教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基督教和人权思想。在基督教中,人与人之间没有职业、性别、年龄的差别,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此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整个基督教文化中深入人心。此外,基督教的神圣著作《圣经》更是为人权思想的孕育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发现基督教对于人权的发展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它限制了世俗的专制政府,它提出了人类尊严的理论,它创造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然而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教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并未对于人权思想的发展产生足够的社会效力。因此,从一定角度上说,基督教的发展其实是相对于古希腊时期人类理智的一种倒退,但是面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当时的权力机构远离公民,很多问题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解决,人们也就只得寻求超自然的力量,这也就变得合理了。直到启蒙时期,理智和自然才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理智才再次建立起其主导地位。
启蒙时期人权思想的哲学根源。启蒙时期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对于人权思想能够深入人心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西蒙妮所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全书中都在考虑自由和法律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确,孟德斯鸠认为人类享有的自由就是从事法律所允许的任何事情的自由。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的根本权利,当然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也清晰地描述了过度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也是遗害无穷的。孟德斯鸠认为只有建立有效的政府方能真正保障人类的自由。因此正如哲学评论家德瑞尼所说“孟德斯鸠就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特权的捍卫者。”
相对于孟德斯鸠,启蒙时期的另外一位杰出代表卢梭的理论对于人权的捍卫就更加彻底。卢梭为“天赋人权”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假设。卢梭提出了人类“自然状态”的假想,卢梭认为人类生而平等和自由,自由和平等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人类的本质”,因而人类从本质上说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体结盟成为主权者是一个由个别性向普遍性转化的过程,而只有合乎“公众意愿”的政府才是良好的政府。“政体,诚如人的肉体,在它出生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它内部有着它最终消亡的原因。但肉体和政体也都有着或强或弱的结构以使它保留或长或久的时间。人体结构来自天然,而国家结构是一种艺术。”因此,各个民族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确定相应的政体。
启蒙思想如此深入人心,当时的人们倍受影响,以至于欧洲和美洲各国都纷纷地通过革命的形式与旧制度进行抗争。但是就是在被称为进行了最为彻底的革命的法国,甚至在《人权宣言》颁布之后许多年,仍旧要求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必须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公民”,因此也就没有人权可言。
人权思想的起源有重要的文化根源。通过古希腊文化理念,我们明白了人权是理性的产物。通过基督教文化,我们了解到人权是人类美好的追求,它是人类超越自然的更高层次的理想。通过启蒙思想运动,人权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一种世俗的宗教。人权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适应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况下的人权文化和状况才是最为合适的。
人权是普世性的吗?
人权是普世性的吗?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到,但是由西方各国所提出的人权“普世性”问题经常受到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质疑。人权的发展如果没有各个民族的参与是遗憾的,但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迥异,那么不顾各国的特色,在所有的国家实施统一的人权标准现实吗?有学者认为“人权的全球化秩序的乌托邦,仅仅是空洞的幻觉”,哲学家马母德说道:“不能要求所有的文化都按照西方国家两个世纪以来设定的轨道运行,如果这样,就无疑是将所有的文化都禁锢于西方模式之下。这就等同于新殖民主义。”他还指出西方国家否定其他国家的文化,将自己的人权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强加于其他的国家,这就相当于否定了各种文化中最为宝贵的本质:独创性。人权,诚如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产物,渐渐地变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下,人权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实际上正是文化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因此,在现代人权发展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承认并且确保文化的多样性,人权的普遍性方能发现实现它的途径。在人权的国际化发展中,对构成全球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内部原则和程序,做出重新协调,从而才能保证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下的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重新协调必须是在“新的包含承认普遍原则的同时,允许文化上的区别和特色的观念前提上”。
因此对于文化的差异性的尊重,可以被认为是人权价值的财富而并非对于人权实施的一种阻碍。对于人权的理解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人生而自由,人生而平等,人权思想是世界性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然而对于人权思想的具体实践却不是可以实施万用准则的。不同的文化圈对人权有着不同的解读。因而在与人权文化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最适合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国度的人权理念。在实践中,对于人权问题,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社会环境甚至自然环境中,人们会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实施标准。(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