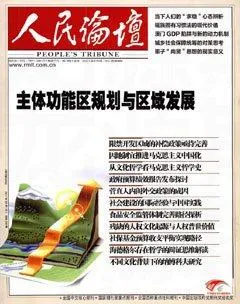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认同
2011-12-29杨川丹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1年6期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近年来广受关注,他们与城市社会认同有“内卷化”的趋势。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解决途径,“内卷化”对于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扩大。正因如此,城市政府和社会应给予这一特殊群体合理的地位和保障,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并建立起积极的城市社会认同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社会认同 内卷化
问题的提出
两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认同。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即“对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价值观念、市民群体的日常运作逻辑等的赞同、认可、渴望与同化,并将城市人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和评价标准”,①就会更多地将自己归类于城市人群体,藉此获得自尊感和归属感。第一代农民工被称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老实、本分、文化层次低,迫于生计才会选择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一旦他们有了生活上的保障,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父母所面临的不同情况是:文化程度相对高,择业期望也高,更注重现代的物质文化需求,具备更多现代的自主和自觉意识,但是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在吃苦耐劳方面却远不如上一代农民工。
所谓“内卷化”。“内卷化”的概念最初是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被用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因为其特殊的体制背景形成了除“城里人”和农民以外的第三大身份群体——处于城乡两极之间的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内心不愿意归于农村一极,并憧憬着城市的一切,但是又由于各种体制、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阻碍而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现代城市,于是便出现了梦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那条横亘于他们和城市社会之间的“鸿沟”,使得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度没办法发展到一种他们所渴望达到的程度,趋于“内卷化”的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内卷化”分析
外部的不认同——城市社会的“排斥”。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等,②这些排斥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流关系网络对之的不认同。
大量的现实证明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了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成为事实上的外来人。户籍制度的存在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制度性排斥,农民工不能取得城市的户籍,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城市所接纳,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也受到了排斥。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受到了排斥,即社会关系网的排斥,“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③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农民工造成了隔离和排斥,还引发了城市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的排斥,人们总是把城市社会治安恶化、交通拥堵、环境卫生等问题归罪于农民工,并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是政治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呼声,足以体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尴尬境地。
自我的认同——共同体内部的“抱团”。美国学者Frank Parkin认为,集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另外一个“共同集团”,当前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就是一种由城乡二元体制所引发的集体排他现象,城市社会的不认同,迫使农民工转向寻求自我共同体的认同,这是认同“内卷化”最直接的体现。
其实严格来说,“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社会群体,而是因为他们的共同际遇而存在于政策文件、媒体报道之中的称谓,这种身份是外部社会强加的,自己没有选择余地,故而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但是,相近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状况、外出动机和经历,以及在城市遭受到的相似境遇终究还是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城市里的“难兄难弟”。社会交往理论认为,“交往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之上,相近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比其位置相差大的人们间的交往要普遍些”,④“同一个阶层的人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⑤农民工就是依靠那些“同质性”建立起彼此的交往,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与城市社会隔离的状态。
这种共同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绝对要比老一代农民工大得多。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无根的一代”,既没有“乡土情结”,也因为城市的排斥没能培育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亲近感,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便构建一个共同体,通过自己所认同也被认同的群体来维护自尊和实现自我的价值,不能不说是平衡失落心理的有效途径,这个途径应可以被理解为“抱团”。2010年底,南方都市报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果》中提到,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在遭遇不公后,选择集体式自力救济(联合工友或老乡想办法)占9.2%”,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抱团”维权倾向。“抱团维权”的想法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从个体走向共同体的趋势,他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个体,他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忍耐,但作为共同体,他们的力量将不容忽视。另外,近年出现的农民工抱团创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但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也可以解释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地方以地缘为基础的“帮派”层出不穷的原因,在受到城市社会歧视的情况下,农民工交往的圈子相对局限,他们所组成的共同体还是相对狭隘、低层次,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受同辈群体的影响特别大,极容易导致“抱团”行为的扭曲、变形。
对外部认同的不稳定——行为逻辑中的激烈反应。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工主动或被动地形成自己的认同方式,而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度又会直接影响这一群体的行为逻辑和态度取向。相关的研究显示,第一代农民工是亲身经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过程的,对于城市社会不公平和歧视往往比较容易接受,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并不预期与城市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因此他们通常有比较平和的社会态度,其行为也是相对平和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有向外、向上拓展的迫切愿望。但是现实总是残忍的,城市主流社会的排斥最终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转向内部群体寻求认同,从而非自愿地被沦为“城市边缘人”,这也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社会原本持有的强烈而积极的认同意识,变得既不明确又不稳定,更有甚者“由爱生恨”,内心充满“凭什么”的愤懑心态,这种心态如果压抑得太久,很有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上述三个层面的认同演化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认同不断“内卷化”和复杂化的基本逻辑。
结 语
城市化进程中,“在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一链条上,伴随的是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的过程。”⑥社会认同是实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经路径,目前我们应该正处于面对这个问题的阶段上。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社会认同“内卷化”趋势的加强是两种力量“内外夹击”造成的:外部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内部共同体的自我“蜷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强烈的认同期望,像一个内部不断充气的气球,在“内外夹击”下,其内在张力得不到释放,必然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所以社会认同的实现也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可、赞同,还必须包括外部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吸收、接纳。笔者认为,这种互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制度来达成,比如创造温馨宽容没隔阂的工作、生活环境,为外来民工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理解城市、热爱城市,促进和保护他们积极的社会态度;再深一步比如积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门槛,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性障碍;更深一步比如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接纳农民工,消除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就业权利、教育就学等方面的一系列待遇差别,实现外来人口相关权利的促进和保障……这样才能逐步从根源上消除“内卷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认同城市并融入城市。(作者单位:中共衢州市委党校)
注释
①李超海,唐斌:“城市认同、制度性障碍与‘民工荒’现象——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实地调查”,《青年研究》,2006年第7期。
②潘泽泉:“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③⑥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
④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⑤赵树凯:“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