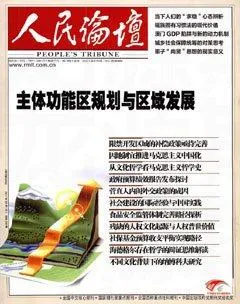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基层民主治理
2011-12-29马珂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1年6期
【摘要】坚持农村基层民主治理,对于新形式下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调查,成都市周边农村的民主治理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和经济发展压力下的乡、村关系是主要原因。为此,可以从提高农民自身利益表达能力、再造有效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关键词】城乡统筹 基层民主治理 监督机制 议事规则
目前,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头等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民主治理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制度保障功能。一方面,它可以保证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得农民自身的意愿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防止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结构性的损害。2007年,成都市和重庆市被中央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成都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新一轮的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作为试验区的成都无疑走在了前列,成都周边农村基层民主治理领域所遇到的问题,应该说在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2010年10月,我们组成研究小组,以成都周边农村为对象,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抽样调查。
研究方法与调研结果
调查组随机选取成都中心城区以外的两区两县中的八个村作为调查地点,调查对象为村民。我们在每个村针对村民发放问卷2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份。对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后,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的数据来反映目前成都农村民主治理的现状:
民主治理的客观情况。我们设置了两个问题来反映调查地区的民主选举情况。当问及“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是否由村民直接产生”时,26.32%的受访者回答“是”,55.79%的受访者回答“不是”,回答“不清楚”的占17.89%。在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中,实行等额选举的占11.58%,实行差额选举的只占37.89%,其余的回答“不清楚”。大部分受访者(55.79%)表示他所在的村不能保证每年召开一次以上的村民会议,而多达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很少或从未参加过本村重大事务的决定。当问及所在的村村务是否公开透明时,只有30.53%的受访者做了肯定的回答,而其余的受访者(占69.47%)则表示村务不能做到透明公开,或者根本不知道。在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和监督这一项上,60%的受访者表示他所在的村没有这样的渠道,15.79%的村民表示不知道,只有24.21%的村民给予肯定回答。
民主治理的主观绩效评价。首先是受访者对现任村干部的评价。在问及“村干部对解决您和您家庭的困难是否有帮助”时,多达73.68%的村民认为很少有帮助或根本没有帮助,只有不到9%的村民认为有很大帮助或有较大帮助。当涉及对村干部任职动机的评价时,多达51.58%的村民认为村干部任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有17.89%的村民认为他们任职是想为村民服务。
通过了解受访者对下一次选举的预期来反映村民对本届村干部的评价。当问及“在下次选举中,您是否会投现任村干部的票”时,有24.%的受访者表示会投全部或会投其中的多数,有35.78%的受访者表示只会投其中的少数干部或一个都不投。如果除去没有作出决定的受访者(31.58%),应该说现任村干部的支持率还是较低的。
在被问及“农村民主治理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意义”时,仅26.32%的受访者认为有意义,认为意义不大和没有意义的受访者占到了近58%。在被问及“您是否比以前更关心村委会的决定”时,有40%的受访者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仅仅有2.20%受访者作了否定的回答,令人疑惑的是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57.80%)表示无所谓。在作肯定回答的受访者中,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都是“村委的决定比以前更关系到自己的利益”;而在回答“无所谓”的受访者中,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是“关不关心都一个样”。在被问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您认为是否还需要政府的规范、监督和引导”时,高达77.80%的受访者表示需要。
原因分析
基于上面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调查地区,农村民主治理的水平不高,无论是选举、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村务的监督,都无法达到民主政治的要求。村民对所在村的民主治理绩效的主观评价也偏低,对现有村委干部的认同度普遍不高。基于相关数据以及研究小组与村民和村干部展开的座谈,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成都农村民主治理现状不尽人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缺乏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主动的角色。政府往往在市场培育、招商引资、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优化上占据主导地位。与政府的主导地位相应的是,乡村和村民的自主性将会受到一定抑制。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将不是主要体现在“自我服务”和“自我决策”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在民主监督这一环节上。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在乡村日常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中,村民进行事中和事后的监督缺乏有效途径;而在集体经济的管理以及土地的流转过程中,村民也缺少参与和监督的途径。其原因在于:第一,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现行法律法规还有待改进。第二,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依然是成都周边农村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严重地制约了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转。①因此,仅仅依赖农村基层内部的监督机制,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实践证明,试图通过建立监督小组、村务监督委员会之类的村级监督组织,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实施民主监督,这种做法不仅难以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目的,而且有可能增加农民的负担。②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共谋关系继续保持。县乡两级政府与村委之间的共谋现象是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农村税费取消了,但新一轮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的任务又成了新的诱因,它使得这种共谋关系继续延续,甚至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许多接受调查的村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情况就是,许多村在选择村干部上都受到了乡镇一级政府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全国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它虽然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在现阶段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③乡镇一级政府直接面对农村工作,有很多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另外,就目前而言,省、市、乡镇各级政府都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在农村基层开展大量的工作,比如土地的集约化、招商引资、开发项目等等,这些工作不可避免会牵涉到每一位村民的利益。这其中有大量的、琐碎的且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和抵抗的工作要做。为了高效地推进经济工作的进行,客观上来说,乡镇政府需要将村一级的管理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来作为村民利益代表者的村干部却与乡镇干部结成了牢固的同盟关系,共同“对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村民。
政策建议
改进农村内部的议事规则。农村的民主决策一般是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来体现的。然而,现今农村在做出有关决策时,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会议发起者的村委会不愿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了能快速作出决定提高工作效率,许多决策在村委会内部就做出了;二是农村开会难,会议流程不规范,很难达到民主决策的效果。因此,积极地引入新的民主治理机制,以适应目前农村社会的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组织和壮大农民自身的力量。根据调查,目前成都周边农村村民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受损、利益表达缺乏途径的现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民大多以散户生产经营为主,与强势的村委和上级政府比起来,他们的力量非常单薄。遇到利益受损的情况时,单个的农户往往由于力量单薄而选择沉默,或者走上非常规的意见表达途径(比如集体上访)。因此,组织和壮大农民自身的力量(比如农会)、将农会组织之下的农民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纳入到现有法律体制之内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倾听和更多的活动空间,将会有利于农民群体的利益表达。
再造农村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村委与乡镇以及乡镇上的区级政府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使得这三级政府(组织)之间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很难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反,村民对区级以上的政府还是普遍存在信任感的。政府的层级越高,受到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形压力(具体发展指标)就越小,也就越容易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和公平公正上保持平衡。此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第三方监督是由媒体、社会独立人士构成的志愿团体,负责对农村中的事务进行定时的、独立的了解、评估和监督,从而形成一股独立于各级政府和农民自身的第三方独立监督力量。与体制内的监督制度比较起来,它避免了农村居民身处熟人社会之中面对权利与利益之网时的顾虑,也摆脱了政府在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之时出于自我目标和利益的考量。(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吴毅:《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②卢福营:“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③谭秋成:“农村政策为什么在执行中容易走样”,《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