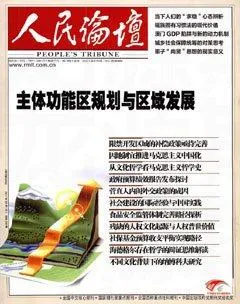主体功能区建设任重道远
2011-12-29踪家峰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1年6期
主体功能区建设这种新的区域发展思维,透露出许多新的发展理念。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描述了一个崭新的美好愿景,如何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然是个难题,甚至是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实施主体和途径、评价机制、各规划的协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区划的科学性和是否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等关键问题值得研究。
主体功能区从2005年的概念到2010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与2011年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之中的国家战略,成为“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人口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建设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规划、粮食生产规划、交通规划、防灾减灾规划等在空间开发和布局的基本依据”,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区域开发和地区发展的新的思维。
新的区域发展思维透露出新的发展理念
这种新的区域发展思维,透露出很多新的发展理念,表现为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发展顶层设计理念;区域差异化发展与有限开发理念。特别是后两个理念尤其值得注意。
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区域发展也需要顶层设计,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全国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陆续续推出了以不均衡增长为特点的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滨海新区开放开发、海西经济区发展规划等,这些战略的特点就是对某一局部地区进行设计,而主体功能区战略从全局的角度对重要的区域发展问题进行顶层设计,这是在以往的区域发展中没有的现象。
区域差异化发展与有限开发的理念。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千差万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往往忽视了这种差异性,一刀切处理各区域问题。尤其是共同的区域发展评价机制造成了GDP崇拜,带来了千城一面,所到城市处处皆是新加坡,各地区发展缺乏特色。主体功能区强调的是区域分工和各区域特色发展,这种特色发展的实现是通过不同区域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发展重点来保证。主体功能区还贯穿着有限发展的理念,有限发展不是不发展,而是发展要综合考虑各种制约条件,发展要各主体协调,各区域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
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描述了一个崭新的美好的愿景,如何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然是个难题,是个艰苦的过程,甚至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其中又有6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即实施主体和途径问题、评价机制问题、各规划的协调问题、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问题、区划的科学性问题和是否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问题。
实施主体与途径问题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利用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九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实施,这里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主体功能区划分是适应现行体制还是现行体制适应主体功能区而改变,特别是财政体制,现行的分税制体制自1994年以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存在着很多弊端,主体功能区要求建立不同的评价机制和转移支付体系,而现行的分税制体制难以适应这种要求,而改革分税制体制是牵一发动全身,本身也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主体功能区的九大政策工具分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这些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又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弄不好演变成各部门各地区为争取利益而进行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实施主体之战难以避免;相似区域的政策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同一个地理单元却分属于不同省区,如三江源地区,如何适用政策;主体功能区规划属于开发强度的规划,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的区域本身又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不增加GDP靠什么来支撑整个发展?会不会在新的不平衡基础上更加不平衡?对于前两个问题,本身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规划的实施过程就是利益调整过程,需要综合考量。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同一地理单元适用相同的支持政策,不管所处的行政单元如何。对于第四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由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转移支付来完成,由于中西部的数省GDP才能抵得上东部如苏州市的GDP,可以考量完全放弃GDP考核。
评价机制问题
主体功能区的评价机制是关系到主体功能区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建立一个科学的差异化的动态评价机制成为重中之重,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就会带来发展结果。以GDP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为增长而竞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但这种增长是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评价的关键是评价各地区的领导人,目前很多城市发展换一个领导就换一个规划,领导行为本质上决定了规划实施的力度和风格,而领导是跟着评价机制走,有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就有什么样的领导。所以重塑各地区的评价机制成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评价机制首先要明确各地区的主导属性,到底哪些地区属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只有科学的主导属性才能有理由使不同区域各司其职,遵守各自的开发强度;其次,建立差别化各种侧重的评价体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域过于考察生态环境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过于考察GDP都同样有害,现存的发展模式中,许多大城市热衷建设生态城市、中心市区高的绿化率降低了土地的利用利用,既无公平又无效率,成为城市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盲目考察GDP也会带来种种灾难性后果,我们建议优化开发与重点开发的考核机制为GDP、生态双维考核;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为生态环保一票否决制度;再次,评价机制的调整机制,主体功能区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今天的重点开发可能成为明天的限制开发,所以要与时俱进地推进评价机制的动态调整。应该看到我们官员评价机制中的对上负责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评价机制的特点,从长远看,如何引进社会评价乃至居民评价也是调整官员评价机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各种规划的协调问题
中国的区域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比较复杂的体系,可以称之为区域规划丛林,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海西经济区战略、皖江城市带等等,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土面积,每个规划都有一套发展重点和支持政策体系,很多地区面临着多套区域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叠加,甚至有些规划彼此有矛盾之处,比如西部大开发与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大多数地区都属于主体功能区的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这些区域如何实现西部大开发中的大开发呢?我们认为这些规划应该互为补充,不可分割,但需要自我完善和规划之间的协调,不能规划之间相互打架,实施起来不知所措。首先要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地位,是其他规划的基本依据;其次,要对现行规划进行梳理、精简,确定核心规划和一般规划,否则多如牛毛的规划往往成了墙上挂挂图上画画了的流于形式了;再次,对现行的各种规划的支持政策进行清理,哪些政策需要加强、哪些政策需要改变、哪些政策需要废除,有个比较明确的说法,使得每个地区对本地区适用政策心知肚明。
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问题
作为一项战略性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贯穿的思想还是解决区域发展差异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政府主导理念,在整个规划中着重体现了政府规制和政府支配的思想。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而且事实上政府也起到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但是,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需要加强,政府支配资源数据巨大、上游产品、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等没有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进程并不是区域经济差异、粗放式增长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与此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和不到位才产生了许多区域问题和区域大战。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着重推进:其一,放松土地的用途管制,主体功能区将全国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三类,每类都设定相应的土地用途进行土地用途管制,对于生态功能区进行土地用途管制是应该的尤其是生态脆弱区,但是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地区应该放松土地用途管制,主要发挥市场的力量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无论是城市化地区还是农产品地区城市化进程都处于加速期,进行土地用途管制无疑会降低这种进程;其二,推进上游产品、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市场化进程,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进程缓慢,生态环境利用与破坏的成本太低,这也是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反而落后所谓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三,推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的城市化过程,特别是促进人口的沿海化集聚进程;其四,推进横向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对于主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可以采取谁受益谁出钱的措施,建立流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交易市场。
功能区划分的科学性问题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四类,并赋予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三类具体内容。这种划分的依据有3个,即现有经济开发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未来发展潜力,如何评价这三个依据成为划分的科学性最大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北京市的人口控制,1000万人口北京没有崩溃,2000万也没有崩溃,3000也不会崩溃,所谓的科学的预测成为笑谈。所以如何精准划分这四个类型城市主体功能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这四个类型中,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可以分成一组,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可以分成另外一组,我们建议把前一组称为集约发展组,后一组称为生态发展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东部地区的集聚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都是粗放式增长,都面临集约发展问题。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如此,中部地区也是如此。正因为集聚效率高,人口的沿海化进程仍在加速,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不仅需要优化发展而且在未来数年内还是重点开发区域,而相应的中部地区则会成为次重点开发区域,优化开发与重点开发并存于东中部地区,截然将两者分开没有意义也难以实现;生态发展组包括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区,成为我国生态资本的主要富集区,主要承担保障生态安全的任务,本质上都是生态功能区,不仅是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等需要禁止开发,而且特别是生态脆弱区和关系到全国水资源供给的地区都应列入禁止开发区域,而不是限制开发。
主体功能区区划原则为以县为单元、国家定区域、省级定范围,这本身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一县之内亦有差别,可能并存主体功能区的四个类型,当然以更小的地域单位为划分单位可操作性又成问题;省级定范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每个省的范围划定必然与其政府意愿相一致,与官员的偏好相一致,如何平衡地方利益与主体功能区要求的全国利益确实是摆在主体功能战略面前的一项重要难题。
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说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发展道路,不如说在尽量少走弯路上进行了探索。中国改革开发30多年是经济迅速发展的30年,同时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的30年,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或者不治理成为现实,并没有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新路,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生态环境之路更为曲折成本也更大。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几乎难以避免;二是中国的粗放式增长和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使得一切向GDP看齐,为GDP而竞争的越演越烈的趋势使得环境问题雪上加霜,绿水青山从此与我们相隔,成为争取金山银山的惨重代价。已经污染的只能去治理,没有污染的不能污染,怪圈需要打破,弯路不能再走。主体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可能使之成为现实,而实现目标关键措施是生态补偿、生态移民和继续推进人口的沿海化进程。(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