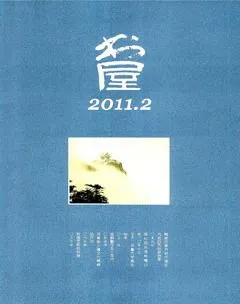1948:齐鲁大学南迁始末
2011-12-29岱峻
书屋 2011年2期
一
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1864年,来自美国北部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借用登州(今山东蓬莱)城里的一所“观音堂”开办义塾“蒙养学堂”,1872年定名为“文会馆”。1902年,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学堂”。1907年,迁至潍县东郊的广文学堂,与青州的神学堂、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合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新建门筹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新址,三年后校舍落成,建有麦柯密古办公楼、考文物理楼、柏尔根化学楼、奥古斯丁图书馆、郭罗神学楼及康穆礼拜堂等。1917年9月,齐鲁大学在济南正式开学,文、理学院位于新建门外,学制四年;医学院及附属齐鲁医院则在新建门内,医科七年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鉴于齐大教学水平“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1924年,加拿大政府准予立案,批准齐大具有学位授予权;医科毕业生授予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医学博士”学位。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收回“教权”。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齐大董事长兼名誉校长,聘朱经农为齐大首任华人校长。不久,校长职由齐大文学院院长林济青代理。1931年12月,齐大获国府教育部核准立案。1935年刘世传接任校长。他与前任林济青一样,广揽人才,如国文系主任郝立权、社会经济系主任余天麻、教育系主任陈祖炳、化学系主任谢惠、物理系主任王长平等。尤其重视发展社会与人文学科,创办国学研究所,国内知名学者如墨学大师栾调甫、作家老舍、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大还办有影响国内外的学术刊物《齐大季刊》及《国学汇编》。1936年在校生人数达到六百人。有人说,“齐大从此进入了名牌大学之林”,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有“南齐北燕”之谓。
抗战期间,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仍然不低。据毕业生曹伯恒、梁鹏回忆:“我们的校长,鼎鼎大名的国际法专家,借居华西大学行政大楼的一角办公,与我们稍有接触的机会。教务长为哈佛出身的汤吉禾博士,文学院院长为江之泳博士,理学院院长为留法的薛愚博士,医学院院长为侯宝璋博士。”“齐鲁师资雄厚,……化学系主任刘遵宪刚从美国MIT及斯坦福大学深造,途经香港到达成都,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刘教授就为我们讲授有关原子能的理论及应用,诸多名教授所开课程并没有落后于时代。”
1945年10月1日,齐大在济南原址复校。但华西坝的齐大仍在成都招生,一直坚守到1947年夏。据统计,齐大1947年上半学期的在校学生为四百四十二名,其中文学院一百零五名、理学院一百二十三名、医学院二百零三名、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十一名,教职员工七十人。此时距离1948年春还仅只有一个学期,也就是说齐大师生席不暇暖,又得成为流浪人。
二
吴克明是齐大最后一任校长。按前两届校长刘世传的女儿刘贞一的说法,他是孔祥熙的女婿,因由这层关系他才当上齐大校长。此说或有些意气用事。吴克明本质上只是一个学者,他齐大毕业,留校在化学系任教。1923年秋被校方推荐到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任教员兼教务主任,此校校长即是山西太谷人孔祥熙。1929年,由铭贤学校资助,吴克明前往欧洲各国参观,并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化学,获硕士学位,曾发明三种镉之磷酸盐,1931年归国后继任铭贤学校教员兼训导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吴克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化学组主任,从事中药提炼的研究和防毒设备的设计。1938年起,返铭贤学校任教务长,他带领师生迁校,先西安,后沔阳,最后落脚四川金堂,学校更名为“太谷铭贤学院”,吴克明任院长。1944年春至1945年夏,他又应聘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技术专员,从事研究解决抗日后方食盐不足的问题。
此时的齐大已人多事之秋,1943年冬校长刘世传辞职。继任者汤吉禾仅上任一年多即被学生赶走。1945年秋由齐大校董会与校友会共议,请回校友吴克明出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吴克明主持了齐大回迁济南复校的工作。他是个技术型的人才,虽与孔祥熙的关系很深,但并未在军政界谋过一官半职。1947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拟任命精通英文的吴克明为少将衔“绥署”副秘书长,吴克明坚辞不就。冷眼看官场,热心办学堂。原齐大学生束怀符曾回忆吴克明“爱生如子”的往事:
张聿修是济南市中学我的同班同学,1946年与我同时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当时由于功课负担重、营养不足,1946年冬患结核病休学,1947年夏病重住齐鲁医院,后去世。他父亲是济南邮局职员,经济负担重,欠医院的住院费未交。聿修的男友(也是我们市中的同学)从天津赶来,提出想给聿修组织一次追悼会以安慰家长,并希望能减免她的住院费。我和文学院的骆瑞舟校友去找吴校长说要求。他沉思了一会说:“这个学生死得可惜,你们的要求我想办法,下午听通知。”果然下午通知第二天下午四点半在康穆堂开追悼会,由我们负责组织安排,他主持,张聿修的住院费不用交了。实际上我们考入齐大的中学校友仅二十多人,校长在冷冷清清的小追悼会上做了主持并致悼词。
高圣选是考入齐大理学院的我们中学同学,为人敦厚,学习努力。有一天(1947年),骆瑞舟找到我说高圣选家里来说他被警察抓走了。因为他家在解放区,老家经常来人要报临时户口。前天又来了人,去报户口时警察从他家发现了“北海帮”,说高通共,就抓走了。我们三个同学去找吴校长,说明情况,请吴校长把高保出来。吴校长听后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应该保他,他为什么那么粗心,我去想想办法。”过了两天看见高又回来上课了。听骆瑞舟说高也没有去向吴校长道谢。我上下班在路上遇见吴校长,他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三
1948年6月3日,华东野战军陈毅部攻占津浦路之大汶口及界河,一周之内连克曲阜、邹县和龙山等地,济南已为孤城。处于圩子墙外的齐大校园已成了王耀武的前沿驻军兵营。就在济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为躲避战争伤亡,校董会在董事长孔祥熙的主持下,决议由校长吴克明主持齐大再次迁徙。当时济南除总务长杨德斋留守和农专几个学生没走之外,全校四百多名学生大都随校迁到南方就读。据亲历者马挺光、杨懋春、褚承志回忆:
1948年7月,在济南解放前夕(1948年9月28日济南解放),齐鲁大学主要负责人及新来执教的内科教授张光璧,谋划向南方迁校,当时驻济南城郊的中共济南市委获悉后,派人与齐大杨德斋博士联系,阻止齐大迁校,并要保护图书仪器,勿使运往江南,结果阻止未成功。
民国三十七年春,国共战事已逼近济南城下,齐鲁大学为躲避战祸,于是决定再作一次往南迁校的举动。先是派人到长江以南去考察,接洽可以把学校迁去的地点。考察接洽的结果是浙江杭州郊外的云栖寺。
学校包了两架民航飞机,将决定南迁的教职员与眷属,连同所带行李,由济南空运到青岛。两架飞机两次飞航就完成这项空运。到了青岛后,有亲友者往亲友家暂住,无亲友者被安排在几所教会中学宿舍内。在青岛停留了十天,使大家有与亲友相聚及告别的机会。然后全体登上预先订妥的轮船,直航上海。到上海下船后,在安排好的旅馆中休息一天,翌日即乘火车去杭州,由杭州市再租大型汽车进入云栖寺。学生们的旅行也是取这些方式,经过这条路线。
校本部与文学院、理学院则在吴克明校长与孙恩三教务长领导下,坐飞机到苏州,从苏州坐火车迁到杭州。到杭州后,虽有当地基督大学尽量做各项协助,但住的问题仍不能解决,于是宿舍选在杭州郊外两公里的云栖佛寺。去杭州的学生是二百八十名,其中女生九十九名。教职员五十五名,连同眷属共一百二十名,大家挤住在云栖寺。
医学院选择了另一处南迁地。马挺光、彭万程、段惠灵等回忆:“医学院师生及图书仪器、病理标本、简易病床等均乘飞机至青岛,转乘二战后退役的美军登陆艇由海路到福建马尾港,再乘木船逆行闽江,到福州码头。医学院基础科学生在福州苍前山协和神学院开课及住宿,临床科学生则在福州南门协和医院开课,宿舍在乌山路一教会大院内。”
至此,齐鲁大学再一次成为流亡大学,并分置杭州和福州异地办学。校长吴克明则于急遽动荡的时局之中,奔波两地。
四
流浪中办学,艰辛备尝。时任齐大文学院院长的杨懋眷回YVt25svo/5QnnNbmXByFH/T796IjHECZrWvPZ+tTGvU=忆:
齐鲁大学迁到云栖寺后的情况可以分三方面说。论教学,可以勉强进行。寺内有不少房间稍事改装后,就可以在其中进行教学,也可做办公室。需要做实验或试验的教学比较困难。幸该时齐鲁大学的经费尚能由英美与加拿大等国源源汇到,教职员薪津得按时发给。在杭州市的国立浙江大学却因政局紊乱,其教授领不到薪水,于是有人愿意应云栖寺齐鲁大学之聘,为其兼课教授。
吴克明从浙江大学请来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束星北、王承基、谭其骧等一批名教授来为学生上课,让流浪中的学生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当年理学院的学生苗永明回忆:
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两位顶尖的教授苏步青和陈建功,都是全国数学界的泰斗。我有幸做了他们的学生,记得陈建功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复变函数论课。我们从微积分步入复分析,一时还适应不了,就去问沈庆辰。她习惯性地歪着头笑着说,我也听不大懂。陈建功教授只好为我们改讲高等代数,并叮嘱我们要买吴大任译本,不要买另一位教授的译本……
物理系的几位著名教授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也来到云栖。束是齐大校友,曾在齐大物理系读过一年。他前额宽大,面色殷红,气宇轩昂,个性刚直,声如洪钟。为了抗战,他弃教从军,研制成功雷达后,又回浙大任教。他与当时已经是著名核物理学者的王淦昌教授私交甚笃,在同学中流传着束对rKUv/lhxFgROQ/W8yfOnccEcNo6V3bHEShz9nmE90o4=王说“诺贝尔物理奖应该属于你”的故事。……多年以后,杨振宁说过:“吴有训、赵忠尧、王淦昌,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物。”……在三位大师的教育和熏陶下,高年级同学收获多多,其中四年级学长苑之芳较为突出。曾在云栖寺读医预科的王裕民和张正荃回忆
医预科附设在理学院,有预科一年级及二年级两个班。预科一年级多是由上海等南方考进的学生,人数较多。至于文理学院,除药学系外,还有其他系的同学。著名教授有化学系刘遵宪、生物系的秦西灿、药学系的刘国华等。因为是教会学校,自然有外国老师,如教我们英语的裘柯农老师,对教课很认真。教室因陋就简,能开的课都开,能做的实验都做,有生物、化学、药理等实验室。校长吴克明先生不常在校,教务长孙恩三教授住在校内,掌握大权。他要求很严格,考试不及格者留级或退学。
我们在那里(云栖山上的云栖寺)读三年级。刚从美国回来的李炳鲁教授开课讲授毒物分析。当时这是一门很新颖的课程,国内没有参考书,李教授讲授内容很丰富,要求将英文讲义先打印成稿,人手一份。庙里没有印刷厂,我们又没有经费来源,只好由班里自行解决讲义的打印。
这群异乡客就像钻进沙里的鸵鸟,一时间竟然忘记了天地玄黄的大变革已悄然来临。
山中数日,世上千年。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战役正在紧张筹备。吴克明正在台湾、香港访友,他完全可以金蝉脱壳一走了之,但他拒绝了亲友故旧要他留居海外的劝告,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大陆。他去到春花烂漫的云栖寺,当他召集文理学院师生开会,宣布将前往解放了的济南一探究竟时,不少师生为校长的安全竟失声痛哭,他是校长,怎能在意一己之安危。
这年5月3日,解放军攻占杭州。
五
在暴风骤雨来临前的低气压中,迁到福州苍前山协和神学院及福州市南门协和医院的齐大医学院照常开课。医学生张汝黻、丁云鹏回忆:
齐大医学院医本科为躲避战火,1948年夏由济南经青岛迁往福州,我们男生分别住在福建神学院的苍前山和黑石山宿舍,女生全住在福建女子文理学院的宿舍里。每天乘学校的交通车往返于协和医院和几个其他较小的医院上课、实习。为了便于和病人交往,询问病史,我们还学福州方言。
8月底,我从北京到天津,再乘船经上海到达福州。从闽江入海口溯流而上,经马尾、协和大学到达市内码头,约行四小时。一路风景秀丽,宛如一幅山水画卷。校址位于南台仓前山,地势较高,闽江和对面市区尽收眼底,有大桥连接两岸……
在福州那一年,同学们学习上刻苦攻读,生活上却十分困难。不少人只好靠卖血维持生活。我也卖过三次,一次三百毫升,得到一担(一百六十斤)大米的钱,够一个月的饭费。那时,早饭只有大米粥,喝三四碗撑饱了,但不到十点钟就饿得腹内辘辘作响。
福建本地学生范启修、程素琦却因为齐大的到来而改变命运。他们写道:
很多同学是从小就立志学医,当医生治病救人。但由于家乡——福建省山多平原少,解放前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发达,交通很不方便,到外地上学甚为困难,因此不少同学都先在本省大学学习医预科,以等待机会。1948年秋适逢齐大医学院本科迁到福州,经过考试录取后,我们就成为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一年的基础课学习,更激起我们对医学的兴趣。
1949年8月,解放军攻下福建长泰,截断福州厦门交通线。在福州的齐大医学院负责人也在思考出路。马挺光写道:“据说张光璧教授(福建人)及医学院负责人,想借助福州教会、协和医院为依托,另立福州齐鲁医学院,李缵文教授为医学院院长。福州解放前夕,医学院负责人又准备将师生搬迁到菲律宾。当时医学院学生邵孝珙在校图书馆半工半读,了解到医学院当局将要收拾图书,准备装箱,搬迁到菲律宾,学生得知后即在医学院内展开了‘返校’‘反搬迁’的斗争。”
大多数师生在静待转机。据张汝黻、马挺光、彭万程、段惠灵、范启修、程素琦、王裕民等回忆:
8月15日,解放军攻入福州,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他们有的拉着架子车或黄包车,有的用扁担挑着罗筐,携家带小,杂乱地从苍前山宿舍门前狼狈逃窜。在枪声还断续未停的紧张气氛中,有的同学参加了由医学院发起临时组成的救护小组,带着担架和急救箱,别着带有红十字的袖章,快步沿着去大桥头的大路为遇到的伤员服务。
福州一解放,解放军派员入校宣传政策,并对学生介绍解放后济南的情况。解放军有很多山东人,老乡见老乡情绪激动,同学们要求返校的呼声很高。当时医学院领导对返校态度犹豫。8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学生在乌山路食堂开会,由学生会主席刘琨、杨葆真主持,会上除个别学生反对外,大部分学生坚决要求返校,在解放军福州十兵团政治部的支持下,成立了“返校委员会”。学生代表多次与医学院代院长李缵文商讨返校事宜,最后取得院方同意。经与济南校本部联系,得到校方支持,并汇来三千五百美元为返校经费。
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责成校长吴克明负责齐鲁大学回迁事宜。济南市军管会负责教育的李澄之,要求校方尽快派代表接回医学院师生,重整齐大,造福人民。吴克明和学生代表段惠灵起程前去。他们到了上海,住在新亚酒家。吴克明在上海召开了齐大董事会,沈克非、张汇泉、孙恩三等人与会,商定了齐大医学院院长由张汇泉担任,返校经费去圆明园路中国教会大学办事处争取,由吴克明等到福州,去接回医学院师生等项决定。
1949年10月下旬,齐大医学院所有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装箱,师生们分乘几艘机动木船沿闽江上行抵达南平。再由解放军十兵团政治部利用往前线运输军用物资的空车返回之便,免费把齐大的师生从南平运输到上饶。当时,沿途都能感受到战时气氛,军车上覆盖着绿树枝叶的伪装,还遇到过一架国民党的空军飞机在上空跟踪。经过武夷山时,仍有散兵和土匪骚扰,解放军全副武装戒备,在卡车上架有机枪护卫。师生们安抵上饶,住在一教会中学内。李缵文和彭万程、高维济先去上海找军管会魏文伯政委。魏文伯认为齐大医学院回到新解放区,会起到很好的政治影响,并写信给上海铁路局军管会,要求免费提供火车送师生回济南。
当时几个福建同学曾有些犹豫,怕远离故土,人地生熟,与家里失去联系。当时福建有些小城镇被国军残余占据,担心经济发生问题。在大家的关怀和劝说下,他们终于打消了顾虑,随学校去济南继续上学。北返途中,一位叫韩培慈的女生不幸患脑炎在杭州病逝,她的芳魂永远留在西子湖畔。
1949年11月,在吴克明的率领下,齐大医学院全体师生终于返回济南。
六
此时,齐大面临新的困难,济南原来的校园已被别的单位占用,只得临时在拥塞的空间里艰难办学,许多学生还得住地下室。当时校门口挂了两块牌子,一是私立齐鲁大学,一是华东革命大学。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了齐鲁大学,校长职务由原总务长杨德斋代理。学校在新形势下加强了政治教育工作,将新民主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列为公共必修课,各学院也成立了相应的政治教学委员会。各系师生经过集中学习历史唯物论、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社会发展规律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齐大医学院毕业生原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承认学历和资格。1950年,抗美援朝初期,医学院学生为了表达新中国的主权意识和爱国思想,宣布放弃加拿大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1952年9月,根据华东高等学校调整方案,齐鲁大学撤销文、理学院,理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师生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天算系和文科的部分教师合并到山东师范学院。据苗永明回忆:“1952年,院系调整,程廷芳先生领着齐大应届毕业生徐邦信和胞弟(苗)永宽到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调过去的四位老师组建天文系时,带走了天算系拥有的两架天文望远镜。……‘人去楼空’,齐大的天文望远镜被拆走了,两座观象台只剩下空壳,不久也就拆掉了。其中一座,镶有‘泽普观象台’的石碑,以纪念我国知名天文教育家、齐大天算系主任王泽普先生。齐鲁大学又失去两座标志性的建筑。”
齐大医学院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山东医学院,原齐大的校园由新组成的山东医学院使用。那群从福建考入的学生赶上了好日子。据范启修、程素琦回忆:“齐鲁医学院良师荟萃,他们在教学中具有认真负责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注意把医学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的医德。……1952年初,在我们即将临床实习前,通过三天的政治思想学习,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都表示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当时我们五位同学——徐丽丽、闫国珍、高维济、范启修、程素琦被告知到上海人民解放军科学院(即现今军事医学科学院,1958年迁到北京)报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济南,奔赴新的工作单位。”
文理学院的学生命运各有不同,尤其是1949年5月那批迎接解放,参加军管会办的干部学校的同学。据苗永明回忆:
我仅记得去干校的有化学系四年级雷钊华、物理系二年级赵以成等,雷后来是山师大化学系主任、理论化学教授,赵是复旦大学的宣传部长,他们都享受离休待遇。但是也有部分人历经磨难,如天算系的石辰生,1950年毕业后,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用我堂弟院士(苗)永瑞的话说:“石是天算系真正的天文爱好者。”石几经坎坷,备尝艰辛,死于大饥荒年代,英年早逝,真是太可惜了。但是我们系也有几位成功的杰出人物:永瑞在1991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后又增选为工程院院士;与永瑞同班的赵先孜,曾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是天文方面的著名学者,后任江苏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与程廷芳先生同去南大的徐邦信,在天体物理方面有着突出的业绩。沈、石、赵、苗、徐是我们天算系,也是齐鲁大学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当时,吴克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授命下,奔波于战火硝烟之中,将齐大师生包括外籍教师全部召回。但此次南迁异地办学,被说成“在少数反动分子操纵下,裹挟部分人员和物资到了南方,打算投奔国民党”。吴克明等人自然难脱干系。1950年,吴克明重回山西太谷铭贤学院,1951年秋调山西大学工学院(后为太原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任教授。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受折磨,于1977年9月12日去世。
说到母校的命运,著名的牙科专家、原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王翰章晚年仍有些愤愤不平: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几乎不大知道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所大学。齐鲁沉寂湮没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有解放后政治的因素。解放初,四野有个卫生队,后来成立卫校,一下子占了齐鲁校址,说是合并,实把齐鲁的有生力量都摒弃在外面去了。后来成立的山东医学院齐鲁就没有入了,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入当上。
(《齐鲁大学八十八年——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齐大校友会编,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